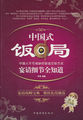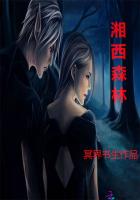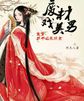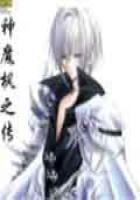)第一节 冯骥才:文人互赏是一种幸福
都说我们的时代没有大师,我却从他们身上,隐约感到了大师的某些气质和特征。
2011年3月13日,是全国政协闭幕的日子,这天适逢冯骥才六十九岁的生日。会后,他给九十四岁高龄的妈妈打电话说,妈妈,大会闭幕了,今天是我的生日,给您道个喜!老妈说,刚才生你的时间,我还在电视上找你呢,我看见你了……老妈的话使他获得一种幸福的感觉。
平常的年月,大冯是从不过生日的。但今年,他特意把夫人顾同昭接到北京。夫妻俩相濡以沫五十载,原来是你记着我生日,我记着你生日;现在则变成一个共同的生日了:我的生日是你的,你的生日也是我的。而且这种变化极其自然,无须努力地刻意地去做去想。大冯说,他喜欢一切都是自然的,该开花就开花,该结果就结果。
傍晚,大冯伉俪如约来到位于北京通州的韩美林艺术馆。这是一个充满丰富想象和艺术灵性的殿堂,馆中的每一座雕塑,每一幅书画和每一件陶瓷艺术品,无不美轮美奂,令人惊叹艺术家生机勃发永不枯竭的创造力。本不想大过生日的大冯,正是被两位文坛挚友——姜昆和韩美林请到这里,策划和组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生日party。从老杜步入韩美林艺术馆的那一刻起就强烈感受到:这场艺术家的生日聚会与礼仪无关,与奢华无关,与一切世俗的应酬无关,所有受邀者不论年龄长幼,职位高低,名气大小,都沉浸在一种亲密、自然、温馨而忘情的快乐中。刚刚在“两会”上提出“文化要承担的责任是使人们精神幸福”的大冯,深深被眼前的景象感动着幸福着……“我的生日变成了大家的节日,这个快乐是大家给我的。”
七十大寿:一场自然的不期而遇的聚会
大冯的生日,一直是以最简单的形式度过的。他的生日是农历二月初九,公历三月五日左右,而这正是他在北京参加“两会”时。他从1983年担任全国政协委员,迄今已连任六届近三十年。最早的政协文艺组委员吴作人、萧军、冯牧、黄苗子、杨宪益、丁聪、张贤亮、谢晋等,都与大冯关系十分融洽,但他不忍为自己的生日麻烦别人!每年的这一天,他都悄悄到“两会”驻地的食堂要碗面条,自己给自己过个生日。有时也会忙得忘了生日,是妻子和孩子打电话来祝他生日快乐,他才恍然大悟。只有两次例外:一次是韩美林周建萍夫妇不知怎么获悉了他生日的时间,三人一起吃了顿饭;还有一次是他六十岁生日时,自觉已到了人生的秋天,为了给自己鼓鼓劲儿,一年中分别到父亲的家乡宁波、母亲的家乡济南和自己身居之地天津及石家庄举办了四次“甲子画展”。
2011年“两会”期间,大冯与韩美林等,在一次会后聊天时,姜昆忽然跑来:“大冯,听说你是这几天的生日?”大冯笑道:“姜昆,我的生日是3月13日,政协会的最后一天,上午参加完闭幕式,下午我就回天津了!”姜昆说:“那不行,大冯,你今年六十九,你不是搞民俗的嘛,过九不过十呀!”这时在场者一齐响应起来:“过,过,给大冯过七十大寿!”韩美林当即表示:“就在我的艺术馆过!”大冯盛情难却,又怕折腾太大,所以特别叮嘱姜昆:“受邀者都是艺术界名流,每个人都一大堆事儿,千万别给大家添麻烦。”后来才知,姜昆当即就给大家群发了短信,以后几天有接到短信的朋友不断向大冯道贺,大冯一看坏了,赶紧问韩美林怎么办,韩美林说:“你甭管了,你的生日聚会归我媳妇管,其中的细节,她对我都保密!”
礼物是心:一条红围巾,一首祝福歌而已
最让大冯感动的是艺术界朋友们那种真情实意,相互信赖,持久可靠的友谊。“比如姜昆,是我朋友中最富热情也最能干的一个。我认为他是中国头号攒局和组台的高手,不经意间,就把人气凝聚起来了,为大家创造着无穷的快乐……”确定为大冯过生日的当天,恰好有人拿来一沓日本卡纸,想请“两会”的艺术家们签名,在场的画家们便灵机一动,即兴为大冯作起画来:韩美林、何家英画马,宋雨桂画山水,冯远画寿星,然后当做生日礼物送给大冯。艺术家历来都用艺术表达他们的真性情。
生日会现场,“老寿星”收到的礼物可以说与礼仪无关,与奢华无关,与世俗的应酬无关,却寄寓着艺术家朋友的一份心意:中央芭蕾舞团团长舞蹈家冯英为大冯买了一条红围巾,亲手给大冯围在脖子上,显得格外喜兴又醒目;指挥家谭利华送的是两瓶从意大利捎来的异域风味的果酒,并在酒签上题写了赠言;歌唱家郁钧剑为大冯赋诗一首,并用他潇洒的书法一挥而就,镶进镜框里;雕塑家曾成钢则将其代表作不锈钢材质的雕塑《莲花》送给大冯……
在受邀的艺术家朋友中,有些人公务缠身,不能亲临现场,也通过多种形式表达了心意:董卿、白淑湘送来祝寿花篮;濮存昕晚上有演出,只能遗憾地发来祝贺短信;姗姗来迟的宋祖英迟到的原因,也是为大冯选购小礼物去了,至于礼物是什么,大冯却秘而不宣。
在送礼的人中,朱军的礼物最“无形”——清唱了一首令大冯感觉很温暖很煽情的歌——《伴你到永远》。演唱前朱军说他特别开心:“我在做《艺术人生》时,深为他保护民族民间文化而竭尽全力的那份真情感动得热泪盈眶。他从一个人开始做起,到现在已引起政府和百姓的高度重视,为子孙后代做了件大好事呀!”
在送礼的人中,韩美林的礼物最“值钱”——赠给大冯一幅他的“天书”作品。韩美林历时三十四年,从中国各地的甲骨、石刻、岩画、古陶、青铜器上的三万多个待考古文字中,探微抉幽,整理创造,变成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显示了中华文化的恒久魅力。韩美林的“天书”作品从不送人,此次慷慨出手,足见他对大冯的浓情厚谊。
别出心裁:“阿凡达”推着蛋糕车来了
生日晚宴上,一连串新鲜有趣的创意令人耳目一新,不时赢来笑声掌声一片,而这些创意都出自韩美林的妻子周建萍。
在韩美林艺术馆的前厅,每一位受邀前来的嘉宾都会得到一份印刷精美的十二生肖动物画片,高度概括夸张变形的造型手法,一看即出自韩大师的手笔。而每位嘉宾按自己姓名标签领到的画片,恰恰是自己属相中的动物形象!周建萍事先做了多少“调查摸底”工作,由此可见一斑。
当“寿星佬”大冯步入前厅时,工作人员立即为他穿上一件特制的T恤衫。T恤衫的前面印着大冯和韩美林抹着红脸蛋的搞笑头像。周建萍请大冯停住脚步,让嘉宾们在他后背上签名并题写贺词。
晚七时,陆续进入宴会厅的嘉宾们从两块电视屏幕上收看了与大冯有关的视频画面。视频中的主持人模仿央视《新闻联播》的方式,用诙谐幽默的语言,播报了全国政协文艺组委员举办冯骥才七十诞辰生日晚宴的新闻,以及介绍大冯艺术人生的图像资料。韩美林艺术馆的漂亮女孩们,还现场表演了天津快板《说说冯骥才》,还跳起活泼欢快的“小兔子舞”。
生日晚宴上的“吃”也设计得别具匠心,充满浓郁的地域特色和文化意蕴。其中有两个亮点尤其引人注目:一是将天津特色小吃“狗不理”总公司负责人和厨师请到晚宴现场,为大家现包现蒸正宗的狗不理包子;其中的三只包子馅中,分别放进大枣、核桃、花生,象征红红火火,和和美美,人生圆满,而有幸吃到者则可获得韩美林的书法作品。二是邀请北京人民大会堂的国宴师傅,用南瓜、黄瓜、胡萝卜、菠菜、紫菜等七种蔬菜磨汁和面,做成三米长的一根“七彩面”,象征“七十大寿,长长久久”,并请大冯当场表演“吃面条”。
更大的意外和惊喜还在后面。当朱军接替李扬担任生日宴主持时,宣布要有一个重要仪式——请“老寿星”切生日蛋糕。而推蛋糕车的女孩是谁呢?一定会让大家眼前一亮!正当大家四处张望翘首以待时,一位手持弓箭全身彩绘的女孩快步上场了。“阿凡达!”人们一齐惊呼起来。
这位比好莱坞大片《阿凡达》中的外星人还要年轻娇俏的女孩,有一个温馨的名字:关欣。为了给大冯和所有来宾一个意外的惊喜,她从早上九点开始化妆,直到下午四点才“变身”为外星人。如此精心费力,令大冯夫妇十分感动,双双走到关欣身旁表示慰问,而关欣也摆出一个拉弓的Pose,让摄影师们纷纷抢拍下这一“人神共处”的美丽瞬间。随着大冯夫妇切蛋糕的动作,台下齐唱“祝你生日快乐”,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生日感言:文人相互欣赏是一种幸福
在那个空气中都弥漫着温情和友情的美好夜晚,恐怕没人会忘记那个精彩乐章中的尾声部分。所有在场嘉宾,无论年龄长幼,职位高低,名气大小,人人都戴上一只绒布制作的兔子耳朵,把自己的双手搭在别人肩上,组成一个蜿蜒的长蛇阵,围着三十米长的餐桌忘情地跳起“兔子舞”。
舞者中有中国文联的老书记胡振民、新书记赵实,文艺界的老领导王文章、周和平、罗扬、丹增等;有姜昆、李静民夫妇和孙小梅、阎维文;有音乐停了仍不尽兴,自己在那儿扭个不停的吴雁泽、刘敏、宋雨桂、滕矢初;有虽未一展歌喉,却舞得很美的宋祖英;而一向斯文的何家英则对着摄影者的镜头扮起了鬼脸……大冯认为,这种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状态,才是艺术家最本真的状态和终极的追求。
即席发表生日感言时,大冯首先夸赞了这次聚会的“东道主”,与他可以“掏心窝子”的韩美林,言谈中不乏深情与幽默:“我和美林是文坛奇怪的一对:我是文坛个子最高的,他是最矮的,这是老天给的,没办法;我们站在一起时,我必须俯视他,但我心里对他是仰视的!别人快乐,他就快乐,这是韩美林最爱说的一句话,也是我们这次聚会的主题!”
大冯认为,在艺术家之间有一种东西特别美好,那就是能够欣赏别人的优点:“欣赏别人的优点是一种幸福。我在政协及文坛接触过形形色色的人,不管他是什么脾气什么个性,都没有关系,艺术家愈有个性愈好。重要的是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种特别的才气、灵性和闪光的作品,能与他们同时代是一种幸福。想想看,如果我们与达·芬奇、梵·高和鲁迅同处一个时代,甚至相识相知,该有多么幸福!所以我爱你们当中的每个人,我享受你们的才华和作品。我今天这个不期而遇的生日的快乐是你们给的。你们使我将这个人生重要的时刻永远铭记在心。”
)第二节 王蒙:别把眼睛盯着“诺贝尔”
说王蒙是中国作家中最富传奇色彩的人物是并不为过的。鼻梁上架副金属框近视镜,衣着朴素,举止儒雅,谈吐幽默。像谜一般吸引着他的众多“粉丝”的,不仅有他非凡的经历,敏锐的思维,还有仿佛与生俱来的探索精神及永不枯竭的创造力。2007年10月,王蒙来津参加他的好友冯骥才主持的国际研讨会期间,老杜与他进行了一次获益匪浅的交谈——
为何在海洋大学研究文学
老杜:您好,王部长(他曾任文化部长),对您仰慕已久,又从大冯书中读到不少有关您的轶闻趣事。听说您在青岛的中国海洋大学创办了王蒙文学研究所。请问,您为何要在一所理工科大学搞起文学研究,五年中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哪些成效?
王蒙:中国海洋大学的前身是山东大学,它本是一所综合大学,文科也非常棒,前后在那任教的有梁实秋、闻一多、老舍、洪深、朱自清……都是文坛大家,可见此地有这个风水,有这个灵气,有这个积淀。后来,山东大学迁到济南,把有关海洋的专业留在中国海洋大学。五年前他们成立王蒙文学研究所,大概是想拉着我壮壮门面吧(笑)!我的研究所与大冯的研究院性质不同,是别人研究我的文学创作。我在这儿最擅长的事是每年都来给学生搞个讲座。另外,我在全国结识很多作家、学者、教授,这是我独有的优势,像铁凝、王安忆、张贤亮、韩少功、张炜、尤凤伟、叶辛、方方、舒婷、叶嘉莹、毕淑敏、迟子建、白先勇、余光中、李希凡、冯其庸都去讲过课,还有大冯和你们天津的赵玫。法国、英国、俄罗斯、德国、日本、新加坡的专家学者也是我们的常客……
老杜:学理工的大学,经您这么一折腾,很可能出来几个文学方面的才子!
王蒙:(笑)也许会吧!我还邀请一些“驻校作家”到海洋大学“作家楼”写作,由学校提供食宿和零用钱——只要您的身影能出现在校园里,抽空与学生座谈座谈,写完书在文稿最后缀上一句“某年某月完成于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即可。这东西当时你不觉得怎么样,十年二十年之后不得了!今天我住的利顺德(饭店)不也这样吗?孙中山也好,胡佛也好,在这儿住上一天也算历史!有一次开我的文学创作五十周年研讨会,张贤亮从宁夏赶来时乘的是一架小飞机,他笑言:“像坐拖拉机一样,我把一百多斤撂这儿了,为你献身了!”作家们都是个体户,平日里各自为战,有这样一个相互沟通交流的平台,对学校,对青岛,对作家都有好处。我们不是要建设和谐文坛吗?
不急于获取“诺贝尔”
老杜:中国作家一般重视人文,轻视自然科学。您曾感叹中国没有达·芬奇、罗蒙诺索夫那样既懂艺术,又懂自然科学的文化巨匠,这是什么原因呢?
王蒙:这个事情现在先不忙。中国之所以缺少文化巨人,与中国特定的历史背景有关。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处于急剧动荡之中,一次次战争,政治运动,尤其是“文革”,连生存都成问题,如何造就文化巨人?而且,正规的教育屡受干扰,谁能规规矩矩上学,认认真真读书?我们本来就是一个科学不发达的国家。刚才电视新闻报道说,一位德国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我们离这个还有相当的距离,但我认为不必着急。因为中国人脑子很聪明,现在又实现了社会稳定,大家能塌下心来念书,扎扎实实搞试验,做学问,写书,国家才有希望。
老杜:提到诺贝尔奖,据说您已四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您对获奖有无期待?
王蒙:那是关心爱护我的人提的,不仅是美国一批华人作家,还有其他方面的人士。这里边有许许多多复杂的情况,这些情况我在第三部自传《九命七羊》中会有详细的披露。
心态浮躁只是一个过程
老杜:我们正在构建和谐社会,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创作环境,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开始崇尚物质,沉溺于享受,从而造成文艺作品的娱乐化和平庸化,您认为这是正常的吗?
王蒙:这也是社会转型期一种尚不成熟的心态浮躁的表现,我认为这只是一个过程。因为从饥饿线挣扎过来的人,刚吃饱肚子,突然口袋里一下有了钱,又要买车,又要买房,还要买首饰做美容(笑)……这个问题,我觉得慢慢能变得理智起来。总的来说还是往好的方面发展,我不主张过分夸张这个过程,情况并没有人们想象得那么悲观……
阅读的魅力无可替代
老杜:您在中国作协做领导工作多年,我想问一个文学创作方面的问题。记得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林海雪原》《红旗谱》《苦菜花》《红岩》……每出现一部优秀长篇小说,都会引发全民的阅读和欣赏,包括据此改编的影片,为什么现在小说多了,却缺乏动人心魄的经典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