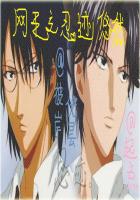在这批被砍头的罪人之中,就有庆余堂的掌柜施景芝。不但施景芝要身首异处,连同他的夫人、儿女、佣人、伙计一干人等,老老小小三十余口,全要在午时三刻,辞别人世,不向天堂而奔地狱了。
这批人因了何事,而触犯了天条,惹得龙颜大怒,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呢?他们的死,又与一个小小的驿站站长有何牵连?
这事还要从头说起。
施景芝的祖辈是肃州祁连山下的药工,主要是以采挖野生大黄为生。传至他的父亲,已经是五代人了。
大黄,在植物分类上属蓼科,多年生草本植物,高约两米,地下有粗壮的肉质根及根状茎,单叶互生,花淡黄色,产在西北、西南海拔两千米左右的高寒山区,喜干旱凉爽气候。
大黄别名又叫黄良、火参、将军、川军等等,按产地分类又分别唤做南大黄与北大黄。但其中品质最优良的是产于肃州、凉州与西宁等地的野生大黄。
中医认为,大黄可调中化食,安和五脏,平胃下气,并敷一切疮疖痛毒,是一种常用与常备的药材。然而在中亚、西亚以至欧洲,长期以来把大黄当做一种珍贵的奇药。中亚的游牧民族,在不知饮茶之前,全靠中国的大黄健胃消毒。而中世纪的欧洲人,更是迷信中国大黄,把它视为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
12世纪生于开罗的阿拉伯名医伊本·贾米在其专著《大黄考》中,记载了中国大黄、突厥大黄、波斯大黄、叙利亚大黄的研究成果,认为“强肝健胃以及促进其他内脏功能最有力的大黄,治疗急性腹泻、痢疾和慢性发热最有效的大黄乃是中国大黄,而事实上最有镇静作用、渗透性最强的也是中国大黄”。
正如大黄有凉州大黄、西宁大黄、四川大黄、天水大黄、河州大黄等名称一样,肃州所产的大黄名叫肃州大黄,又称肃州黄。1550年,威尼斯地理学家赖麦锡记述了一位亲自从肃州贩运大黄到威尼斯的商人哈智·摩哈默德的谈话。哈智说,中国有很多地方都产大黄,但最佳者是产于肃州附近高峻的石山之上。哈智还为赖麦锡展示了一幅精心绘制的大黄图,这也是欧洲人第一次看到的大黄原物图。
正因如此,从中世纪的欧洲到近代的中亚,古丝绸之路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可以叫做肃州黄之路。1675年出使中国的俄国使团团长斯帕法里在《前往中国之路》一书中说,肃州是大黄的产销地,托博尔斯克人和布哈拉人都沿着这条路去那里收购大黄。的确,欧洲所有的大黄,都来自这个地区。
由于大黄贸易有暴利可图,沙俄政府一度实行垄断经营,私贩大黄者将处以死刑。但因为垄断,又造成了沙俄帝国大黄奇缺,沙俄政府不得已于1727年宣布大黄自由贸易。为了满足国内需求,俄国人甚至不顾大清朝廷的禁令,试图引种大黄,但因缺乏技术支持,显然没有成功。
施景芝十岁那年,他的祖父因为跟随贩运大黄的布哈拉商人前往俄国,打算帮助俄国人栽培肃州黄。虽然他非常清楚这样做的后果,但帮俄国人种大黄赚的钱,要超过上山采挖大黄上百倍。施景芝的爷爷做梦都想拥有一家自己的药材商铺,而仅仅靠采挖大黄赚的银子,是一定不会实现这个梦想的。
也许上苍注定施家要为肃州黄付出生命的代价,结果是施景芝的爷爷被边境卡伦的清军查出,全家抄斩的黑云顿时压顶。
在一家人从祁连山里押往肃州城受刑的路上,夜宿驿站的施景芝引起了老干棒的注意。老干棒为这家人送晚饭时,十岁的施景芝那双眼睛,如同弹弓射出的石子,一下子就击中了老干棒那已经粗糙不堪的心灵。乘押送的清军不注意,施景芝的父亲从隐秘处掏出一锭白银,递给了老干棒,低声说道:“救下孩子,这是我唯一的根!”
老干棒迟疑了片刻,收下了银子。
当夜,负责押送人犯的清军管带认真地掂了掂那锭银子,微笑着对老干棒说:“老干棒,咱们也是老相识了,就这一小块玩意儿,要换一条命?”
“我就这一点积蓄,您就发个善心。”老干棒苦着脸。
管带瞟了一眼进屋送水的女娃:“她是个谁吗?”
老干棒打了个哆嗦:“她是俺的女人,刚从老家来,要和我成亲呢。”
女娃低着头,退了出去。
管带的眼珠子没转圈,盯着女娃消失的背影,半晌没言喘。
老干棒说:“行不行?”
管带回过神来:“嗯,好。水灵,好。老干棒,这是笔掉脑袋的买卖。不答应你,这银子不归我。答应你,我觉得有点亏。这样,今晚那女娃归我用一下,明日你就连婆姨带娃娃全有了。咋样?”
老干棒盯着管带看了半晌,没言喘。
管带心里发毛:“你看
个啥吗?我脸上又没写字。”
“我觉得你脸上有字呢。”老干棒的脸色阴沉得要下雨。
“有字?有啥字吗?你真会说笑话。”管带边说边用手在脸上抹了几下。
老干棒说:“写着呢,臭不要脸。”
管带的笑容凝固了:“你咋骂人呢?”
老干棒狰狞地:“我还会宰羊呢!”
“好,有种。老干棒,别忘了,是你先找的我。一个女子都舍不得付出,还想救命?给,这是你的银子,收好。”
管带把那锭银子扔到老干棒脚下,吐了口唾沫,转身走了。
老干棒愣了。
许久,外面传出一声狗叫。
老干棒惊了一下,蹲下身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