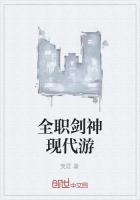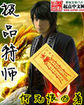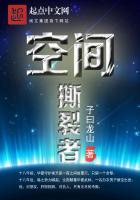上文已经提及整个小说文本可以被视为作者用某种方式记录下的叙述者说的话。因此,叙述者转述人物的讲话或“想”话,就是转述中的转述,双重转述。转述方式不可避免地卷入叙述主体的复杂分化和分配。
叙述文本中所有的转述语无一例外受制双重主体——说话人物与转述叙述者。应当说,转述语既是人物说的话,就须独立于叙述者主体;转述语既然是叙述者转述出来的,是叙述文本之一部分,经受了叙述加工,就须受叙述者主体控制。二者矛盾,形成一个根本性的悖论。
可能因为汉语中没有引语动词时态接续问题,转述语问题在中国从来没有受到欧洲修辞学自古以来给予的那种重视,在中国文学史或语言学史上,甚至没有给转述语分类。但就是在西方,转述语分类也至今没有统一的意见。本书试用一种简单而明晰的分类。
分类之一:直接式与间接式。直接式假定保持了原语言,说话人物自称“我”;间接式把说话者的语言改写成转述者的语言,说话者自称“他”。
分类之二:引语式与自由式。引语式用一些特殊标记,最常见的引语标记是“他说”之类的引词,有时还用写印方式标记(例如引号),把转述语与叙述语流隔开;自由式没有任何标记,因此在书面形式上与叙述语流混杂。
把两个分类相叠交,就有四种基本形式:直接引语式,间接引语式,间接自由式,直接自由式。这种分类方式似乎适用于包括汉语在内的许多语言。
引号并不是可靠的引语式标记,汉语原无引号,而且许多语言,包括现代汉语,无引号的直接引语依然很常见。实际上,直接引语可以只用引号而不用引词,也可以只用引词而不用引号,只要把转述语从叙述语流中隔离出来就行。在很特殊的场合(例如在文言文中)二者可以都不用而仅靠文体延续构成直接引语。在中国白话小说文本中,引词是唯一的直接引语标记。
从理论上说,人物的任何想的或说的话语都可以用这四种方式转述。四种方式虽然内容相同,主体控制方式却大不同。在每段转述语中,叙述者与人物不断地在抢夺更大一份主体性。所有这些标记——引词,引号,自称方式,都是叙述语流与转述语对抗的痕迹。简单地说,可以看到四种转述语中主体分割方式有如下区别:
在直接引语式中,(他犹豫了,他想:“我犯了个错误。”)转述部分用引词和引号从叙述语流中隔离出来。人物主体几乎全部保留对转述语的控制权。
在间接引语式中,(他犹豫了,他想他犯了个错误。)人物的声音几乎完全被吸纳进叙述语流之中,叙述者主体几乎全部控制了转述语。
在间接自由式中,(他犹豫了,他犯了个错误。)叙述语流改造了转述语,但引词消失等于叙述者失去一个干预的标记,转述语处于比较独立地位,有时读起来甚至不再像转述语,而像一个叙述声明。
在直接自由式中。(他犹豫了。我犯了个错误。)人物主体不仅控制了转述语,而且,由于转述语与叙述语流相混杂,人物主体渗透到叙述语流中去,反使叙述流受到人物影响。所谓内心独白和意识流,就是这种渗透在大规模范围上形成的特殊语体。
二
古汉语无引号,无时态延续,文本不分段,引导句带直接引语就成为必然的引语方式,不然引语部分与叙述背景难以区分。然而,文言同样具有这些语言学特征,文言记叙文,包括文言小说中,引语方式却是多种多样,间接式与直接式都可使用。直接引语式在白话小说中几乎成为唯一转述语方式,根本的原因并不完全在于汉语的特征,而在于白话与文言是不同文化层次的表达方式。
但是,叙述艺术又要求引语形式有变化,在白话小说中,这种变化只能是直接引语式中的变异。
当引语中说话者没有自指时,甚至没有间接自指(例如叫听者为“你”,以暗指“我”的存在),确定直接引语会有困难。在某些语言中,动词时态之接续是重要指示,汉语动词无时态变化,就只能靠风格特征。如果转述语风格与叙述背景类近,就很可能是叙述者主体占上风的间接引语;如果转述语保持了人物与叙述者不同的特有语汇及风格,就应当是人物主体占上风的直接引语。
问题是,这个判别规则并不适用于中国传统白话小说。在传统白话小说中,经常遇到一些形式上是直接引语,事实上却是间接引语的语句。
(在下面引的例句中,为了表现传统白话小说在这问题上的特殊性,我将去掉现代编者加的标点符号,而代之以传统的圈点。实在说,现代式标点加诸于传统小说,虽然读起来方便了,却时常歪曲了原文叙述方式。)
《三国演义》第九十九回:
却说司马懿引兵布成阵势。只待蜀兵乱动一齐攻之。忽见张郃戴陵狼狈而来。告曰。孔明先生如此提防。因此大败而归。
张郃与戴陵说的话,有引导语。现代编者在“告曰”后面加了冒号和引号,使之变成了绝对的直接引语。可是这二人说的话,明显经过叙述者加工,用“如此如此”避免重复前文说过的情节。二军恶斗,却尊称对方为“先生”,也可能是叙述者语气,而不太像张郃戴陵的语气。
上述例子,我建议改为间接引语式,即不加引号。标点中国白话小说的编辑在“告曰”、“说道”之后,一律加引号,似乎太机械了一些。
有时候,转述语落在间接直接之间,可间可直,无所依傍。《西游记》第八十九回:
八戒道。哥哥。我未曾看见那刁钻古怪。怎生变得他模样。行者道。那怪被老孙使定身法定住在那里。直到明日方醒。我记得他模样……如此,如此,就是他的模样了。
这一段话中,孙悟空的话,不完全是直接引语,因为其中“如此如此”表明不是原话直录,但又无法视之为间接引语,因为说话者孙悟空自称我,称对方猪八戒为你。我们只能说,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直接引语,可能是中国传统白话小说所特有。现代标点符号在此种情况下,加也不好,不加也不好,几乎完全不适用。
那么,不加引号,视之为自由式,如何?显然不行,因为引导句“曰”、“道”永远安在那里,以分隔转述语与叙述语。一旦被隔开,就非自由式。但在某种情况下,传统白话小说中的引语扭曲得相当严重,以致引语的某些部分与引导语脱离了关系。例如《三国演义》中的此句:
程昱献十面埋伏之计。劝操退军于河上。伏兵十队。诱绍追至河上。我军无退路。必将死战。可胜绍矣。
在此段中,唯一的引导句是“劝”,这不是惯用的直接引语引导句,因此它引导出来的转述语可以被视为间接语。但是,最后三小句说话者自指“我”,应当是直接转述语,而且它与引导句隔着一个间接引语,因此它本身不应当是引语式,而是自由式。《三国演义》的现代编者把“劝”字之后的全部两段引语圈在引号之中,实际上这两段都不可能是直接引语。
此类例子在中国传统白话小说中极多。《金瓶梅》词话本第十二回有一例:
……(潘金莲)到晚来归入房中。粲枕孤帏。凤台无伴。睡不着。走来在花园中款步在花苔。月洋水底。犹恐西门庆心性难拿。怪玳瑁猫儿交欢。斗的我芳心迷乱。
这段中,“犹恐”和“怪”都不是引导句,但最后一句明显是直接式转述语,它只可能是自由式。《金瓶梅》崇祯本可能认为这安排不整齐,把“我”改成了“他”,使这句不再是转述语,成了心理描写。其实词话本这种句式在其他小说中也常可遇到。《隋史遗文》第四十八回:
(世民)差人搜出尚德儒。责他指野鸟为鸾。欺人主取高官。砍了。家属并不伤犯。
此段中,引导句“责”之后显然是间接转述语(称对方为“他”),但是最后二小句是命令式,应当是直接转述语。而且与引导句无关,它是直接自由式。
因此我们在中国传统小说直接引语式一统天下中看到一个变异的方式:
引导句+间接引语式+直接自由式
这个结构看起来有点勉强,但实际上可以写出非常自然流畅的转述语。《警世通言》中的名篇《玉堂春落难逢故夫》有一例:
玉姐泪如雨滴。想王顺卿手内无半文钱。不知怎生去了。你要去时。也通个消息。免使我苏三常常牵挂。不知何日再得与你相见。
这里的引导句是“想”。一般说,在中国传统白话小说中,心里想的,用间接引语的机会比较多。但此段中的间接引语中途转入直接自由式,用“我”直接向“你”倾诉。此段直接自由式实际上已接近现代小说研究所谓“内心独白”体。
在口述文学中,从间接式到直接式的转换是比较方便的,只消表演者从自己的口吻突然转为人物口吻即可。甚至,他可以以歌代词。此类以歌代词也在传统白话小说中出现。《金瓶梅》词话本中例子特别多。第二十回:
西门庆心中越怒起来。指着骂道。有满庭芳为证。虔婆之不良。迎新送旧。靠色为娼……虔婆也答道。官人听知。你若不来。我接下别的。一家人指望他为活计……
(第六十一回):
官哥儿死了。李瓶儿大哭。又一头撞倒地下。放声哭道。有山坡羊为证。叫一声青天。你如何坑了奴性命……
万历本全部删去了这些诗词,或改写成散文。但实际上不自然的并非诗词代言,而是双引导句。看来第二个引导句(“有满庭芳为证”等)是为了表证转述语风格的转变。
这导出了一个问题:人物不太可能以诗词代言,用诗词写出的转述语明显是叙述者加工过的语言,因此不应当是直接引语。但“指着骂道”,“放声哭道”明显是直接引语的引导句。在此,我们又见到一种“假性”直接引语。
中国传统白话小说中直接引语之多变,或能使我们对直接引语式转述的本质了解得更深一步。不少叙述学者,例如恰特曼和热奈特,都认为直接引语给人物主体以绝对的控制权,叙述者没有任何干预能力,因为直接引语从底本形态中直接取来。我认为完全排除叙述者主体是不可能的,因为叙述者只转述人物的某些语言,而并非其全部语言,就是一种选择。选择是叙述加工的最重要方面,况且自然状态的语言录成文字,就已经过叙述改造。
从中国传统白话小说的直接引语诸多变异中我们可以看到直接引语可以有“指称分析”与“质地分析”两种倾向。在30年代初,巴赫金写了两篇对俄国小说转述语的典范分析。他指出,由于俄语的特殊性质,间接引语一直在小说中占主导地位。但在不同时期,间接引语的性质不同。某些时期人物主体占优势,引语倾向于保留人物言语的风格,称为“质地分析”(textureanalyzing)。在另一些时期,间接引语中叙述者主体占优势,倾向于让人物言语溶入叙述语流,称为“指称分析”(referentanalyzing)。
从理论上说,直接引语,只能质地分析,而且是绝对的质地分析,但在中国传统白话小说中,直接引语可以倾向于指称分析。早期的白话小说,所有的人物语言风格几乎完全类同而且与叙述语流的风格一致,都是一种俗化的半文言。甚至性格分明的粗野人物,甚至在口述文学中早已获得特殊语言风格的人物,例如“邓艾吃”,也不再具有个人语言风格。这在早期历史平话中特别明显。
李商隐在9世纪写的诗句:“或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骄儿诗》)很多学者认为这是口头叙述艺术最早记录之一。任半塘(《唐戏弄》,1958年版,第151页)认为这是儿童戏仿早期戏曲表演。无论怎么说,到《三国演义》或《三国志平话》成书之时,邓艾已在说三国与演三国中口吃了几个世纪。而到书面文本出现时却有口吃之名而无口吃之实,这证明白话本小说远非口头文学记录本。
到《水浒传》成书时,直接转述语的质地分析开始出现,不过只出现于市井小民(郓哥、王婆等)或粗野人物(李逵、鲁智深等)口中,其余略有社会身份的人都讲一式的语言。金圣叹说:“《水浒传》并无之乎者也等字,一样人,便还他一样说话,真是绝奇本事。”是过誉。《水浒传》中,连武松、杨雄这样略识文墨的粗汉,说的话风格相当雷同,更不用说社会上层人物。
这种情况,到16世纪中叶,以《西游记》和《金瓶梅》为标志,发生了重大变化。《西游记》语言诙谐,质地分析比较容易做到:
行者摆手道:“利害!利害!我老孙自为人,不曾见这大风——哏,好风!哏,好风!”(第二十一回)
烧火小妖……惊醒几个,冒冒失失地答应道:“七——七——七——滚了!”(第七十七回)
而《金瓶梅》才真正做到了人物个性化。张竹坡说“《金瓶梅》妙在善于用犯笔而不犯也。如写一伯爵,更写一希大,毕竟伯爵是伯爵的,希大是希大的,各人的身份,各人的谈吐,一丝不紊。”虽略有过誉,倒也不尽失实。
如果说《金瓶梅》依然占了一个便宜,即大部分主要人物是社会中下层。那么,《红楼梦》人物上至王公贵族,下至贩夫走卒,真正做到了直接引语的质地化。只有当白话小说成熟到这个阶段,我们才能说人物主体在转述中有能力争夺言语主体。不然,即使白话小说直接引语一统天下,也没有人物说话者的发言权。
三
在晚清小说中,直接引语依然是几乎唯一可行的转述语形式,由此而引出的各种难题也依然存在。《九尾龟》一例:
(章秋谷)……忽然眉头一皱。想出一条接木移花的计策。心中大喜道。有了有了。只消如此这般。这事便有二十四分拿手。不怕书玉再装腔。
“有了有了”的语气是直接引语式,但是“只消如此这般”又是间接语的省略式。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引导句是“心中大喜道”。心中的“想”话,在中国白话小说中比较经常进入间接引语式。
尤其在第一人称小说中,叙述者兼主角人物,就更容易在叙述中转述他作为人物的思想,而这些思想更容易进入间接引语式。下引例子摘自《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四十六回:
过了这天。明日一早。我便出了衙门。去拜张鼎臣。鼎臣见了我。十分欢喜。便留着谈天。问起我别后的事。我便大略告诉了一遍。又想起当日我父亲不在时。十分得他的力。他又曾经拦阻我给电报与伯父。是我不听他的话。后来闹到如此……当日若是听了他的话,何至如此。
“想起”之后的,是间接引语式,有的地方是总结式的节要,有的地方是几乎原“思”直录(例如上面加着重号的段落),这是间接引语式特具的弹性。甚至间接自由式都可能在这种第一人称叙述中出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十八回:
只一番问答。我心中犹然照了一面大镜一般。前后的事。都了然明白。眼见什么存在生息的那五千银子。也有九分靠不住的了。家族中人。又是这样。不如依了母亲的话。搬到南去罢。
最后一句话是转述语,但找不到引导句,只能视之为自由式。在另一部第一人称小说《冷眼观》中,此类“想法”转述也常用间接引语式,间或用间接自由式。
在第三人称小说中,这两种间接式都不容易安排,但造成的风格变化就更明显。晚清小说大量进入人物内心世界,间接引语用来写想法,造成许多新的可能性。吴趼人的《恨海》中,人物说得不多想得多,但主人公大部分的想法依然用直接引语转述,其中“想”话者自称为“我”。如此长段的思想过程转述在中国小说中还是首次。奇怪的是,此小说的现代编者并不把这些直接引语放在引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