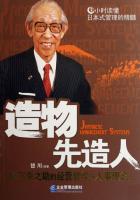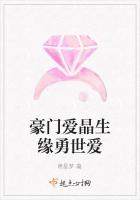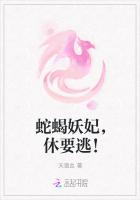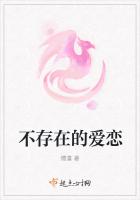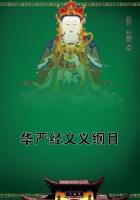其次是资金缺乏、思想闭塞落后。左宗棠给甘肃引进机器设备前曾说过:“官开之弊防不胜防,又不若包商开办,耗费少而获利多。似须以官办开其先,而商办承其后。”《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三),第520页。19世纪70年代,东南地区有一批手中积聚着大量货币财富,想投资于近代企业的官僚、地主和买办商人,要在那里实行这种官带商办经营企业的政策,是不太困难的。可是甘肃却不同,长期以来就“寒苦荒俭,地方数千里,不及东南一富郡”《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三),第478页。能够集到巨额资金的富户不多;且这些人僻处内地,对于试办企业的新鲜事物还少见寡闻,满脑子的陈旧思想,在没有见其利而得其惠之前,断不会冒倾家荡产之险去经营新兴的机器工业。甘肃也没有一批与外国人长期打交道而发了财,眼界又比较开阔的买办商人,如唐廷枢、徐润、郑观应等辈。为数可怜的旧商人还“未闻陇上行商战胜于上海、京都之说,况澳、美、英、法之远在外洋,其足迹更梦想不到
也”《陇右纪实录》(卷八),《中国近代开发西北文论选》(下),第78~79页。,
根本没有那种胆识和才智来接办从外洋引进的机器工业。因此,左宗棠官带商办的主张也就无法实现,而《申报》所说:“设能将此局(注:兰州织呢局)归作商办,涓滴无遗,安见必无起色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第905页。当然只能是仅做议论而已!
(3)对开发中的民族利益问题,重视不够。
左宗棠在对甘肃开发之初,对回族进行强制迁徙,破坏了当地原有的经济结构,造成了回族社区和当地经济的落后。战后,回族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作为“叛产”被剥夺,生活毫无保障,生存受到极大威胁。左宗棠每平复一地,都要对当地回族进行强行迁徙。在镇压了金积堡回族起义军后,将2万多名陕西老弱回族安置在平凉与华亭交界的化平川、圣女川等处,并将侨寓的甘肃回族3千余人解赴平凉安置;在镇压了河州回族起义军后,将陕西回族3万多人安置在平凉、会宁、静宁、安定等荒偏地区;在攻破西宁后,将“西宁陕西老弱妇女壮丁合计两万有奇,悉数迁移平凉、清水、秦安诸处”;肃州城破,将屠杀所剩的起义军家属全部外迁。河西出现了“自是甘、凉、安(安西)、肃一带无回族聚处”的现象。
强迫迁徙给甘肃回族带来了灭顶之灾,传统回族经济几乎被扼杀,严重妨碍了回族自身的社会发展。此外,还实行严格的政治管制,限制回族的人身自由。左宗棠对回族迁徙的原则是:“回民近城驿非所宜,近汉庄非所宜,并聚一处非所宜……分起安置,痪其群,孤其势。”《左宗棠全集·奏稿》(卷五),第282页。每安插一起,先令查造户口清册,编审户口,发给门牌,每一居住区设官严加管制;一旦安插后,不得“私迁”、“合居”或私返原籍,严禁回族有往来各地的自由;去附近城市探亲、购物者,须得百家长允准和领取“号签”,去省内远府州县,须得地方官允准并领取“路票”,违者严办;在迁徙地实行联甲制度,设置十家长、百家长,不准阿匐管理回族事务;不准在近城地方进行商品贸易;他处外来亲友到家,必须报知百家长方准招留,违者察究。
强迫到迁徙地之后,封闭的地理环境,物产的极度贫乏,再加上行动自由受到限制,都决定了经商活动的非可能性。强制的迁徙使西北回族社区逐渐分散,规模缩小,回族的商业贸易遭到破坏,经商的回民被迫迁徙至贫困山区,成为垦荒的农夫。例如,处在丝绸之路上的商业重镇肃州、陇西等地,经过战乱和迁徙后,这里再也找不到回族商人了。这就造成了这些地区经济结构上的单一化,使西北回民长期局限在贫困的小农经济之中,这也是近代这些地区长期贫困的重要根源之一。
(4)开发甘肃的政策缺乏连续性。
在封建社会的人治环境下,政策的变动往往取决于重要人物的去留。所以,许多有眼光的政治家都非常注重汲引和培养人才,以继承和光大自己的事业。左宗棠离开西北以后,人去政怠,人亡政息,许多重要的开发计划都没有坚持到底,造成了很大的缺憾。并不是左宗棠不注重人才,相反,他为开发和建设西北,发现、引用和培养了一大批的人才,还一一加以重用。但大概因为左宗棠是“中兴名臣”,眼界、资望威重一时,又深得朝廷倚重,所以,有关西北地方的兴革大计,均可凭自己的见解才识,一一决断,其后继者却未必有这样的威望与气魄。他们不仅不能开拓创新,就连维持左宗棠的开发规模也难以做到。关于这一点,秦翰才在《左文襄公在西北》一书中有一段精到的议论:左宗棠在西北“只完全恢复了这一个地区的主权,却没有完全改善了这一个地区的政治和社会状态。……所以文襄公一去,地方弊政很容易恢复了原状。财政在甘肃,根本因为经济力量所限,本是不易积极开源,所以文襄公离位的次年,(后继者)竟不惜破坏文襄公禁烟的成规,公然征收烟厘。至于文襄公的物质建设,人力多靠楚湘各军,财力都就军费挹注,甚或由他自己捐廉;而这种军费,又是特准开单报销,不按则例。后来的人没有这种机会,或不会运用这种机会,又不像他慷慨,只好听他们停废。虽是有些建设,文襄公曾顾及日后的维持,曾规定办法,例如关外沿路官店,对于来往客商,准许酌收费用;又如有几个机关,指拨公地取租,但怕仍难持久。至如甘肃织呢局,没有流动资本,更是无从经营。不过吃亏还在人才缺乏;如有人才,就应有办法。……清政府在文襄公去后,所用西北大员,像陕甘总督一席,从杨昌浚(护理),而谭钟麟,而杨昌浚,而陶模,而魏光焘,新疆督办和巡抚一席,从刘锦棠,而魏光焘(护理),而陶模,而饶应祺,无不和文襄公有深切的渊源。便是其下的布政使和按察使,也几无一不是文襄公所识拔。这一个情形,一直延续到光绪三十年左右。照理他们该能扩展文襄公的设施,或至少该能保持文襄公的规模。然而事实则不尽然,或因他们的人格,不够转移风气;或因他们的气魄,不够支持困难;或因他们的眼光,不够担当大事;或因他们的资望,不够笼罩一切,以致文襄公的志业,没法继续或完成。”甚至出现了对左宗棠“苦心经营的制造局和织呢局,后人随意裁并”的事;更出现像“文襄公禁烟,杨昌浚来开征烟厘;文襄公办到甘肃乡试分闱,陶模来又议并入陕西”的可叹可悲之事。所以,“从这来看,创业之人,固属重要;继事之人,尤为重要”《左文襄公在西北》,第222~226页。左宗棠在西北的事业难以为继,已经不单纯是一个人才的问题了,而是封建制度发展到了晚清,已气息奄奄,毫无生气,丧失了全部的更新与创新能力,凭借这个制度,已无法完成开发西北、挽救中国的使命了。而这已不是任何个人所能够左右的事情了。
(三)对西部大开发的启示
左宗棠治理与开发甘肃,是中国近代建设大西北的首次尝试。尽管他的很多设施并没有贯彻到底,甚至人亡政息,甘肃与西北贫困依旧,但是其影响却是十分深远的。左宗棠“白头戍边”,誓死保卫西北,全力开发西北的献身精神与历史功勋,深深激励着后人,为后起者提供着巨大的精神力量与智慧启迪。正如《左文襄公在西北》一书的作者秦翰才所指出:“亏得文襄公坚忍奋斗,才算给吾们保全了这一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疆土,同时也是保固了西北毗连各省区。且新疆自用文襄公主张而建省,由军府制度进而为郡县制度,从前属国性或殖民地性的西域,永为吾国本土的一部分。……在吾中华民族筹边史上,实占着空前的一页。”《左文襄公在西北》,第221页。
秦翰才还高度评价了左宗棠经营西北所留给后人的宝贵启示:“文襄公以新疆为我国的生命钱,又以甘肃和陕西为经营新疆的基地。他明了国际的危机,他懂得内在的乱因。所以他于以武力收回这个地区以后,更加以苦心的经营。他筑路,筑城,改兵制,制造新兵器,一方面巩固国防;他开辟河渠,提倡种棉织布,育蚕缫丝,以机器织呢,一方面开发资源;他设书院,设义学,刊发书籍,一方面又发扬文化。现在西北形势的重要性,没有变更。我们要建设西北,要保卫西北,那末,巩固国防、开发资源和发扬文化,都得同时并进。没有国防,就不能维护资源;没有资源,就不易树立国防;没有文化,也就无从齐一民众的心志,提高民众的知识水准,共同负起这一个巩固国防和开发资源的使命。”《左文襄公在西北》,第224页。这充分说明,开发与建设西北是一个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必须同时并举的规模宏大的系统工程。必须全力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发展西部地区教育是改变西部落后面貌的关键
当年左宗棠在甘肃,就痛感优秀人才的缺乏,一方面各级地方官员的政治品行低,造成吏治的腐败;另一方面广大百姓的文化素质低,使先进的生产技术很难推广,甚至有一些灾民领到救济款后不去买粮食而去买烟土。而贫穷落后的经济条件与艰苦的自然环境,不仅留不住优秀人才,甚至造成一般百姓的大量流亡,这就更加加剧了西北的贫穷落后。“这样,这个地方没有优秀分子,正气消沉,人才不出,或许可以继续腐败,永远衰落。”《左文襄公在西北》,第225页。因此,为了振兴西北,必须坚定不移地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