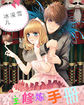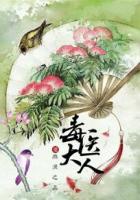学衡派注意到胡适文学革命论理论之基点在于“文学的历史进化观念”:“胡君之倡文学革命论,其根本理论,即渊源于其所谓‘文学的历史进化观念”’,“一代新文学事业,殆即全由此错误观念出发焉”。吴芳吉认为这种“文学的历史进化观”是对文学自身艺术性的忽略和损害,“历史的文学观念既生,于是新派之陷溺以始。新派之陷溺由此始者,盖只知有历史的观念,不知有艺术之道理也”。学衡派则从各个角度论证衡量文学作品价值的尺度存在于文学作品自身,而不应该仅仅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去衡量。文学的流变自有其特点和规律,各个时代的文学都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吴芳吉提出了“文心”的概念:“夫文无一定之法,而有一定之美,过与不及,皆无当也。此其中道,名日文心”,文心就是使文学作品产生美感的技法、风格、尺度等等要素。各个朝代的文学虽有变易,但各个时代的文学都有其文心,而文心的价值是不会因时代变迁而磨灭的:“盖文心者,集古今作家经验之正法,以筑成悠远之坦途,还供学者之行经者也。故作品虽多,文心则一,时代虽迁,文心不改。欲定作品之生灭,惟在文心之得丧,不以时代论也。”另一位《学衡》的作者易峻也认为文学最主要的因子是情感和艺术,这些都是无所谓进化、退化的:“文学之历史流变,非文学之递嬗进化,乃文学之推衍发展,非文学之器物的时代革新,乃文学之领土的随时扩大。非文学为适应其时代环境,而新陈代谢,变化上进,乃文学之因缘其历史环境,而推陈出新,积厚外伸也。文学为情感与艺术之产物,其身无历史进化之要求,而只有时代发展之可能。若生物之求适应环境以生存,斯有进之要求。文学则惟随各时代文人之创造冲动与情感冲动,乃承袭其先代之遗产而有发展之弹性耳,果何预于进化与退化哉。”“文学情感与艺术之物,更多为古今人生之所共通,能表现古人之情感与艺术者,而乃不能表现今人之情感与艺术耶。”
学衡派反对文学的进化观念,强调各个时代的文学都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表现出了对文学传统的深厚的依恋之情。进而他们作出卫道的姿态,以维护文言文在正统文学中的地位为职志。他们对新文学运动提倡白话文、废除文言文的主张极端反感,在白话文已被社会广泛接受的情况下,依然起来维护文言文,试图阻挡白话文一统天下的进程。
学衡派认为白话文固然有其优点,但文言文更胜一筹,更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和不可代替的作用。邵祖平从文字日常应用的角度论证文言优于白话,他说:“夫文字不过意志、思想、学术传达之代表,代表之不失使命及胜任与否,乃视其主人之意志坚定,思想清晰,学术缜密与否为断,故其人如意思游移,思想淆杂,学术偏缺者,其文必不能令人欣赏以领会。文言然,白话亦何尝不然,盖为文必先识字,识文言之字与识白话之字,固无以异。文以载道,文言之能载道,与白话文之能载道,亦无以异也。至其传之久远,行之寥阔,文言视白话为超胜,良以白话之文尔见缕,篇幅冗长,不及文言之易卒读,一也。白话文以方言之不能统一,俗字谚语,非赖反切不可识,不及文言之久经晓喻,二也。沈约有言,文章有三易:易见一也,易识字二也,易读育三也。王通有言:古之有文约以达,今之文也繁以塞。由此言之,文言白话,知所从矣。”
学衡派对于文言文白话文不同的立场比较集中地体现在易峻《评文学革命与文学专制》一文中。这篇文章首先批判了胡适的文学的历史进化观,然后论述了白话文与文言文的优劣。他从文学的艺术、文学的功用两个方面论述了这一问题。他认为“所谓文学的艺术谓如何陶铸文学的美感是也”。“就文学艺术言之,白话文,艺术破产之文学。吾人须知文学有二重生命,即:(一)真实之情感,(二)艺术之方式。文学之价值不贵其能表情达意,而贵其能以艺术之方式表情达意耳。”他认为胡适等人的新文学主张完全忽略了文学之固有的表达方式:“胡氏之主张‘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赤裸裸表现出情感来’,盖人知有真实之情感,而不知须有艺术之方式也。夫如是,则世间又何贵乎有艺术,又何贵乎有文学家?噫!此今日白话文学界之所以滥欤”。而文言则讲究法度格律声调这些艺术手法,因而能使文章能够“惬于章法,精于词彩,畅于韵味,而妙于感觉也。故旧文学在文艺上之优点,即为能简法雅驯,堂皇富丽,及整齐谐和,微婉蕴藉之风致”。从文学的功用来讲,易峻亦认为旧文学胜过新文学。他说:“论文学的表现作用,吾人以为文言有一优点,即以其历史根源之深厚,词品极丰富,措辞造句,可得心应手,左右逢源。白话文虽以其组织之自由,容易骋其奥衍曲折之致,然既非所以语于文学全部精神,亦非即以此可以压倒文言文者。吾人以为在语言,词品枯涩,字义浅泛,只便于描写日常生活之云谓动作。至少吾人一切幽微要涉之情感意志,则殊非日常平易直率之话词所能因应无穷,而必赖此繁复柔韧富满充盈之文词,以委曲达之。今白话文之所以成文,仍赖有文言词品为之供应耳。”他的结论是文言的表述能力要超过白话。最后,他总结说:“白话文在文学的艺术与功用方面,俱无健全的理论与基础,而文言文方面,却有坚实的壁垒与深厚的根源。”“文言文为能表现艺术而亦能便利功用之文学,有数千年历史根基深厚之巩固,有四百兆民族文物同轨之要求,有须与吾民族之生存同其久远之价值”;“白话文则为艺术破产而功用不全之文学,只能为文学一部分应用工具,只能于文学某种意义上有其革新之价值,只能视为文学的时代发展中之一种产物,绝不能认为文学上革命进行的一代‘鼎革’,而遂欲根本推翻文言,举此以统一中国文学界”。总之,易峻认为,无论是从艺术的角度还是功用的角度,文言文都较白话文有更大的优越性,因此,文言文绝对不能废除,并且还要在文学领域发挥主导的作用。
以上我们从整体上对学衡派的文学思想进行了考察,可以看出,他们架构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文学理论体系,主张文学反映情感、人生、人性,同时又认为文学作品中所描写的情感、人性和人生都应当是有选择、有节制、常态的和向上的,作者应当努力地去体现情感、人性和人生中的善和美,而不能趋于极端,散漫无际,无节制地暴露人生、人性中放纵和丑恶的一面。他们非常注重文学的形式之美,认为文学创作必须符合一定的标准和程式法则,只有这样,才能凝练出一种精致与和谐之美。不难看出,学衡派所主张的是一种古典主义的文学理论。事实上,学衡派应该被认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流派古典主义(或是新古典主义)的开创者。正是他们从西方引入了完整的古典主义的文学理论,并以此为指导进行了一系列的文学批评活动,同时开始尝试进行古典主义的文学创作。然而,他们的这一贡献在文学史上几乎被有意无意地遗忘了。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他们被长期地贴着“保守”、“顽固”、“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言人”这样的政治标签,他们的贡献便为人所讳言。另外,学衡派的文学创作尤其是小说创作的实绩不佳,作品很少,更谈不上有经典意义的作品。这使得他们的影响大大降低。李怡先生对此有比较精到的研究,他说:“学贯中西、义理圆融的‘学衡派’所阐述的理论更像是对于文学现象的宏观的整体的认识,它更接近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学理论或文学批评的范畴——它是自成体系、自圆其说的,但与文学创作的实际状况却比较隔膜。考察‘学衡派’诸人之于文学的关系,我们就会发现,在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之间,他们都显然更长于前者”,“(他们的)创作都没有从根本上走出传统文学的大格局。这并不是说遵从传统的创作路数就没有前途,而是说正因为中国古典文学已经取得巨大的成就,并且在客观上成为屹立在后来者前进之途上的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所以平心而论,传统的辉煌事实上大大地降低了‘学衡派’诸人的创作分量”。“更重要的是‘学衡派’对于他们所批评的五四新文学的创作思路实际上是相当陌生的,这种陌生使得他们的文学主张没有能够获得丰富的新文学创作现象的支持,他们的文学思想只是部分反映了他们所掌握的西方文学知识和远非独到的旧体文学的创作经验。”可以说,他们创作中存在的严重缺陷使他们的文学理论没有产生应有的影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新古典主义的开创之功就应该被抹杀和遗忘。事实上,他们的理论宣传被另一位新古典主义文学大家梁实秋发扬光大。梁实秋很推崇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1928年,他与吴宓联系,将《学衡》杂志上发表的有关新人文主义理论的文章结集出版。他在序言中说:“白璧德的学说我以为是稳健、严正,在如今这个混乱的浪漫的时代是格外有他的价值,而在目前的中国似乎更有研究的必要。”此举对古典主义文艺理论的弘扬可谓功不可没。此后古典主义的影响逐渐扩大,阵营日益壮大,除了梁实秋外,还有林语堂、沈从文、闻一多等,他们不仅在理论上认同古典主义,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渗透着古典主义理念的创作活动取得了非凡的成就,粱实秋等人都可称得上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巨匠。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承认。当我们在欣赏和赞美古典主义文学的成就的时候,不应该忘记学衡派在理论上的开创之功。
当历史进入到21世纪的时候,我们回头再看学衡派与新文化运动派的争论,就会发现很难说那一方取得了优胜。诚然,学衡派保留文言文的愿望已被历史事实击得粉碎,但新文化运动派文学进化观也并不完全符合文学的本质规律。以今人的眼光看来,学衡派和新文化运动派只是接受了两种不同的文学理念,这两种理念都应当是能结出丰硕的果实(历史事实也是如此),所以他们之间的关系只是互补的关系,应该能够进行对话和沟通,而不是对立和攻讦。然而历史不能假设,中国特有的文化历史传统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注定那是一个理想主义盛行的时代,形形色色的理想主义与传统遗留下来的根深蒂固的独断心理结合起来,便是对一己主张绝对的尊崇和对异己的绝对不宽容。各个派别之间共同之处就是都标榜一种令人窒息的道德理想主义。在这样的情势下,文学的功能逐渐被异化,变成鼓吹道德理想主义的工具。随着文学派别与政治斗争的结合,文学呈现出愈来愈浓的政治功利色彩。学衡派启其端的新古典主义文学尽管也带着相当浓重的道德理想主义气息,但由于他们远离了政治,他们的理想主义与政治性意识形态有比较大的距离,所以他们的文学作品少有政治功利性。这既使得他们长期地遭到主流文学派别的批判,却又使得他们的文学作品更富于文学应当具备的特质,因而更有生命力。
三、走向实证主义——学衡派的史学思想
史学研究应该是学衡派最为成功的领域,他们所取得的成就相当令人瞩目,在学衡派成员中,汤用彤、柳诒徵、缪凤林、陆懋德、张荫麟等人都是著名的史学家。而两位史学大师陈寅恪、王国维和学衡派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他们在史学领域的耕耘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为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与他们的研究实绩相应,他们史学思想也相当精深与独到,对中国现代史学的研究产生了广泛和长久的影响。
史学研究的对象毫无疑问是历史。那么历史是什么?学衡派有自己的见解。缪凤林说:“盈天地间层叠无穷流生不息之现象,生灭绵延,亘古亘今,是名日史。”柳诒徵也认为历史的范围无所不包:“历史范围无所不包,未有文字之先,地层化石动植物之寸骨片叶,皆历史也”;“广言之,充满宇宙皆历史”。可见学衡派心目中的历史之范围极为广泛,凡是在大字长宙中发生过的现象都在历史之列。这样的历史概念未免过于宽泛,在实际的历史研究中意义不大。因此学衡派更为关注的是人,认为历史的主体是人的活动:“所谓史之自体,即人类之活动。”从他们的言论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所有发生过的人类活动构成了历史的主要内容。
在这个基础上,学衡派又提出了他们的史观。他们的史观可以认为是一种生存史观,他们认为人类丰繁复杂的活动之根本动因在于人类保生、乐生的愿望。缪凤林《历史之意义与研究》一文比较完整地反映了学衡派的观点。缪凤林提出人类存在的意义在于“保生”和“乐生”。他认为欲乐恶苦为人类的天性:“凡人天性,莫不欲乐而恶苦。虽其所欲所恶,未能尽同,然所欲为乐,所恶为苦,欲欲恶恶,靡不皆然。”而得“有生之乐”是人类最普遍最根本愿望。“人性莫不欲乐恶苦,而又大抵以有生为乐也,故‘智之所贵,存我为贵’。人类一切活动,亦大抵起于保生之需要。”普通人满足于实现保生的愿望,不思进取。但也有一部分智慧之士并不以此为满足,而是更进一步,求得“乐生”:“充其欲乐之天性,不以有生之乐为已足,更进而求其乐生,用其心力从事其他之活动,思得有生以外之大乐,冒万难,忍万苦,勇猛精进,死而后已。较前之忍苦以保生,殆有过焉。”最后,缪凤林总结道:“人之活动,至此由保生而至乐生,人世之现象,遂繁复而不可究诘。是则宗教也,美术也,政治也,经济也,学术也,伦理也,皆人类之活动,起于保生乐生之避苦求乐之需要者也。人类之活动即史之自体。人类活动之意义如是,史之意义亦不外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