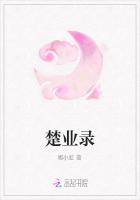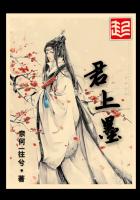今吏既亡教训于下,或不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与奸为市,贫穷孤弱,冤苦失职,甚不称陛下之意。贾谊说:夫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俗吏之所务在于刀笔筐箧,而不知大体。王吉上疏说: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礼义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独设刑以守之。其欲治者,不知所由。匡衡上疏说:
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礼让而上克暴,或忮害好陷人于罪,贪财而慕势,故犯法者众,奸邪不止,虽严刑峻法,犹不为变。东汉以后,这种责难有增无减。与此同时,酷吏则受到种种限制。首先,在升迁方面,酷吏往往因其形象不佳而失去官职。如:汉代酷吏严延年、阳球均是。其次,酷吏的罪刑擅断,日益受到法律的制约。日趋完善的封建法制,对酷吏的独断专行也是一种制约。再次,在“天人合一”的灾异谴告说影响之下,历代统治者往往因发生灾异而大赦天下。这对酷吏的肆情妄为也是一种制约。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上述种种制约因素不断扩大,造成使酷吏艰于生存和发展的社会条件。
据《史记》、《汉书》之《酷吏列传》记载,西汉的酷吏有14人:
郅都,河东杨(今山西洪洞县东南)人。景帝时任济南太守,后迁中尉,以执法严峻而被贵戚、列侯称为“苍鹰”。后任雁门太守,因得罪窦太后,被杀。
宁成,南阳穰县(今河南邓县)人。景帝时,任济南都尉,郅都死后迁中尉,效法郅都,执法严峻,为宗室、豪强所畏惧;武帝时,任内史,因罪入狱,后逃脱;后又被起用为关都尉。在济南时,时人评价“其治如狼牧羊”;而任关都尉仅一年多,出入关者竟说:“宁见乳虎,无直宁成之怒。”
周阳由,真定(今河北正定县南)人。景帝时,任郡守;武帝时,以执法“最为暴酷骄恣”而闻名。后任河东都尉时因争权被告罪,处以弃市。
赵禹,藻(音台,今陕西扶风县东南)人。景帝时,任丞相史,廉洁公平,用法深刻;武帝时,“以刀笔吏积劳”,后迁为御史、太中大夫。曾与张汤一起编定律令。
张汤,杜(今陕西西安东南)人。自幼便喜欢诉讼,随其父学习法律。初任长安吏,武帝时任太中大夫、廷尉、御史大夫等职。曾与赵禹编定律令。其断狱,对诸侯、贵族、豪强、富商大贾用法严峻深刻,开“腹诽”治罪之先河,曾主持审理陈皇后“巫蛊狱”及淮南王、衡山王、江都王谋反等重大案件,株连甚多。但对平民犯罪,处刑尚宽。后遭陷害,自杀。
义纵,河东(治所在今山西夏县西北禹王城)人。武帝时,任长陵、长安令,执法严峻,不避权贵。后迁为河内都尉,族灭其豪强穰氏之属。为定襄太守时,将郡狱中重罪、轻罪囚犯二百余人及私自入狱探视的犯人亲属等二百余人,以策划越狱的罪名上报朝廷,全部处死刑;后为右内史,因阻挠“告缗令”(奖励告发逃避资产税,打击富商大贾的法令),被处以弃市。
王温舒,阳陵(今陕西成阳市东北)人。武帝时,任御史、广平都尉、河内太守、中尉、少府、右内史等职。善督盗贼,杀伤甚多,尤其打击豪强酷烈。后因隐匿其属吏,并有人告其受赃枉法,被处以族刑,自杀。
尹齐,茌平(今山东茌平县西南)人。武帝时,任御史,关内都尉、中尉,善督盗贼,执法不避贵戚,名声甚于宁成。
杨仆,宜阳(今河南宜阳县西)人。景帝时,任御史,善督盗贼。后迁主爵都尉,拜楼船将军,封将梁侯。率军出征朝鲜,因兵败有罪,免为庶人。后病死。
减宣,河东杨(今山西洪洞县东南)人。武帝时,任御史及中丞,治主父偃及淮南王谋反案,用法严酷,果断决疑,杀者甚众。后为左内史、右扶风。因大逆罪,当处族刑,自杀。
杜周,南阳杜衍(今河南南阳市西南)人。武帝时,任御史、中丞、廷尉、执金吾、御史大夫。善于审理,用法深刻至骨,以皇帝意旨为狱,专门负责审理诏狱。以“暴酷”而甚于王温舒等酷吏。“其治大放张汤而善候伺”。
田广明,字子公,郑(今陕西华县)人。武帝时,河南都尉、淮阳太守,因破公孙勇、胡倩谋反案立功,徵人为大鸿胪;宣帝时,因罪自杀。
田延年,字子宾,其祖上为战国齐国田氏,汉初迁至阳陵(今陕西咸阳市东北)。武帝时,任河东太守,因打击豪强得力而选人大司农。昭帝病危时,茂陵富商焦氏、贾氏用数千万钱购买丧葬用品囤积牟取暴利。宣帝即位后,大司农田延年奏请处理此事。因此受损失的富商大为怨恨,出钱刺探田延年的违法行为,并上告田延年主守藏赃,犯有“不道”罪。朝廷下诏审理此案,田延年闻讯自杀。
严延年,字次卿,东海下邳(今江苏邳县南)人。自幼随父学习法律。宣帝时,任涿郡太守,以严刑酷罚镇压豪强东高氏、西高氏;后任河南郡守,对豪强施以酷罚,诛杀甚多,被称为“屠伯”。后因诽谤朝廷罪被处以死刑。
《后汉书·酷吏列传》所记载东汉的酷吏有7人:董宣、樊哗、李章、周绔、黄昌、阳球、王吉。
《魏书·酷吏列传》记载北魏酷吏有9人:于洛侯、胡泥、李洪之、高遵、张赦提、羊祉、崔暹、郦道元、谷楷。
《北齐书·酷吏列传》记载北齐的酷吏有4人:邸珍、宋游道、卢斐、毕义云。
《隋书·酷吏列传》记载隋的酷吏有8人:厍狄士文、田式、燕荣、赵仲卿、崔弘度、崔弘升、元弘嗣、王文同。
《旧唐书》、《新唐书》之《酷吏列传》记载唐的酷吏有24人:来俊臣、周兴、傅游艺、丘神勃、索元礼、侯思止、万国俊、来子殉、王弘义、郭(弘)霸、吉顼、姚绍之、周利贞、王旭、吉温、王钧、严安之、卢铉附、罗希、崔器、毛若虚、敬羽、裴升、毕曜附。
《金史·酷吏列传》记载金的酷吏有2人:高闾山、蒲察合住。
五 法家精神与严于吏治
官吏是履行国家职能的重要工具。一个国家的吏治如何,直接影响到这个国家的统治效能。因此,先秦法家一直比较重视对官吏的治理。其根本原因就是,在战国初期,新兴地主阶级完成夺取政权的任务之后,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日益突出。与民众相比,官吏对君主地位的影响更直接、更具威胁性。如何巩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成为摆在法家面前的首要问题。申不害开始探索君臣关系,并提出了“术治”说。到韩非那里,发展成“明主治吏不治民”的著名论断,并将“法”、“势”、“术”结合,提出了一套具体的治吏方法。
韩非将君臣关系列于首要地位,主张“法”是君主“制臣”的有效工具,而“治吏”、“禁奸”则是“法“的主要内容。认为,君臣之间是一种“一日百战”的对立关系,同时君主也离不开臣的辅助而共同统治民众。君主对民众的统治必须通过官吏来进行,因而官吏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君主的利益,“治吏”比“治民”也就显得更迫切、更重要。由此,提出了“明主治吏不治民”的著名论断,强调“法”的作用是“治吏”。
法家严于吏治的精神,自秦开始一直贯穿于历代封建立法之中。秦统治者以法治吏,通过治吏而治民。秦律从封建官僚体制建立始,就十分重视吏治,要求官吏首先必须懂法,并以之作为划分“良吏”、“恶吏”的标准。从《睡虎地秦墓竹简》来看,秦律大都是针对官吏制定的。如:有“不胜任”、“不廉”、“纵囚”、“不直”、“失刑”等具体的罪名,还有“犯令”、“废令”罪名。秦律中有大量的针对官吏的禁止性规范和命令性规范,其中大多没有具体罪名,而是以“犯令”、“废令”罪统称;违犯禁止性规范的以“犯令”罪论处,违犯命令性规范的以“废令”罪论处。此外,还规定了专门适用于官吏的刑罚原则:
一是责任惩罚制原则。即在同一官府任职的官吏,各自承担其所主管方面的罪责。惩罚的根基是官吏所负的责任,无责任不惩罚。这一原则的根据是秦实行的官吏责任制、官吏考核制,以法律的形式将各级、各部门官吏的职权、职责固定下来,要求官吏各行其职、各负其责,并定期检查,予以奖惩。
二是“追诉时效”原则。即官吏免职或调任后,如对其在职时所犯的罪或对其下属犯罪负有责任,则该官不能因免职或调任而逃脱刑事制裁。简言之,对官吏犯罪的追诉期限不受其在职(犯罪时所居之职)与否限制,只要活着,就追究其刑事责任。
秦汉以后的律典继承并发展了秦律严于吏治的立法精神,设专篇规定官吏职司。如:西晋时,《晋律》有《违制》篇,北齐沿用;隋《开皇律》则改为《职制》篇,唐、宋律沿用。《职制》律的内容是有关官吏超编,贡举非其人,玩忽职守,泄漏机密,奏事犯讳,制书有误,指斥乘舆,贪赃枉法,等等。明朝则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一方面,明初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六部直属皇帝统领,以适应高度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发展的需要。为此,《大明律》一改唐律的体例,仿《元典章》以六部官制编目:《名例》、《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工律》。其中,《吏律》2卷,分为“职制”15条、“公式”18条,这为清朝律典所承用。另一方面,朱元璋“刑乱国用重典”的立法指导思想中包括“治吏”、“治民”,首要的是“治吏”。“治吏”不仅是为了维护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更好地发挥官僚机构的统治效能,而且也是为了更有效地“治民”。为此,朱元璋亲自指导编定了《大诰》,其突出特点之一就是强调重典治吏:一是《大诰》所列举的各种案件中,80%以上是惩治官吏的;以《大诰续编》为例,共87条,属于打击官吏贪污和豪强作恶的案件就占了约70条。二是朱元璋所作的《训导》,绝大多数也是针对官吏而发的。三是以法外用刑、轻罪重判的原则,惩治官吏犯罪。
先秦法家严于吏治的精神还被后世的封建改革家所继承、发展,最典型者就是北宋的王安石、明代的张居正。
任贤使能,加强吏治。这是王安石法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历了变法实践的王安石深切地认识到,要实现天下大治,必须依靠两种办法:一是“大明法度”,即废除旧法、弊法,创立新法、善法;二是“众建贤才”,即汰除守旧、平庸之吏,起用进取有为之士。前者固然是变法改革的当务之急,但只有善法不足以治理好国家,还必须有好的执法官吏贯彻执行善法。因此,官吏能否守法、执法,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危。所以,王安石极力主张运用法制手段选拔、任用官吏。
(1)“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绩之法”
王安石认为,当时在选拔、任用官吏方面,存在着两大弊端:一是不重视真才实学,二是任官“不久于其任”。针对前者,他反对以短时间的考试取人,也反对不问能力只看资历,更反对变相的世袭制;主张以考试和推荐相结合的办法,选拔有真才实学的官吏。针对后者,主张任官“久于其任”,只有这样,才能获得专业技能,做好本职工作。在这个基础上,再用“考绩之法”对官吏进行考核,胜任者留,有功者升,不胜任者辞退。
(2)设“明法科”,培养执法官吏
王安石认为,当时审判质量差的原因就是科举制度无“明法科”。因此,建议恢复“明法科”,以律令、《刑统》大义和断案作为考试的内容,考试合格者才能充任司法官吏;凡已参加进士和诸科考试被录取者,必须再参加律令、大义和断案考试,合格者才委派官职;经“明法科”考试合格者,其名次在及第进士之上,以示褒奖。这一措施冲击了传统的旧观念。因为“昔试刑者,世皆指为俗吏”,“旧明法最为下科”,汉代“律学在六学之一,后来缙绅多耻此学,旧明法科徒诵其文,罕通其意”。从历史上来看,如此重视法律教育,并与官吏选拔任免制度合为一体,仅王安石一例。
整饬吏治,不仅是明代政治家张居正推行改革的有力措施之一,而且也是其法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执法与坏法的关键在于官吏。长期以来,“当国者政以贿成,吏脸民膏以媚权门”。这不仅造成了大批冗官,加重了财政开支,而且大大降低了行政效率。因此,主张严格官吏考核之法,严明黜陟,全面考察官吏的功过是非,使赏功罚过名副其实。为此,万历元年(1573年),张居正实行“考成法”,规定:各级官吏必须贯彻执行诏令,并定期向内阁报告执行的情况;考课分三等:称职、平常、不称职。在选拔人才上,要求不务虚名,不拘资格,全面审核,以政绩为标准。
六 法家精神与律学传统
春秋末期,法家先驱邓析首创“刑名之学”,其内容就是后来《商君书·定分》所说的“法令之所谓”。战国时期的法家代表人物,如商鞅、申不害、韩非,皆好“刑名之学”或“刑名法术之学”,将名学理论运用于法律实践及法学研究,从而为中国古代法学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并为后来律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从实践出发,注重法律的操作性,即围绕如何定罪量刑等刑法问题进行探讨,注重法律概念、名词的精确解释及命题的逻辑论证,进而形成中国古代律学的传统——法律注释学。这种法律注释学的学风,在战国时期促进了“百家争鸣”的古代法学的形成,但在秦“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文化专制主义政策之下,这种学术活动已经毫无民间的自由色彩,而一概由官方垄断。1975年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法律答问》就是秦官方刑名之学集大成的代表作。《法律答问》共有简210支,内容187条,多采用问答形式,对秦律某些条文、术语以及律文的意图作出明确解释。精练、准确的文字表现了其价值。从其内容范围来看,所解释的是秦律的主体部分,即刑法。
一般认为,律学研究兴起于汉代。程树德《九朝律考·汉律考·律家考》所列汉代律家有:萧何、叔孙通、张苍、董仲舒、贾谊、吴公、张叔、晁错、张恢、宋孟、刘带、张汤、赵禹、杜周、杜延年、公孙弘、韩安国、田生、于公、于定国、路温舒、郑宾、郑昌、郑弘、黄霸、严延年、孔光、陈汤、丙吉、薛宣、尹翁归、何比干、弘恭、石显、王禁、淮阳宪王钦、赵敬肃王彭祖、广陵思王敬、王霸、梁统、梁松、郭弘、郭躬、郭睚、郭镇、郭祯、郭僖、郭曼、郭贺、陈咸、陈宠、陈忠、王涣、吴雄、吴诉、吴恭、张禹、侯霸、陈球、钟皓、阳球、樊晔、周绔、周树、徐徵、应劭、黄昌、董昆、卢孟、荀季卿、叔孙宣、郭令聊、马融、郑玄、张皓。这些律学研究者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儒者,提倡以儒家经义作为研究律学和审理案件的理论依据。这些儒者解律实际上是将儒家学说注入律文,其中不少是牵强附会。另一类律学家多出身文吏。他们解释法律则侧重阐明条文本义,探讨法律名词、术语的含义。这类律学,滥觞于西汉中期,到东汉后期已经非常盛行。这两类律学从西汉始就逐渐合流。东汉末期,私家注释法律的风气盛极一时。许多儒学大师采用研究儒家经典的章句学方法,即对《经传》分章析句以解释义理的训诂方法来注释法律,着重阐述法律条文的本义和立法本旨。因而,注家蜂起,其说各异,各自形成门户。据《晋书·刑法志》记载,其中著名者有叔孙宣、马令卿、马融、郑玄等十余家,每“家数十万言。凡断罪所当由用者,合二万六干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二干二百余言。言数益繁,览者益难”。但汉代的律学著作大都佚失,今能稽考的仅仅是西汉武帝时杜周、杜延年父子所注的“大杜律”、“小杜律”;另外,当时诸家《律说》,今见于《史记》和《汉书》注所引者尚存8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