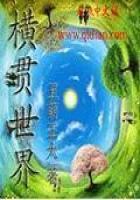魏晋时期,律学有了重大的发展。曹魏初期,针对东汉私家注律给司法审判造成的混乱现象,魏明帝下诏:各级司法官吏在审判中“但用郑氏章旬,不得杂用余家”。一纸诏书,使私家的法律注释上升到具有法律效力的官方地位,对晋影响颇大。程树德《九朝律考·魏律考·魏律家》所列曹魏律学家有:刘劭、庾嶷、荀诜、陈群、卢毓、高柔、钟繇、钟毓、钟会、王朗、卫觊、刘虞、丁仪、阮武。这时的律家开始研究法典的篇章、体例,最有成就者就是魏《新律》改汉代《具律》为《刑名》,并冠于律典之首。《九朝律考·晋律考·晋律家》所列晋律学家有:贾充、郑冲、荀勖、裴楷、成公绥、荀辉、荀颧、羊祜、王业、杜友、杜预、周权、郭颀、柳轨、荣劭、张斐、卫璀、高光、刘颂、续成、石妙、顾荣、王坦之、李充。晋是律学鼎盛的时期,律注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其标志就是出现了很多专门注释晋律的著作。其代表者有:张斐:《汉晋律序注》一卷、《杂律解》二十一卷,《律解》二十卷,等等。原书均已失传,现《晋书·刑法志》中仅存《律注要略》一篇。杜预:《刑法律本》二十一卷。张斐、杜预的律注经晋武帝批准,诏颁天下,从而与晋律视为一体,具有法律效力,至南朝时仍行,用,历时二百年,后世称之为“张杜律”。张、杜律注继承发展了先秦以来的“刑名之学”的律学传统,注重研究律典的体例结构,注意从法理上推究律文的含义,提倡运用逻辑思维,抽象概括法律名词、术语,并作出简明、确切的解释,因而成为秦汉以后“刑名之学”的杰出代表作。这些成就在唐代被现存最完整的“刑名之学”的代表作、长孙无忌的《唐律疏议》所继承,反映出中国古代律学发展的最高水平。
唐代以后,律研究虽代不乏人,但却没有大的发展。明清时期,由于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高度发展的需要,统治者非常重视法律的实际作用,通过设立讲读律例的制度,在官吏中提倡律学,要求官吏研究律学,以提高司法审判的水平。因此,这一时期,注释法律、讲读律令律学又向前发展了一大步,注释法律、讲读律令的著作多了起来。
《大明律》颁布以后,官方律注有《明律纂注》。民间为之作注者颇多。据《明史·艺文志》记载,有张楷的《大明律解》十二卷,应梗的《大明律释义》三十卷、高举的《大明律集解附例》三十卷。此外,还有王樵、王肯堂父子分别编写的《读律私笺》、《律例笺解》。
而清代大量的律学著作注重应用,王明德的《读律佩瞒(×T)》就是典型代表。大部头的注律著作有:沈之奇的《大清律例辑注》、万枫江的《大清律例集注继编》;还出现了一些简明读物,如:胡凤丹校的《读律要略》、杨荣绪的《读律提纲》、刘衡的《理论撮要》。甚至出现了用白话文和图表解释律例的通俗读物,如:志和的《大清刑律择要浅说》,邵春涛的《读法图存》。以歌诀形式出现的通俗读物:《大清律例歌诀》、《大清律七言集成》。此外,在考证、比较研究、案例汇编等方面,都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
七 法家精神与法律教育
史载,春秋末期,郑国大夫、法家先驱子产聚徒讲学,传授法律知识。这是中国法律教育史上空前之举,它开创了私人传授法律之先河。在此之前,“学在官府”,精神生产领域长期被贵族及神职人员垄断,加之法律处于秘密状态,基本谈不上法律研究,更无所谓法律教育。春秋末期之后,社会处于大变革中,教育制度也发生了变化,“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私学大兴。从此,文化教育走人民间,出现了私学传授法律知识的现象。
战国时期,在诸子百家中,力主“法治”的法家学派的法律教育最为著名,其有关法律教育的模式及精神对后世封建社会的法律教育影响最大。法家为推行“法治”,提出了“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法律教育模式和精神。所谓“以法为教”,即要求官吏、百姓都必须学习法律;所谓“以吏为师”,即私人学习法律者都要向主管法令的官吏学习,由司法官吏宣讲、解释法律。同时,法家还主张,司法官员必须由精通法律条文者担任,必须有问必答、所答必对,否则就要以其所忘记的法令之名处罚。身兼法学家、政治家双重身份的法家代表人物,将其法律教育思想、精神付诸实践,使秦国的法律教育具有“亦私亦官”的特点。结果,使“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境内之民皆言治,藏管、商之法者家有之”,有力地推动了“法治”的实施。
秦统一天下之后,采纳了法家代表人物李斯的建议,禁绝私学,“以法为教”、“以吏为师”,逐渐垄断法律教育。这种官办的唯一的文化教育——法律教育,实际上成了国家司法活动的附属物,使法律教育的内容、形式变得狭窄、单一。由于禁绝私学,使本来比较丰富的诸家法律思想成为异端,从而窒息了包括法家在内的法律思想和法律教育活动的正常发展,僵化了法律教育的灵魂。因此,秦朝的法律教育就以中央政府对各级法官的司法指导、业务培训为中心内容。秦法律教育的主要内容有:
(1)司法业务教育
秦以“明法律令”为“良吏”的必备条件,因此,十分强调提高各级法官的业务水平。中央政府对各级司法机关提出的问题,包括律文的内容、名词、术语等,均明确解释、答复,并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以供学习、掌握。1975年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之《法律答问》即是。此外,在案件的调查、勘验、审判等环节中,应注意哪些事项,如何制作法律文书等,也是业务训练的重要内容。《睡虎地秦墓竹简》之《封诊式》即是这种教材。
(2)司法道德教育
秦还注重对法官进行品行教育。如:《睡虎地秦墓竹简》之《语书》强调区分“良吏”与“恶吏”的标准不仅在于是否“明法律令”,而且还在于法官的品德。“良吏”,办事“廉洁”,出以“公心”,忠诚老实,随时纠正错误;“恶吏”,“无公端之心”,办事草率,荀且懒惰,遇事推诿,说假话,处处表现自己,喜搬弄是非。《睡虎地秦墓竹简》之《为吏之道》就是进行司法道德教育的教材。其形式为四五字一句,便于记诵。如,其中有:“审悉毋私”,“毋以忿怒决”,“毋喜富、毋恶贫”,“中信敬上”,“为人臣则忠”,“为人子则孝”等一类的道德说教。其目的是使各级司法官吏服从上级,杜绝枉法徇私。
这种贯穿“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法家精神的法律教育模式,在秦之后的历代王朝被继承发展。
汉承秦制。汉初曾下诏令:明习法律者汇集丞相府中,专门传授法律知识,令各郡县欲学法律者至京师接受专门培训。汉文帝时,蜀郡太守文翁非常重视司法官吏的培养,曾选拔十余名聪明、敏捷,且有才华的郡县小吏前往京师,“受业博士,或学法令”,学成归还,“以为右职”;并“常选学官童子,使在便坐受事”,让他们一边办公事,一边学习法律。武帝时,曾诏令地方荐举贤才,分为四科,第三科就是录取“明习法令,足以决疑”者,任为司法官吏。这就促使人们努力学习法律知识,从而推动了法律教育活动。
汉代的法律教育还别有特色。其一,随着法律知识的儒家化,出现了“春秋决狱”式的法律教育。其始作俑者董仲舒又是个大教育家,其弟子很多,有的见不着面,便采取老生教新生的教学方式,授受“春秋决狱”的审判方法。这种做法引起汉武帝的重视,武帝甚至要求自己的儿子来学习。其二,随着律学的形成发展,私家注律者收徒讲授,成为当时民间法律教育的主要形式,并且是“子继父业”。《南齐书·崔祖思传》记载:
汉末治律有家,子孙并世其业,聚徒讲授,至数百人。
如:西汉的杜周、杜延年父子,东汉的于公、于定国父子,郭弘、郭躬、郭旺等数代,世任国家的司法官员,大多官至廷尉、御史大夫。生活在这种法律世家中,晚辈可以自幼修家业,在潜移默化或有意识培养之中,得以明晓法律。
魏晋至唐宋时期,法律教育逐渐“步入正轨”。魏明帝时,为了扭转人们只重儒经,小视法律的习俗,卫觊上疏说:
九章之律,自古所传,断定刑罪,其意微妙。百里长吏,皆宜知律。刑法者,国家之所贵重,而私议之所轻贱;狱吏者,百姓之所悬命,而选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请置律博士,转相教授。
这一建议被采纳,从此,律博士成为负责培训地方司法官吏的专职官职,在官学中占有一席之地。晋时虽然在注律方面达到了最高水平,但是由于时尚清谈,以研经学律为陋,因而冷却了一般知识分子研究、学习法律知识的积极性。北魏列律博士于廷尉属官。北齐转属大理寺,其职责是参与司法审判并解答咨询、培训司法人员和教育官吏子弟。唐代的法律教育开始步入正轨,其表现是,法律教育、官学、考试制度与官吏选拔联系在一起。唐大兴学校,贞观年间,在国子监之下设律学馆,其下又设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主掌教习;招收八品以下官员子弟及平民子弟50人,年龄在18至25岁之间;学习的内容是当时的律、令、格、式,学制不超过6年。律学馆每年进行考试,及格者参加尚书省礼部的考试,再合格者得以任官;不及格者仍留馆学习,连续三年不及格者和不从师教、逾假不归者,免除学籍。唐代科举考试,由中央礼部主持,分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六科。考生为参加州县考试合格的“贡生”和中央、地方学校毕业的“生徒”。“明法”科由律学馆出题、阅卷。由于地方学校不专设律学专业,因此律学馆的学生实处近水楼台。考题有十道,其中律七道、令三道。全答对者为甲等,答对八道者为乙等。另外,吏部以身、言、书、判四项取人。身,体貌丰伟;言,言词辩正;书,楷法道美;判,文理优长,即逻辑严谨。《文苑英华》有判牍二十余卷,《白氏长庆集》也有甲、乙判,大抵为备考的范文。
宋代法律教育因袭唐制并有发展。其律学馆入学者不以品官子弟为限,各地举人也要入馆学习。学习的内容为律令、断案两项。其中律令一项还包括朝廷新颁布的法律、法令。每月“~公试”(集体考试)、“三私试”(单独考试)。结业时,学律令者考《刑统》大义五题;学断案者考案例一题,其中包括“刑名”内容的小题五至七题。合格者参加礼部的考试。宋科举考试设进士、明经、明法等科。明法的考试内容是律令40条,而经、传诸科也要“抽卷问律”。975年,进士诸科都要考试律义十道;990年,明法考试分七场,分别考律、令及六经疏议。王安石变法时,立新科明法,考试科目是律令、《刑统》大义、断案,凡没有考取进士的都可投考。应“明法”考试而被录取者,由吏部列入备用的司人员名单中,其名次在进士之上。后来又规定:凡参加进士和诸科考试而被录取者,还要参加律令、《刑统》大义、断案的考试,合格者才能委派官职。但司马光任宰相时,废除了明法新科。仁宗时,有书判拔萃科,召试长于书判者。《名公书判清明集》正是书判的楷模。
高宗建炎年间,曾一度恢复“明法科”,但不久又废。明清均未恢复。同时,明清也不设律博士、律学馆。究其原因,是明清提倡的法律教育的方法与从汉魏到唐宋采取的有所不同。汉魏以下采用的是开办培养法律人才的学校(律学),设置主管律学的官署(律博士)和开科取士(明法科及其他诸科)的办法,鼓励天下士子朝这个方向走;而明清则是通过设立讲读律令的制度,督促官吏学习法律知识。
明、清律都有一条“讲读律令”的专门规定:要求百宫必须熟读法律,讲明律意,以便剖决事务。还规定,每年年终,京内、京外各个部门的官吏都要由其上司进行考核,以督促官吏学习法律。如果发现有不能讲解、不知晓律意者,官要罚俸一个月,吏要笞四十。
明国子监学习的课目除经义外,还有《大诰》及其他法令;科举考试还考书判五道。清代的学校制度基本承袭明制,国子监及地方学校唯一涉及法律的只有《御制律学渊源》,但科举考试连书判也免了。
明清民间的法律教育方式,主要是以乡规民约及家族法规来把封建道德教化与法律教育结合起来,训导人们服从国家的法律,以平息争讼,防止犯罪,弥补国家实行以对官吏进行法律教育为主之不足。这也是明清法律教育的特点。
八 法家精神与法律艺术
所谓法律艺术,即从事立法、司法等法律实践活动的能力、技术和方法,包括立法艺术、司法艺术、法律文献管理艺术等。它们是保障立法、司法活动得以正常进行的主观条件。.在西周、春秋末期以前,法律实践活动表现出极大的分散性,立法、司法的统一,在当时诸侯割据、大夫专权、政在家门的状态下是无法实现的。同时,除了制定重大法律政策、原则和法令之外,立法与司法活动浑然为一,尚未分离。法官既是司法者又是立法者,判例成为主要的法律规范。因而,法律实践活动对法律艺术没有提出更多的要求。
但是,在战国、秦时期,立法、司法活动首先在诸侯国(后在全国)领域内被统一起来;同时,立法、司法活动成为分离的两个过程:立法机构依照法定程序制定成文法律,司法机构依照成文法律进行审判。一切活动都要严格合法、准确。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求立法者和司法者具备专门的法律技术和方法。因而这一时期,法律艺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由于法家学派代表人物利用主持变法的时机,将贯穿在其法律思想中的法家精神付之于实践,奠定了这一时期法律艺术的基础。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法律艺术贯彻并充分体现了法家精神,对汉以后的法律艺术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归纳起来,战国、秦的法律艺术是:
立法艺术
包括立法组织与程序、法律规范的表达方法两方面。国君与重要大臣共同讨论重大立法问题已成常规;君臣共议立法事宜而由君主最后裁决,是当时立法的既定模式。法律规范的技术要求主要有两项,一是要求“明白易知”,二是要简练、准确。
司法艺术
包括审判方法、司法勘验技术和法律咨询。关于审判方法主要有两点要求:一是在审讯中,凡能根据被告人的口供发现破绽、线索进行追查而不刑讯逼供就能查清案情的,是上策;刑讯获得真情的,是下策。二是审讯被告,必须听完其陈述并记录下来,即使发现说谎也不能随时反驳;陈述完毕后再发问,然后再听其陈述,以发现其中的矛盾。这样被告难于自圆其说,理屈词穷,就会说出真情。
《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之《贼死》、《经死》、《穴盗》、《出子》是迄今为止所见最早的刑事勘查记录。从这些法律文件可知,秦的司法勘查制度已初具规模。案发后,要求司法人员立即赶到现场,搜取物证,询问证人,尽量详尽地掌握现场情况并记录下来。从《封诊式》来看,秦司法人员已经掌握了比较丰富的司法检验技术。对“经死”(自缢)案件,不仅注意区别自杀、他杀,而且还总结了一套鉴别方法。如:舌不吐出、颈部无血、头部不能从绳套中脱出,这些可能是他杀的迹象。还对斗殴致使妇女流产案、麻风病等总结出一套检验方法。这种检验技术虽然不尽科学,但却是长期实践的总结。这些知识、技术被后世继承并发展,形成了中国古代法医学的繁荣。法律咨询技术也比较成熟,法官的职责之一是回答臣民的法律询问,有关内容要写在左右券上;左券给询问者,右券由法官收藏。
法律文件管理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