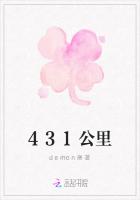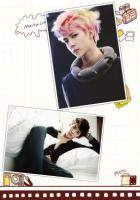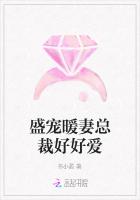法家的“法治”是一种治国理论、治国方略,是针对当时儒家的“人治”提出来的。法家强调,国家的治乱与兴衰,关键不在于君主是否英明,而在于法律制度的有无与好坏;只要“以法治国”,就能治理好国家。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法家主张公布法律,强调“刑无等级”,要求“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法家的“法治”主张代表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反映了要求改革的希望,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可以说,法律作为一种调整社会关系的工具,“法治”作为一种治国的方法,是法家“法治”理论的实质内涵,也是人类文化遗产的精华。因而汉代以后,虽然历代封建统治者绝口不提“法治”二字,但在实践中,继承并贯彻了“法治”思想的实质内涵,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西汉文景之治、唐初贞观之治,都与法家“法治”思想有很大的关系。当然,由于法家所提倡的“法治”与封建君主专制联系在一起,因此,在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国家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建立。
先秦法家的“法治”思想甚至影响到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主义中国。中国的法学界曾在1979年至1982年间,对“法治”与“人治”问题展开了一场学术争鸣。主要观点有:“法治论”、“结合论”、“取消论”。“法治论”认为,依法治国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主要应依靠建立一个完善的法律制度,并加以贯彻实施,作为一种治国原则,要求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都必须严格依法办事。从某种意义上讲,发生于改革开放之初的这场争鸣,实际上是中国历史上关于“法治”、“人治”争论的继续,其实质是探讨:权大?还是法大?可以说,这是在理论上对两千年来封建君主专制及其影响所作的一次总清算。时至今日,这场争鸣已经有了结果。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作为战略目标加以规定。这表明,“法治”作为一种治理国家的方法,法律作为一种调整社会关系的工具,是没有阶级性的,封建社会可以用,资本主义社会可以用,社会主义社会也可以用。
(4)严于吏治的精神
法家代表人物都强调整饬“吏治”,并以之作为推行“法治”的保障。要求官吏“德才”兼备,既要有公正、清廉、审慎的品行,又要具备良好的业务素质;同时主张建立一套监察制度,制定监督、管理官吏的一系列法律措施,要求官吏严于律己、不避权贵、严格执法。秦汉以后的历代封建统治者都认识到“徒法不能以自行”,重视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执法队伍,培养所谓的“清官”,并用法律将“治吏”制度化。隋唐以后,甄选官吏的科举考试制有了很大发展,并对西方近代的文官制度产生了启发式的影响。
2.先秦法家法律文化的劣性遗产
(1)极端的君主专制主义
法家代表人物强调君主专制,尤其是后期法家代表将其极端化。君主掌握国家一切权力,甚至凌驾于国家之上,以“法”、“势”、“术”来控制封建官僚机构,以“尊君”来构建封建等级,法律则成为公开的等级的法律。秦始皇将法家的君主专制理论极端化、法制化,形成了“朕即国家”、“一家之法”的皇权主义。从此,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中国两千年,造成皇权至上,个人的权利和义务观念模糊,缺乏民主传统,派生出各级大贵族、大官僚以及宦官、外戚等各种法定的、习惯的、法外的、非法的等级特权,最终在国民意识中形成权大于法的权力本位思想。封建的君主专制政体及皇权主义思想扼杀了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一丝活力,使王朝失去了自身变革的契机,从而无可避免地招致改朝换代的暴风骤雨。1912年,封建专制王朝被推翻,但其流毒一直在阻碍中国法制近代化的进程。
(2)极端的重刑主义
法家以“专任刑罚”而著称,主张以严刑峻罚来推动“富国强兵”政策的实施,刑罚的最终目的就是消除法律。把法律特别是刑法的作用夸大到决定一切的高度,轻视甚至完全否定道德感化作用。《商君书·禁令》说:“以刑去刑,刑去事成。”因而,法家主张轻罪重罚,后期法家甚至将“法治”发展成为极端的“刑治”,其表现就是为政太急,役民过酷。这是法家理论的致命弱点。秦王朝将这一致命弱点发展得淋漓尽致,最后导致秦帝国的灭亡。以致后来在人们的心目中,法与暴政、严刑酷罚相联系,“法治”就是暴政的标志。不难理解,要维护一个公开不平等的专制特权制度,除了严酷的刑罚手段之外,还会有什么更好的措施?因此,秦汉以后历朝,在建国之初,刑罚还比较宽平,中后期往往酷刑泛滥。重刑主义发展的结果就是重刑轻民:一是重视刑法而轻视民法,一是重视刑事审判而轻视民事审判。虽然中国古代刑法发展的总趋势是从野蛮至文明,但从整体而言,其刑网之繁苛,刑罚之酷烈,是举世皆知的。历代酷吏虽不乏“不避权贵”的气度,但毕竟以典刑深刻而著称于世;纠举式的审判,重口供的偏见,残酷的刑讯,造成多少冤魂;贪婪的胥吏,污秽的狱政,又使多少无辜者法外受诛。官府衙门居高临下的专横气势,使当事人望而生畏;无休止的审判,无止境的勒索,在百姓心中铸起一句格言:“屈死不打官司。”
(3)文化专制主义
为了推行“法治”,法家要求统一思想、统一认识,“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一切与体现新兴地主阶级意志的“法”不合的仁义道德、诗、书、礼、乐都必须禁止。结果,从商鞅的“燔诗书”到秦始皇、李斯的“焚书坑儒”,其目的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实行集权专制主义,禁止私学,取缔民间的学术与教育活动。战国时期繁荣的古代法学也因此而一蹶不振,从而窒息了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发展。
3.先秦法家法律文化的中性遗产
(1)立足于社会总体利益的“集体本位”精神
“本位”,即具有实际支配价值的基本原则。在法律实践活动中,“本位”的意义在于如何确认和维护某种特定的社会秩序,并在此前提下,塑造人们的权利与义务。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总体精神一样,法家法律文化中也体现着“集体本位”的精神。简言之,在确认社会总体利益的前提之下,来规定一般个人的权利和义务,而不是从确认个人的权利义务出发,来维护某种社会秩序。在这种精神的指导下,中国古代社会从战国时期开始直至明清,一直是集权专制政体与宗法家族结构相结合的“国”、“家”集体本位。这一社会结构的存在,使得任何时代的统治者都深切认识到,家族是国家政权的社会基础,国家是家族的扩大,个人则是家族的缩影。在这样一种“国”、“家”“集体本位”的精神下,常常忽视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个人既是家族成员,又是国家臣民,必须尽双重义务。特别是在商品经济萌芽的封建社会后期,“集体本位”的道德与法律严重阻碍了商品经济的正常发展,延缓了社会前进的速度。这种“集体本位”实质上是单向的,是剥夺绝大多数人的权利而维护极少数人的利益。但是,其中并非没有可资借鉴的“合理内核”。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它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产物,并反过来维系中华民族的团结与统一,特别是当民族危难之际,“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等“精忠报国”的豪情壮志,曾深深地打动每一个人,并激励社会全体成员义无反顾地为民族捐躯。同时,其中体现了“集体”重于“个人”的价值观。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矛盾时,只能克己奉公。这种道德观念,一旦移植到今天的社会生活中,就一定会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对于抵制极端的个人主义的侵袭,激励人们主人翁的自豪感,遏制种种不良风气,将发挥二定的作用。
(2)建立完备的法律设施
法律设施是保障法律活动得以正常进行的客观条件,是国家为实现法制,指导法律活动而建立的一系列专门工作机构的总和。没有法律设施,法律规范既不能产生,也不能实施。
法家出于对立法、司法的审慎与重视,非常重视法律设施的建设。为了更好地推行“法治”,在战国时期的变法实践中,就开始建立立法特别是司法的专门机构。当时,各诸侯国都相继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司法组织。如:秦有廷尉,楚有廷理,齐有大理,魏有司寇;地方审判则由郡、县行政组织兼理。秦统一天下之后,统一了立法、司法机构。皇帝掌握最高立法、司法审判权。下有廷尉为最高司法审判机构,负责审理皇帝诏令审理的案件或地方的重大疑难案件;地方司法审判由郡守、县令兼理,负责审理管辖区域内的一般案件;县以下乡设有啬夫、三老及游徼等,可直接处理简单的纠纷。并且法律设施日趋完备,除立法、司法之外,还设有监察、考核、监狱、法律教育、法律宣传、法律文献管理等专门机构。汉以后的法律设施基本上是在秦的基础上发展完善起来的。其设施之完备,运行之精密,在世界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3)有关法律艺术的思想和实践
法律艺术是法律文化中最具有连续性和适用性的因素,包括立法艺术、司法艺术和法律文献管理艺术。立法艺术是国家制定、认可、颁布法律的技术和方法,包括立法机构的组织及其工作程序,立法指导原则,立法实际的判断与选择,法律颁布的方式,法律规范的题材或样式,法律规范的表达方法,立法解释艺术等内容。司法艺术是法律专门机构实施法律的方法和技术,包括司法机构的设置与协调,审判艺术,证据检验与法医检验技术,法条适用、判例适用和法律意识适用艺术,司法解释艺术,调解艺术,狱政管理艺术等内容。法律文献管理艺术指保存、整理法律文献资料的方法与技术,它与立法艺术、司法艺术是密不可分的。
中国古代法律艺术十分发达,主要原因有三:第一,中国古代社会史连绵数千年而未曾断绝,使法律艺术具有一个传播、继承、发展的稳定环境;第二,法家法律思想和法律实践中朴素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因素和无神论精神,使法律艺术得到较为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指导;第三,中国所独有的“混合法”(即成文法、判例法体系)对法律艺术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并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
法家关于法律艺术的思想的来源有两个:一是春秋以前法律艺术的积累、总结,一是战国时期法律艺术的实践。
《管子》、《商君书》和《韩非子》保留了法家有关法律艺术的思想,如:关于立法、司法、法律宣传教育、法律解释、法官培养等丰富内容,前面已经阐述。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之《封诊式》则保留了法家法律艺术实践的信息,如:“治狱能以书从迹其言毋笞掠而得人情为上”的审判精神,犯罪现场勘验和文书制作制度,关于“贼死”、“经死”、“穴盗”、“出子”案的勘验方法,等等。法家有关法律艺术的思想和实践,奠定了中国古代法律艺术的基础,使得中国古代的法律艺术目臻成熟,对世界法律艺术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今天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仍然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