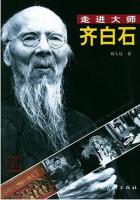姜妙仪向来罢朝罢的利落,那日发了脾气以后便三天接着不曾上朝,正伏在栏杆上拿手拂着冰凉的湖水,女官南竹同她说过了云昭郡主回宫,再捧着卷说三月中旬的祭祀事宜。
“穆哥哥在青山过的可好?”
姜妙仪下颌枕在手臂上听南竹说了半晌,忽然冒出一句没头没尾的话。“青山比燕都许是要冷的。”
南竹并无异色,从善如流道:“穆王在青山修养,有傅太医在调理,身子已是好上许多。”姜妙仪颌首,“那便在青山多留两日。”南竹应了是,拿朱笔在卷上添了字。“那朝臣…陆相可要随同?”
姜妙仪抿了抿唇,“不要了。”
南竹觑了她一眼,拿笔记下。正好瞧见弗荷越过长廊走近,南竹瞧着她脸色忐忑,猜着多半又是陆朝。果不其然,只听弗荷道:“陛下,丞相请见。”
姜妙仪拿绣帕搽了搽手,瞧也没瞧弗荷一眼,悠悠吐出两字:“不见。”
弗荷小脸皱成一团,“是。”南竹挑眉,示意她快走。
回燕绥宫时,还是瞧见了陆朝,身体颀长,站在殿前,一身银白的官服,日头不烈,光柔柔洒在他的身侧,真是清冷好看,姜妙仪想。她停了停步,却只是看了他一眼,什么都不曾说,兀自拾裙上阶。
“陛下
。”
姜妙仪走的极快,大抵是怕她回头,瞧见陆朝那张脸,又没了脾气。回宫后南竹替她点了一盏安眠的香,姜妙仪散了发髻在寝殿睡的沉沉,她睡的轻,内殿一向没人服侍。醒来时胸口沉闷,又是她们。
鲜血和他们的脸不停的在她眼前转换,姜妙仪无意识的蜷着身子在锦被下,她怕,但她只能咬着唇,死死的抑制住喉咙里发出的哭声。南竹好像是听见她醒了,从外殿进来撩起帐幔:“陛下?”
姜妙仪把脸埋在锦被里,闷闷应道,“恩。”
南竹没听出异常,用金钩将帐幔勾住,问道:“陆相还在宫前候着…您果真不见见嘛?”
姜妙仪沉吟了半晌,“让他进来。”
南竹应声去了,陆朝进来时姜妙仪半坐在榻,鸦发未挽,只隔着一方珠帘,这场景常见,只是姜妙仪此次却没打算撩帘出来。陆朝行礼时声线比往常来的柔:“陛下大安。”
“免。”
声线沙哑,陆朝愣了愣,“怎么了?”出口即知失言。姜妙仪对他那句话恍若未闻,只道。“政务不胜其扰,陆卿竟仍有闲暇。”
身后响起珠帘被人掠动的清脆声响,陆朝清淡的声线近在咫尺,姜妙仪的身体倏然僵硬,听见他低低道:“你若不愿我依了你便是。”姜妙仪本是侧对他,这下只好扭头看着他,一双眸还噙着水色,大抵是方起,整个人气场瞧着极为温和,这样看着面上笑意更为刺眼:“那我该谢丞相大恩了。”
她鲜少这样带刺,陆朝知晓她动气,却始终摸不清哪里触了她的逆鳞。
“你为何呢?”
明明知晓他不是这样想的,对何人都是温柔缱绻的样子,唯独对他,满目虚假满身戾气。
“朕乏了。”姜妙仪避开他的眼神,“陆相意欲何为尽随你心意,朕的意见向来不重要不是么。”
陆朝深深看着她,以前的姜妙仪不是这样的,她总是笑的很甜,眼眸弯弯的,像是被满足的孩童。如今的她,出落的愈发娇娆,也愈发的让人看不透。他心里空落落的,可到底没说出来,只吐出三个字。“臣告退。”
其实他们,都是最懦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