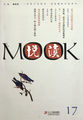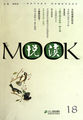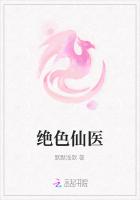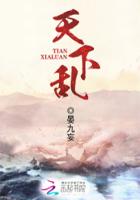虽然也殚精竭虑,但是因为未能真正走到农民的生活中去,所谓乡村建设,便成了社会精英“自己感动自己”却不能运动农民的事业。而国民党的军队花了几年时间,费了千辛万苦,最后不得不借着通公路、装电话、修筑如来螺发一样密集的碉堡才得以肃清“匪区”,随之而来的乡村建设却没有回答与解决一个重要问题,即为什么当年会有那么多农民甘愿为几亩土地冒死一战。
“几十万弟兄的尸骨,仅换来一个地归原主”
1934年,国民党要员彭学沛到江西考察,发现江西的农村到处是碉堡:“如同在巴黎到处看见裸体雕像一样,山顶不消说,只要是一个丘小冈,上面也有一个碉堡……碉堡有些是军队构筑的,有些是民众构筑的,有些是土匪构筑的,每碉上必有标语,远远便可以望到,异常显明,如果商店公司利用来贴广告,真可有意想不到的效力。”(彭学沛《江西农村匪区视察记》,《游客话江西》)小小细节,即可见当年战事之紧张。
从1934年开始,国民政府开始在江西大张旗鼓搞乡村建设实验,有人说也许正是因祸得福,这里的农民不再被漠视。在共产党被驱出以后,地方政府的首要工作便是对农村加以救济和援助。然而,这些农民并没有得偿心愿。
三年后,《大公报》记者徐盈自江西发回特别报道,文章以考茨基论法国大革命的一句话开篇:“不管加诸这些城市分子身上的压迫是如何强暴有力,但比之农民情况总要差胜一筹。”而该文前言标题即为“可怜的农民”。尽管在董时进的农业院等机构的支持下,因为引进稻种使粮食产量有大幅提高,但江西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并没有解决,那就是土地问题。农民抱怨:你改良了种子,培育了树苗,可我们“良种无田”、“种树无山”。
文章直指土地问题的重要性:“‘打土豪,分田地’一个口号便是使共党在江西盘踞了六年的主因。而事实上,也是在土地问题愈严重的地方,共党统治的时间也最久。”徐盈据此分析,“对于土地问题的真相加以曲解固然不正确,而忽视土地问题的严重性的学者们尤不可宽恕”。就在此前,南京地政学院的研究员在调查完江西土地问题后曾经大声疾呼“时机不可错过”,正好利用这个区域做一个“平均地权”的实验。孰料时光流水匆匆过,这个问题因搁置而被淡忘。更令人担忧的现实问题是:“为什么佃农一天天的多起来?为什么匪后的土地相当集中起来?”
红军撤退后,熊式辉注意到,“当时黎川农民分得田地之后,竟有私自向逃亡在外县之地主纳租金者,而广昌田地分配之后,仍各耕其原有之田,而对于新得之田,多置之不耕”,原因是中国“土地制度根深蒂固,所有权的观念等于天经地义,一旦无条件的夺他人之田地据为己有,良心终觉不安。”(熊式辉,《海桑集》)然而,他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农民心觉不安,并不能代表他们不想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
回顾历史,当初国民政府根据蒋介石的要求制定了土地条例,主旨不外乎四项:“地归原主”、“保留其使用权”、“计口授田”及“征土地累进税”。前两项旨在稳定当时的紊乱状态,而后两项则为“平均地权”起步。不幸的是,国民政府之居安思危用错了地方,“平均地权”的想法很快打了水漂。虽然技术人员们殚精竭虑,改良了种子,培育了树苗;可农民说:我们“良种无田”、“种树无山”。
徐盈由此感慨,“我们很同情主持土地整理的负责人的苦衷,可是更承认某军官的激奋:‘几十万弟兄的尸骨,仅换来一个地归原主’是一句血泪语……若是仅以扶植大小地主的复活便算了事,那又何必抛掷了这么大的牺牲!”(徐盈《江西农村改进事业的全貌》,《游客话江西》)
乡村建设,是失败还是中断?
1937年4月,徐盈在万家埠实验区采访,谈到与总干事王枕心有关的两个细节。一是王枕心理论水平实在是高。为了推动乡村建设,王枕心写过一本叫《中国民族自救之路》的小册子,认为中国农村崩溃,如同得了慢性肺炎,外感帝国主义之经济剥削,内有封建势力之弥漫,是故农村问题不只在农村,还需内外一起调理。与此同时,农村问题也不是一方面的问题,需要整个社会的配合,农村的改进绝非是一种技术改良所能达到,必须有各方面的推进才有出路。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得唤起民众自治、自强的力量,使他们首先能够“自信”,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互信”乃至“共信”。
另一个细节更值得回味。当时徐盈正与当地农业指导员畅谈“三农”,忽然听说请来放映电影的“电影汽车”要开回省会了。王枕心为此非常着急,因为他已经通知各保来看电影,岂能失信于民——“就是熊主席要,我也有办法的”。可车子最后还是开回去了,这回不是熊主席要,而是林主席要。这里的林主席,是指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更可以说一个代表着随时可能中断这场乡村建设的外力的隐喻。
在走马乡实验区,苏邨圃希望借助政治力量扶助农民,以达到“四自”:自治、自卫、自给、自强。让他尴尬的是,从一开始,这个机构便不能真正做到自立,因为经费很成问题。而且这是一个较为普遍的问题。有一位教育视导员在看了江西农村实验区教育的情况后表示:“我去视察乡村学校,只要有教师,有校舍,有学生,我就给他满分,因为根本不能再苛求,再苛求乡村就没有一所能称得起是学校的。”(徐盈《江西农村改进事业的全貌》,《游客话江西》)
尽管乡村建设得到了政府与社会的一些支持,但就整体而言各实验区仍只是勉力维持。至于后来一个个销声匿迹,已非各位干事之精诚团结、励精图治所能挽回。一年后,日军入侵江西,位于赣北的走马乡实验区率先沦陷,宣告这场曾经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接近尾声。
文艺评论家姜弘在《苏邨圃传略》一书序言中谈到,苏邨圃在五四运动前入北京大学学习,亲身参加了那场游行示威和火烧赵家楼的过激行动。他既是胡适喜爱的学生,又是李大钊主持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成员,在报刊上发表过激进文章。但在步入社会以后,所奉行的却是“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主张进行全面深入细致的调查,然后进行适合中国实际的改革。而真正的五四精神、五四传统,产生于那场火爆的街头抗议活动以前,《新青年》杂志所代表的启蒙主义新文化运动,才是五四的源头和正身。觉醒了的新青年走上了两条路,一条是激进的革命之路,一条是渐进的改革之路。前一条路经过“一二九”到延安的“抗大”、“鲁艺”和后来的一些“革大”、“军大”(革命大学、军政大学),后来直到“文革”;后者则是从北京大学到西南联大,从《新青年》到《观察》,后来几经迂回反复直到今天。(姜弘《从一个人看一个时代》,《苏邨圃传略》)
回顾当年的乡村建设,是否还有一个“社会的五四”?政治的五四、文化的五四,在某种程度上说都可谓“精英的五四”,且具有理想主义倾向。清末民初,个人觉醒与社会建设并驾齐驱,尽管一度走到了无政府主义的极端,尽管历尽坎坷,几度沉沦,但建设一个可以期许的,即将远离“贫穷,疾病,愚昧,贪污与扰乱”这“五鬼”的美好社会,却是包括精英与大众在内的所有人的共识。
研究者多以“终于免不了失败的命运”为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盖棺定论。不过在我看来,谈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当以得失论之,而不应笼统地归之于“失败”二字。正如有学生因病辍学,中止了学业,你不能说他的书读失败了。更重要的是,透过这些未竟的乡村建设,我们从中学到与得到了什么。又毕竟,就历史增量而言,有些实验区的成果还是较为完好地保留下来。比如说万家埠实验区,距离小堡村不过二十公里,至今以“民国村”留存,成为当地开发农村旅游的一个重要景点。回顾百年中国,如果非要说失败,只能说历史上所有剥夺农民权利的改革最终都失败了。
虽说历史不容假设,如果政治归政治,社会归社会,社会建设能不因政治动荡而得以保全,今日中国将有何等可观的文明累积。同样要问的是,一个自称“不建设,毋宁死”的政权,何以丢掉大陆,败走台湾?倘使当年国民政府能像阎锡山所说在完成民族与民权大任时兼顾民生,能像后来在台湾一样进行土地改革,急农民之所需,历史会不会有另一种写法?有一点是已经发生了的,国民党的军队有能力将苏区的红军赶到陕北,却没有能力赶走自己在土地政策上的漫不经心。当它一错过再错过,历史终于失去了耐心,已经不愿再给它时间了。
4.计划政治下的“盲流”
对于国民来说,人生最大的不幸是他既挡不住历史前进的车轮,又挡不住历史后退的车轮,遭遇双重辗压。
前文回答了“农村是前线,还是后方”的问题,百余年来的中国,农村是既为后方又是前线。农民为了工业化与城市化,被圈在田间地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为国家发展源源不断地输送人力与物力,难免会给人一种身居后方的印象。即使是我本人,从城里回到乡村之时,也自觉像是回到了人生的后方。然而,每当你看到或者想起这些山野里的寂寞生灵,为这个国家所作的默默无闻的牺牲,以及他们正遭遇的普遍的苦难,你就不得不承认,这所谓的大后方实则为中国最真实的前线。所以,有一年夏天我在乡下和一些乡镇干部聊天时说:“今日世界的前线在中国,而中国的前线在乡村,是故中国乡村是世界之前线。影视明星送文化下乡,理应端正态度,明确自己实为劳军。”
乡村这种“既为后方又是前线”的暧昧印象,在建国之初表现得尤其明显。遥想当年满腔热血的知识青年与垦荒大军开始上山下乡之时,各地车站、码头红旗飘飘、人山人海,那时候的人们何尝不是将这些青年当作即将送上前线的英雄一样加以礼遇。然而,如果了解当时的一些历史,你又会发现,青年被大批动员下乡,实则是因为经济与教育等层面出现了重大的危机,也算是和平年代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了。当危机来临时,农村再次成为时代的大后方与避难所。
据统计,1954年,全国约有60%的初中毕业生不能升学,约有63%的小学生不能升入初中,他们需要走上社会,参加生产。刘小萌在《中国知青史》一书中写道:学生们读了若干年书,因为某种原因不得不中断学习,转而从事某种职业或者回乡务农,本是寻常之事。“然而,由政府出面,号召不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从事劳动生产,并且强调回乡务农的必要性,则是旷古未闻的。”1954年7月11日,《中国青年》刊文解释国家不能花费很大力量来办教育的苦衷,此后教育部副部长叶圣陶曾经特别撰文,向家长呼吁如果孩子们未能升学,第一千万不要责怪孩子,第二千万不要责怪政府。今日回望,国民自知“责怪政府”乃现代政治文明之精要。然而,当时在西南地区看到“命苦不怪父母,地震不怨政府”这样的标语,难免在心底叹息这眼前的光景,恍如昨时。
广阔天地,“恩将仇报”
据小堡村村民说,村里没有下乡的知青,只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下放过两个干部。后来他们回了城,时至今日,很少有人提起他们。不过,严格地说,如果按当年国家动员辍学的逻辑,村里还是自产自销过知青的。几位“中小学生土著”,包括我的父亲,虽非在城里生长,在六十年代也是因为国家出面而被从学校动员回乡务农。父亲记得最清楚的也是当年的那句口号——“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这个口号源于1955年12月毛泽东的一句讲话:“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领袖的授权与动员,使越来越多的城中青年被投放到农村。本来是为了化解经济与教育危机的行为,轻而易举地变成了一场高蹈理想的革命运动。1955年下半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一股中小学生辍学风,到1956年达到高潮,有些地方中学生退学休学的人数竟达到了总数的50%以上。大量中小学生回乡生产,农民认为反正也是回乡干活,书读多了也没用。而且,农业合作化以后,靠计工分吃饭的农民也希望孩子早些回家做“劳力士”,多挣些工分。
在一个崇尚知识、功能正常的社会里,人们多会将升学作为人生进步的阶梯。然而,在极端的年代里,读书、升学成了可望而不可即的镜花水月。不唯乡村,城里同样“积压”了大量待业青年。尽管有领袖的亲自动员,但还是有很多人因为某种“劣根性”拒绝回到农村去。有人抱怨高中毕业生参加农业是大材小用,“杀鸡怎能用牛刀?”很快有人自嘲:“现在没有了牛,只好用来杀鸡了。”1957年,甚至连一向温顺的天津中学生也组织游行,喊出了“绝不回农村”的口号。一些地方的学生甚至公开闹事,游行示威。
对此,1957年1月,毛泽东的态度是:
第一条是不提倡,第二条是有人硬要闹就让他闹。我们宪法上规定有游行、示威自由,没有规定罢工自由,但是也没有禁止,所以罢工并不违反宪法。有人要罢工,要请愿,你硬要去阻止,那不好。我看,谁想闹谁就闹,想闹多久就闹多久,一个月不够就两个月,总之没有闹够就不收场……这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把问题充分暴露出来,把是非搞清楚,使大家得到锻炼,使那些没有道理的人、那些坏人闹输。
很快,政府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接连不断的对抗,使最初理想主义的温和动员开始让位于政治斗争的急风暴雨。1957年8月以后,随着反右运动的展开,不能正确对待自己的升学和从事生产劳动问题的学生,被理解为听信了右派分子的煽动。“有命不革命,活着等于零。”由于新生活是党给的,如果因为私利而反对党,在一个高唱“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的时代,很快被视为“恩将仇报”。为完成上级分配的下乡动员任务,一些地方甚至采取了强迁户口、断绝口粮、给毕业生家长办“学习班”等强制性措施。而事实上,作为接收地的农村并不欢迎这些外来客,因为后者的到来,会挤占他们的口粮。
至于毛泽东并不反对的罢工,我曾在1968年7月26日出版的广州《刺刀见红》报上读到这样一则文字:“白云山下东风劲,珠江两岸红旗舞,广州形势大好。……罢工是在资产阶级专政的暗无天日的社会里,苦大仇深的工人阶级的一种革命行动……罢工是有阶级性的。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罢工就是对毛主席的不忠;罢工就是极大的犯罪。”
“逃农役”
1960年代中后期,一些不安心在农村扎根的青年陆续回城,同样被理解为受了阶级敌人的蛊惑,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许多媒体纷纷撰文号召“受蒙蔽的知识青年”、“立即打回农村去,就地闹革命”、“已离开农村的要迅速返回,杀它一个回马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