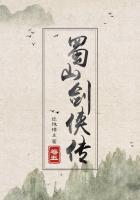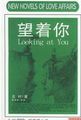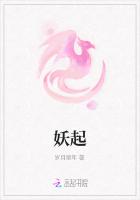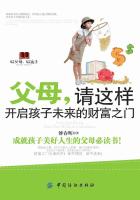然而,这不过是庆喜为了避开齐昭、平冈圆四郎以及其他近侍的激愤而演的一出戏而已。只要对庆喜在第二日——23日在幕府与井伊直弼的对谈略加推敲,自然便会明白。
“一桥卿似乎打算亲自弹劾扫部头。”
对这一说法感到害怕的自然便是几位新任老中。据传闻称,老中们将自己的恐惧转嫁给了直弼,令大老感到十分震惊。然而,井伊直弼并非会被传言吓得魂飞魄散的胆小人物,他在行动之前便已准备好应对意料之中的反抗。
“原来是恶龙之子打算先下手为强啊。”直弼以为自己充分了解庆喜的为人。
(这个毛头小子会说些什么呢……)
直弼怀着浓厚的兴趣,毫不迟疑地答复了前来通报的中根长十郎,决定在幕府与庆喜见面。
二人之间的会谈是在大廊下的上间进行的。他们几乎在同一时间登城,而在二十二岁的一桥庆喜休憩喝茶期间,直弼首先处理了清晨的诸多事务,然后便立刻出现在了庆喜面前。
他刚刚施了一礼,庆喜便抢先开口说道:“扫部头可好?”
“拜见一桥卿。”
“当此艰难时节,足下初任大老之职,实在辛苦了。”
就连颇有度量的直弼都未曾想到庆喜开口便会慰问自己,不禁惊讶地抬头望向对方。只见庆喜一双明眸熠熠生辉,身姿端正,标致的脸庞上带着无所畏惧的平和,勾画出一位有着良好家世的贵公子形象。他的声音也很清澈,沁人心脾。
直弼一时感到心里一阵火热。
(倘若将军能像此人一样……)
总之,对于高高在上的大名而言,外表是很重要的,所以他们才会特意选择美女作为侧室。即便是壁龛中的装饰物,若是难看丑陋,对家老而言也是无比沉重的负担。
“您可知历代将军对世子有何教诲?”此时,庆喜淡然开口。最初的质问既非条约问题,亦非驿使上书。
“历代将军……”就在直弼慌张地重复这句话时,庆喜则微笑着放下了手中的茶碗,看上去没有丝毫争斗或非难的意思,这令直弼感到十分混乱。
“您是说,历代将军对西之丸的世子……有何教诲?”直弼一脸惊讶地反问道。只因庆喜的态度过于柔和,令他不禁提出反问。
“是的,西之丸大人很快就会成为将军,届时将变得无人可掣。”
“无人可掣?”
“届时,没有人能位于将军之上,对其加以训斥,令其惧怕,没错吧?”
“的确如此。”
“因此,我听说历代将军都会对世子如此教诲——倘若举止失当,将是对京都的无礼……您明白吗?”
(糟了!)
直弼没想到对方会从这里开始斥责驿使上书的无礼。
(对此人万不可掉以轻心!)
庆喜继续淡淡说道:“在我年幼之时,也曾受到上代将军家庆公的谆谆教诲。无人可惧会令人变得粗野。因为幕府之中已经无人能够对将军加以训斥,所以要时常念及京都,借以自省。此事是最为重要的大事,关系到日本国体。”
“不胜……惶恐。”对方无视水户学的理论,而通过上代将军的话来展开非难。直弼感到浑身直冒冷汗。
“不必惶恐。我听说驿使上书一事并非出自您的意愿,松平伊贺守忠固似乎本就以为外交属于他的施政范畴,因而专横独断。既然您已让他承担责任,问题也就暂时解决了。”
“啊,不胜惶恐……”
“不过,您应该了解当于何时进京向朝廷直接汇报吧?”
“这个……”
“正如伊贺守所言,京都已将国内政治悉数交付于幕府处理,但涉及在全世界面前决定一国国策的大事,便绝不可专断。锁国是幕府在三代将军家光公时期暗中征询朝廷意向后制定的国家方针,如今已经到了改变的时刻。您对此意下如何?”
“的确如此。”
“您恐怕感到很遗憾吧?堀田备中守正睦等人的考虑极其单纯,他们以为日本人已习惯了太平生活,兼之国防实力不足,面对列强的胁迫,只能忍气吞声地开国。我对此事也深感遗憾。”
“嗯……”
“但是,倘若我们就此屈服于对手的武力而开国,数十年后……不,百年之后,我们的子孙后代将会变得忍无可忍。不平等的外交一定会埋下怨恨的种子。”
直弼茫然地听着。庆喜的声音让他产生一种恍惚的感觉,一字一句直沁入直弼内心。
“总之,我们需要与对手一战。倘若不能在平等友爱的基础上建交,胁迫方与被胁迫方将很难统一。在距离东照公创业二百五十余年的今天,整个日本的外样大名和谱代大名心中仍然有一个疙瘩,此事便是最好的证明,您应该是再清楚不过了。朝廷收到驿使文书后恐怕也会感到遗憾,因为幕府竟连为国一战的实力都不具备……无论如何,此事都是征夷大将军的责任。因此,我认为您必须立刻进京,以留下百年悔恨的条约签订一事为戒,考虑如何善后,并以至诚之心上奏朝廷,请求宽恕。您意下如何?”
“这个……”
“原本当由将军亲自进京,但将军有病在身,理应由大老承担起这份责任,没错吧?”
庆喜的话条理井然,不露丝毫破绽。倘若其中充满责备的语气,自然会令直弼产生反击心理,但庆喜的一番言谈只是思路清晰的推论,令直弼甚至感觉不到一丝敌意。直弼不禁开始责备自己。四十四岁的直弼竟会被年龄只有自己一半的二十二岁的庆喜谆谆教诲。
(为何没有在四五年前便见到此人呢……)
直弼的想法中夹杂着狼狈、悔恨以及感叹。
(原来如此,松平庆永和岛津齐彬极力推举此人的确有其道理……)
想到这里,他顿时觉得世子问题已经变成了一片泥泞的沼泽,而自己已经狠狠地阔步迈入,以致深陷其中。
(前将军家庆公或许当真打算立此人为世子……)
家庆的正夫人也是下嫁自有栖川亲王家,但家庆与正夫人并未生有世子,唯一的儿子便是形同废人的家定。因此,纵然家庆将自己的希望寄托在最亲近的正夫人之妹产下的子嗣身上,也是合情合理的。而且,庆喜还具备世间罕见的贤明……
“直弼惶恐之至。”
井伊直弼浑身大汗淋漓,跪拜在地。在他心中,庆喜指出的“百年悔恨”令他大为震动。
在战国时代,外样大名曾与宗家敌对,因此谱代大名至今仍无法相信他们。即使历经二百五十余年,这种毫无理由的怨恨之种仍在继续萌芽。
(列强与日本之间一定也会埋下同样的种子……)
因此,在能够互相平等握手前倘若不能一战,那么在遥远的将来必定会发生更为激烈的冲突。对于正在钻研佛教的直弼而言,这种因果报应的想法造成了一种极大的震撼。倘若如此开国,总有一天日本会变得军备齐整,届时一定会向列强展开反击。庆喜的目光早已投向遥远的将来,而且他似乎并不打算责难自己,只是不住劝说自己进京代将军请求宽恕。
“倘若……”庆喜说了一个词后突然停住,然后才如同自言自语般的继续说道,“倘若朝廷震怒,要求将军亲自进京的话,事情会变得更加麻烦,请您也要考虑到这一点。”
“不胜感激!直弼立刻了结杂务,而后必定亲自进京。”
直弼斩钉截铁般的说道。这绝非曾对忠固和正睦使用过的手腕,而是直弼的真情流露,他似乎当真发自内心地觉得必须这样做。
“是吗?您会这样做吗?”庆喜也垂下一直紧紧端平的双肩,松了口气。
(总算说服他了……)
任何人都能从眼前的庆喜身上看出一种极度紧张后的放松。
“接下来,我听说已将纪州公子内定为将军世子。”
“是……”
“当此艰难时节,纷争越少越好,因此这件事情如此便好。擅自签订条约的做法极不合适,请您将此事铭记于心,亲自向天皇解释,直至天皇宽赦,多有拜托了。”
“明白……”
“此行必会十分辛苦,请您一定保重身体。”
井伊直弼深施一礼后离开廊下,却仍觉得自己犹在梦中。
(竟令人感到如此清新舒爽……)
这种犹如一抹凉风般的清爽感觉究竟是怎么回事?自己竟会觉得可以为此人献出生命……而且,他明明是水户恶龙的儿子!
另一方,庆喜的父亲齐昭正唤来近侍茅根寒绿,寻找怒气的发泄对象。
一桥庆喜的立场与水户齐昭的立场决然不同。庆喜不仅是齐昭的儿子,同时也是有栖川亲王家的孙子,而齐昭并非如此,他不过是镇压藩内反对派而得以继承水户家的前任藩主而已。他站在继承义公精神的立场上,以指导幕政改革为目标,无论其见识如何高远,也不过与井伊直弼处于同一水平,并且彼此互不相让。
换句话说,庆喜是站在高处往下看,而齐昭则与对手站在同一高度。
在与对手站在同一高度的齐昭眼中,井伊直弼完全就是一个不可饶恕的桀骜不驯的权力主义者。
“你对当前国难有何看法?”
齐昭咬牙切齿地向茅根寒绿问道。侧用人茅根寒绿便是在后来的安政大狱中被判死罪的茅根伊予之介。他当时三十五岁,正值年富力强。
“你听好了,寒绿,倘若彦根有尊皇之心,他们就应该按照朝廷的意愿行动。”
“您所言极是。”
“从朝廷的立场来看,并无外样大名与谱代大名之分,他们都是一视同仁的国之赤子,彼此是兄弟。朝廷下令重行众议,目的就是让赤子发自内心地统一起来,而统一以后才能发挥出真正的力量。可幕府竟然违抗圣意,不仅擅自签订条约,还打算通过驿使上书息事宁人,这是何等无礼、何等傲慢!既不能看清时势,又毫无尊皇之心,你认为我能放过这种人吗?”
“您的愤怒都是有道理的。”
“你明白了吧?若是明白的话,就立刻去一趟越前藩邸。明晨九时,我会偕同尾张大人和水户当家强行登城,将扫部头留住,加以诘问,逼他剖腹自尽!你请越前大人届时一同登城,希望他能为了日本国和德川家协助出力,明白吗?”
齐昭的话语之中燃烧着愤怒的火焰,茅根寒绿认为齐昭愤怒之下的决断是理所当然的,但当时已是23日深夜。于是,他便决定于第二天一早以正式使者的身份拜访越前藩邸,说明所有事宜。
在此期间,黑川嘉兵卫从一桥家出发来找齐昭,将庆喜与井伊会谈之事通过茅根向齐昭作了汇报,至于齐昭是否会听从便不得而知了。
总之,第二天——24日,气氛从一大早就显得危机四伏。大名皆有各自确定的出勤时间,即使是御三家和御三卿也不能随便登城。然而,齐昭打算无视规定,于当日“强行登城”。天刚破晓,尾张的德川庆恕就来到了水户藩邸。隐居的齐昭此时早已来到小石川的水户藩邸,当家庆笃(庆喜之兄)自然也会同行。
茅根寒绿也按照预定计划,以使者身份来到了御家门首座越前的藩邸。对于使者的到来,庆永也显得有些兴奋,他回复道:“我已提出今早拜访井伊宅邸,等会谈结束就立刻登城。”
也许是比水户齐昭年轻的缘故,庆永对于此事表现得更为冷静。
他打算先与井伊直弼面谈,借机说服对方。以当前局势而论,擅自签订条约本就已不可阻止,但通过驿使上书息事宁人——更准确地说是自以为可以息事宁人的做法,完全是因为直弼太不了解政治了,必须在这一点上好好对其教导一番。但与此相比,庆永认为继嗣问题更为重要,并且至今仍未放弃。他相信,必须立贤明之人为世子,消除谱代与外样之间的隔阂,充分发掘整个日本的人才,断然实行幕府大改革。这位三十一岁的年轻大名有着强烈的上进心,他认为直弼也应该明白其中的道理。于是,在茅根离开后,庆永也立刻离开了藩邸。
走出藩邸大门,庆永胸中翻腾不已。
(我一定要帮助井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