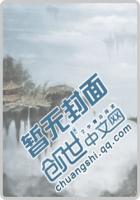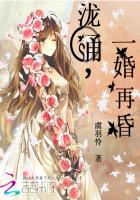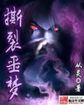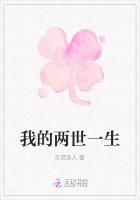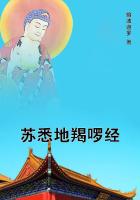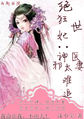费晓玲对丈夫表明自己的态度以后,表面看上去没有什么变化,依然尽心尽力地服侍着丈夫,对公婆也还是很孝敬。她在刚嫁到夏家的一小段日子里,虽说和丈夫一直没什么话可说,但是对公婆特别是对婆婆梁寒烟还常说些琐事和心事。这样的日子不长,后来她的话越来越少,家里的人都已经习以为常。这次她爹妈来过以后,她依然默默的做事,话很少,梁寒烟和夏玺臣并没觉得有什么变化。唯有夏文翰知道,费晓玲从那天晚上他提出分手以后,她不光是话更少了,整个人的变化其实还是很大的。
夏文翰可以很真切地感觉到,费晓玲在服侍自己的时候,以前是有点战战兢兢,生怕一个不小心惹得丈夫不高兴。现在不一样了,可以感觉到她只是在履行妻子的义务,做事仍然很小心,但似乎并不在意丈夫高兴与否了。他能够感到她的心好像已经麻木,或许是已经死了。
夏文翰很同情她,有时候也想再努力一把,让自己能够接受她。但是他偶尔做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不光是费晓玲完全不再迎合他,他自己也是怎么都没法找到哪怕丁点感觉。
他看着年轻貌美、温柔顺从的妻子,看到她表面上心如止水,但明显的一天比一天憔悴,心里很歉疚,可是又不知所措。他们两个就这样顶着夫妻的名分,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实质上却连两个陌生人都不如。
夏文翰深感对不起妻子,不愿意再给她更大的伤害,所以就这样和她做着有名无实的夫妻。他在母亲问起他们之间现在如何的时候,没有像以前那样将怨气发泄出来,而是轻描淡写的说比以前好多了。梁寒烟看他们小夫妻之间并没有现出特别的罅隙,至少并没有比以前更不睦,也以为亲家的努力有了点效果,过段日子小夫妻两个的关系会有所改善的。
梁寒烟知道儿子和儿媳之间依旧有些冷淡,并不像一般夫妻那样亲近和睦,更谈不上什么心心相印。她对这些都看得不重,在她看来心是不是相印无所谓,只要他们小夫妻之间能够肌肤相亲就成。她急切地盼着儿媳给她添丁增口,能够让她抱上孙子。她想的是只要有了孩子,不但夏家香火有继,儿子和儿媳之间也自会增加感情,渐渐正常的。
又是几个月过去,小夫妻两个还是那样,不温不火地。最让梁寒烟焦虑的,是儿媳的肚子依旧毫无动静,很快她就憋不住了。她无论是从费晓玲那里,还是儿子那边,都打听不出什么东西来。但是她感到儿子和儿媳之间好像存在的问题,比先前她所想的还要严重得多。
梁寒烟和丈夫商量过后,动起了别的脑筋。她和夏玺臣都觉得费晓玲人很好,即便是有问题,那也是出在儿子身上。他们不想太对不起儿媳,可是为了夏家的香火,他们又不能不着急。他们夫妇两个的意见有一点是一致的——不能休了费晓玲,那样太过分了。但在如何处理这件事上,夫妇两人出现了分歧——梁寒烟想的是可以考虑给儿子纳妾;夏玺臣却显得首鼠两端,他为了夏家香火觉得这是个法子,但是又对梁寒烟说,夏家祖辈的遗训,其中有一条就是“不可纳妾”。
梁寒烟以为自己想了个两全其美的好法子,她斥责丈夫食古不化,不知变通。夏玺臣受到妻子斥责,想到夏家香烟不继,也就不出声了。梁寒烟见丈夫不再出声,就自说自话开始行动。
梁寒烟和费晓玲说的时候,本想她会不乐意,却没想到她一点反对的意思都没表示出来。费晓玲的反应让梁寒烟感到意外,而更加让她意外的,是夏文翰一听到这主意就发了火,坚决不同意。
夏文翰并不是因为自己不想娶个情投意合的小妾,而是他害怕爹妈又一次包办,再硬塞给他一个他不愿意要的女人。这些年他虽然在外奔波过不少日子,到过的地方也不止一处,但是都没有遇到合适的女人。他自己没有合适的对象可选择,自然就害怕父母再次包办——一个费晓玲就让他受累不浅,如果再加上一个,即便比费晓玲好一点,也会让他受不了的。
这件事因为夏文翰不同意而作罢。夏玺臣夫妇着急的是夏家后续乏人,如今这也不是,那也不成,这越来越成为他们的一大心病。事到如今,夏玺臣夫妇都后悔当时逼儿子逼得太紧,以至于造成了这番困境,可说是自食其果。
梁寒烟这时候开始偏向于儿子的想法,那就是“休掉”费晓玲,然后名正言顺地再娶一个儿媳回来。一旦有了这个想法,她再看儿媳的时候,就和原先不同了。以前费晓玲在她眼里差不多没什么不是之处,现在却渐渐被她发现了越来越多的缺点。在她眼里的这同一个儿媳,没过多久,就成了一个配不上自己儿子的女人。
夏文翰现在的日子更不好过了:母亲的做法越来越过分,也越来越明火执仗,就是要逼迫费晓玲和自己离婚;费晓玲则逆来顺受,看得出她越来越痛苦,但她就是不愿意离开这个名义上的丈夫、名义上的家。
夏文翰很想和费晓玲离婚,但是他十分反感母亲的做法。他要的是费晓玲心甘情愿和自己分手,就算做不到这一点,那至少也要让她自己答应下来,而不能用逼迫的手段。
他在原先的不如意上,又增添了一层新的痛苦。夏家原本其乐融融的一户人家,现在却全家都陷入了痛苦、难受的心灵煎熬之中。
梁寒烟为了香火延续,更为了心痛儿子,渐渐地变本加厉,对费晓玲的逼迫几乎到了公开的地步。她开始冷言冷语地刺激费晓玲,旁敲侧击地点明夏家不可能不顾及香火,暗示费晓玲主动“让位”。费晓玲还是那样,什么都不言语,抱定一个宗旨,那就是无论丈夫再讨哪怕十个八个小老婆,她都无所谓,但是她不会和丈夫离婚。
梁寒烟束手无策,终于言辞上越来越露骨了。这天早上起来,费晓玲就觉得身体不适,耳鸣脚软,但是又没有其它症状。她在吃午饭的时候好了一点,耳朵不那么鸣响了,但是手脚还是很软,人只想睡觉。平日饭后的碗筷都是费晓玲洗的——她总想找点事做做,好分散点心思,同时她也嫌丫环洗得不干不净。今天她实在有些支撑不住,就没有收拾碗筷,胡乱扒拉了几口饭菜,把碗一丢就回自己房里去了。
费晓玲身体不舒服,她没有对谁说一个字,夏文翰又不关心她,因此谁都不知道。今天或许是人实在太不适,她在回房间去之前,居然连向公婆说一声这个小节都忘了。
梁寒烟本就越来越看不惯这个儿媳,见到她甩手就走,连声招呼都不打,顿时怒气直冲脑门。她将手中的筷子重重地拍在了桌上,大声说道:“不像话!现在谁都可以在我们面前摆架子了!这种死样怪气的样子,到底是做给谁看的!想过就过,不想过的话就给我滚!还以为谁稀罕你呐?”
费晓玲听到了婆婆的话,脑子虽然有些晕,但还明白这是说给自己听的,起因大约是自己临走忘了对公婆和丈夫说一声。她没有回头,知道就是现在自己回头补上这个礼节,婆婆说不定不但不会消气,反而可能火上浇油。她的脚步停顿了一下,还是继续朝里屋走了,只是从她抽动的双肩可以看得出,她一定是在强行忍着没有哭出声来。
看着费晓玲的身影消失在客厅通里屋的门后,夏玺臣觉得妻子实在过分,他怒声呵斥梁寒烟:“寒烟,你也太过分了,怎么能这样说话?”
梁寒烟赌气地回了一句:“我说的不对吗?那你说,我应该怎么说?”
夏玺臣还想说她几句,夏文翰已经扔下碗筷,白了他妈一眼,站起身就朝门外走去。一顿中午饭就这样不欢而散。
夏玺臣虽然觉得妻子对费晓玲有些过分,在儿子和儿媳小两口别扭的关系上,错在儿子,儿媳只是性格太柔弱而已。可是夏家几代都是一脉单传,夏家的香火一直不旺。现在到了文翰这一代,更让他忧心忡忡的情况出现了,要是真的一直这么下去,夏家的这一支,就将在文翰这一代完结。由于这个原因,他虽觉妻子没道理,儿媳更冤屈,也就没有多指责妻子。
梁寒烟对儿媳的态度,一天比一天严厉,也一天比一天不讲理。费晓玲整天低眉顺眼,忍受着,丝毫没有想反抗的意思。她这种逆来顺受的态度,让夏文翰对他充满了同情,也愈加无法理解和接受。他对她除了同情以外,还有很深的歉疚,但也因此更加看不惯她的这种性格,更加没有感情可言了。
这样的日子,全家谁都不好过。费晓玲自不待言,夏玺臣和梁寒烟也不好受,而夏文翰也如坐针毡。
梁寒烟见自己怎么做、怎么说都没法让儿媳主动退出,于是开始从儿子这面下力气。她不顾儿子的感受,也不顾丈夫的劝说,在外面替儿子物色起了女孩子。
夏文翰并非没有想过重新找一个妻子,母亲为他找到女孩,也有看上去不错的。可是他对母亲再次这么替他安排十分反感,不但毫无例外地一概拒绝,而且这种反感与日俱增。
终于,他觉得在这个家里,自己再要这么呆下去的话,就快要被窒息了。
这天一上午,夏玺臣和梁寒烟都没有见到儿子。开始的时候他们都不以为意,儿子近来常常这样,一出去就是一天。到了下午,依然没见文翰的人影。夏玺臣差不多每天都会在午饭过后去书房,今天依然如此。他进了书房,还没有坐下,就看到自己常坐的书桌上有一封信。他有点奇怪,似乎预感到了什么,连忙拿起信看了起来。
信是文翰留的,意思说的是——他在家里待不下去了,想到江海去一段日子。要爹爹和妈不用担心,他会照顾好自己的。同时他要爹妈待晓玲好一点,一切都是他的错,晓玲是无辜的。最后,他又留了一张纸给晓玲,告诉她自己不能再和她生活下去,不想耽误她。希望她能原谅他,并且找到一个能待她好的人,他祝她以后能幸福。
梁寒烟再看了儿子留下的信以后,马上就要到江海去找儿子回来。夏玺臣劝住了她,他对她说:留得住人留不住心,即使把文翰找回来,也解决不了他和晓玲之间的问题;倒不如让他在外面住一段时间,或许时间一长,事情自然而然会有转变。
梁寒烟想想觉得丈夫说的也有道理,再加上没有丈夫出面,就算让她去找儿子,偌大一个江海,她也不知道该如何去找儿子。她不再坚持己见,对这件事顺其自然了。
夏玺臣忐忑地把文翰留的信交给了费晓玲。费晓玲看完信,竟然能保持了平静,什么都没说。夏玺臣不知道儿媳是怎么想的,又不好问什么,只好随她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