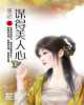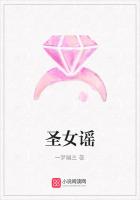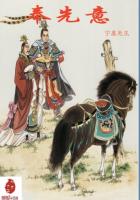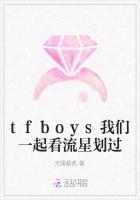科举制度,从隋朝大业年间便已经开始,但是直到宋朝太平兴国八年,才开始分类“三甲”。殿试第一等的称为“一甲”,赐“进士及第”;第二等的称为“二甲”,赐“进士出身”。而第三等的称为“三甲”,划为“同进士出身”。平常,三者统称进士。
“榜眼”的由来,因为殿试结果需要张榜,填写进士榜时,状元的姓名,居上端正中,二、三名分列左右,在进士榜上的位置,好像人体的眼部地位,所以称作榜眼。
南宋以后,第三名才称之“探花”。
就是说,探花,起源于南宋。南宋之前,二、三名,都叫榜眼。
一甲,为前三名,状元、榜眼、探花。俗称“三鼎甲”或“三及第”。
二甲若干名。第一名,称传胪。传胪之称,始于北宋。
二甲名额较多,三甲就更多了。但是三甲,是不上榜的,只是能够进入吏部备用。其身份,高于举人,低于进士出身。
科考,每三年一次。序列:殿试、会试、乡试、县试。
春闱,乃会试(国级),会试过关的,为“中式进士”,称为“贡生”。贡生,才能参加殿试。殿试后,为进士。因为贡生,没有上进士的,鲜有。所以获得会试张榜者,可以基本算进士了。无非,通过殿试,分出“三甲”。
秋闱,乃乡试(省级),中试者为“廪生”,称举人,也叫“廪膳生员”。因为举人,政府要给予他们廪膳,补助生活,所以叫廪膳生员。因而,秋闱也叫考举。举子,才能参加会试。
县试,相当于摸底考试。中试者为“童生”,称秀才。成为秀才,就是“知识分子”了。
甲戌科会试开考,举子们都被关进贡院。
三月的临安(杭州),天气逐渐转暖,万木苍翠、百花争艳。这大街小巷里,多了几分春的妩媚,夏的扶苏。然而,贡院却弥漫着肃杀之气。要进贡院,就要经过严格的排队“搜身”。这,对于读书人来说,十分的难堪。进了贡院后,等于与世隔绝。吃喝拉撒睡,都在一间蜗居里,一人一蜗居。
考生如此,考官也好不到哪里去。按照规矩,考试结束之后,所有主考、同考的官员,在放榜之前都不得离开贡院。贡院外有专门的官兵把守,谁若是走出一步,都以舞弊论处。
这样做,才叫正常。若有非议,人们一定会回答你:开玩笑,国家抡才大典,岂是闹着玩的
会试期间,朝廷上下,近百个官员,都吃喝在这里。考生们,紧张地绞尽脑汁,舞文弄墨,苦思一题又一题,挥毫一文又一文。而同考和监考的官员,偏偏无事可做,每曰只能聚在贡院内的明伦堂里饮茶,闲谈。
考试结束,考生游玩去了。同考、监考官员却严阵以待。
对于阅卷官来说,任务更是紧张无比。几千张试卷的审阅,绝对不是闹着玩的。会试的阅卷规矩,同样极其严格,一丝一毫都马虎不得。阅卷官员,采取的是“转桌”传阅的方式。即一个考官若是觉得文章可取,则画圈;觉得略次,则划上各种既定的符号;觉得不行,直接打叉。无论判定什么等次,都要打上符号并盖上自己的印章,以示负责。紧接着,再递给下一个阅卷官判定。直至,每份卷子的封条上,都有八个符号,八个盖印。这份卷子,才算阅卷完毕。
而“转桌”就是一种流水作业的阅卷方式。每份卷子,但凡有六个画圈的符号,就说明这篇文章,算是通过了阅卷官的审核。
对比乡试,六个阅卷官就够了。所以乡试考卷,有四个画圈的,就算通过。这种,八比六,六比四的比率,自然是要获得占大多数的“O”圈。反之,“X”叉,占多数,就是被判“划落”了。
已经通过审核的文章,送至主考官面前。由主考官,在这些取“中”的试卷之中,择定排名。
这么的持续了四天,所有的卷子总算陆陆续续地阅完。八名阅卷官,早已精疲力尽,却又不敢怠慢,只得强打精神支撑下去。紧接着,进入讨论环节。
所谓讨论,就是主考、副主考,召集所有考官、阅卷官,点评一下文章,尤其是对一些成绩极其优异的文章,分论高下。这本来是主考官一言九鼎的事,不过往往为了以示公平,会把大家一起叫来商议。当然,最后的决定权,自然是主考、副主考手里。
主、副考魏师逊、汤思退眼窝子深陷,显然也是累得不轻。他们昨夜,熬夜看了一夜的卷子,总算理出了一些头绪,不过眼下却遇到了一件难事,在一份卷子上,考官们发生了严重的分歧。
这是一篇极为文思缜密、文采斐然的答卷。若是不出意外,位列会试前三,应当不成问题。可是偏偏,有考官认为,这篇文章里头出了重大的失误。失误在于,文章里承题有一句叫:“颜苦孔之卓”的话。
所谓八股文,其中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最是要紧。那便是,若是文章里头想要引经据典,那么这个经典绝不能超出四书的范畴。而这句“颜苦孔之卓”,考官们几乎都没有印象,也不知是出自哪个经典。这就意味着,如果四书没有这句话,那么这篇八股文的引句就是杜撰,而一旦发现杜撰,那么就属于重大失误,就算你写得再好,就算考官同情你,使你不名落孙山,这名次最多也只是衔在尾巴上。
开玩笑,作文章乃是代圣人立言,哪里轮得到你自创言论?这可不是小事。八位阅卷官,竟然都没有盖印,将矛盾上交。
主考魏师逊暗忖,“颜苦孔之卓”,这样的答卷,绝对不会出自秦埙,便道:“那就打落四等算了。”
副主考汤思退,曾经悄悄开启过封条,看到考生名字。吴皇后召见他时,曾经吩咐道:“要公正对待所有考生,比如等,都是当地乡试解元”此举子,正是皇后在此言中,点到的人物之一。就此划落,若是出了意外,比如“颜苦孔之卓”确是出自某经典,只是一时不知道而已,那便坏事了。须知,吴娘娘,何等博学!?
于是,汤思退道:“按理说,试卷中出现失误,是免不了置之四等,令其来岁再考的。不过,这篇文章字字金玉,下官实在不忍。因此下官的意思,还是置为二等,勉强让他中试,也算是成人之美。”
汤思退开了头,其他阅卷官,便也纷纷说出自己的看法。
“这样的文章,实在是可惜,若没有这一句‘颜苦孔之卓’,一等都是可能的,以老朽之见,或可名列第四名。”
“我却不以为然,如此大的失误,何必要留情面?连书都读不通,文章再锦绣又有何用?不如打落吧。让他好好读书,下次春闱再考。给他一个教训,对这考生也不是坏事。”
一时间,考官、监考官、阅卷官各抒己见,吵得不亦热乎。
汤思退沉吟片刻,终于道:“何不如这样,大家一起做个见证,将这做题的考生请来。这毕竟是抡才大典,既不可让人蒙混过关,也不能冤枉了人家。将这考生请来,问明这一句‘颜苦孔之卓’的出处,再做决定如何?”
魏师逊清楚,汤思退的话还是很有道理的。抡才大典,不能武断,否则难免闹出笑话。可问题就在于,试卷是糊封遮名的,一旦要请考生,就少不得要撕开糊纸,将这考生的姓名公布于众。假若如此,会不会有舞弊之嫌?
其实这个事,也不是没有先例。遇到这种事,需要考官、监考官一起同意,随即大家凑在一起撕开糊名,请来考生,再当堂质问。若是考生能回答出个子丑寅卯,倒也好办。若是回答不出,当场就可以将其打落。
考官们犹豫了,假若这篇文章平平无奇,大家倒是不愿意这么麻烦,可是偏偏这文章作得极好,是少有的佳作,副主考又提出了这个意见,似乎也没什么不妥。
又一番争议之后,总算是拿了主意出来,撕了考卷的糊名,竟然是川蜀乡试解元虞允文。
魏师逊随即,一边命一个差役,飞快地去请人;一边召集了所有相关人员。
小半时辰后,终于有差役过来禀告:“生员虞允文带到。”
明伦堂里,一众聚集的官员,许多人的表情很是怪异。也许,有想看笑话的,也有希望虞允文能够答出问题的。汤思退,就巴望着虞允文,能够给他一个意外惊喜。吴娘娘高兴,他汤思退就交上好运了。
“咳咳”此起彼伏的咳嗽声传出来,大家一个个打起精神。魏师逊很是威严地道:“叫进来说话。”回头又对汤思退道:“汤侍郎,既然是你的主意,你来住持吧。”汤思退赶紧点头称是。
不多久,虞允文跨槛进来,随即向魏师逊行礼,道:“学生见过宗师。”又很谦逊地朝诸位大人行礼:“末学见过诸位大人。”
大家眼前一亮:个头这么高?少见啊!起码身高六尺有余(宋,度量制,并不是三尺等于一米。六尺多,相当于一米八以上)。
大家纷纷点头,有人勉强露出微笑,有人却是虎着脸,还有人发出“哼哼”的一声冷笑。这发出冷笑的人,便是御使科道的御使言官,监考官之一,范同。
这范同,就是绍兴11年,向秦桧建言:“仿太祖杯酒释兵权,来个升官释兵权。”的家伙。之前就说过,范同虽然谐音“饭桶”的名字不好听,但歪邪的水平却是很高,深谙“杯酒释兵权”之精髓。此后,范同便成了秦桧的死党。
这次,秦桧安排死党魏师逊为主考还不算,又安排范同为监考,要他见机行事,确保秦埙的名次。这个虞允文,据说在吴璘手下,甚为有能。当地秋闱的解元不算,这次的八股主卷,除了那句话,又是这般看好。若是让他中了进士,不仅对秦埙的名次来说是威胁,就是对他范同今后的仕途,也是威胁。
一定要先发制人,他想。毕竟他是御使言官,虽然品级不算太高,可是他做的事本来就是得罪人的,连六部堂的大佬们,他都未必怕,更何况是尚未入道的虞允文?
虞允文看了冷笑的人一眼,只是朝他微笑了一下。随即,又向主副考道:“大人唤学生来,不知所为何事?”
汤思退正要开口,那范同忍不住,先发制人道:“本官范同,乃此次抡才大典监考官。本官问你,你到现在还没有幡然悔悟?哼哼,本官问你,‘颜苦孔之卓’出自哪里?分明就是你杜撰。你好端端一个读书人,不去为圣人立言,却是杜撰圣人之言。怎么?你莫非是胆大包天,要自己做圣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