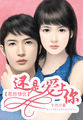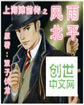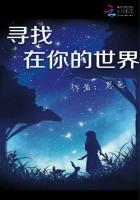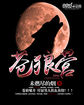回到故乡,躺在儿时的土炕上,久久不能入睡。抚今追昔,浮想联翩,我这个飘泊在外的游子,究竟魂归何处?
桃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想如今,我已经在雍城生活了六七年,原以为,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呆上几年,就可以脱胎换骨,就可以在那里落地生根了,现在才明白,有些地方,你就是脱十层皮,呆上一生,也是不会属于你。
其实,我现在生活的这个雍城并不吝啬,它的门对任何人都是敞开着的。许多和我一样的游子,他们在这座城市里生活过几年,就从里到外地成了城市人,可城市对于我来说,仿佛永远隔着一道玻璃门,我可以看到它,却无法进入它。
多年来,无论走到哪里,我睡梦中的所有场景,都会是我童年的这个河湾村。河湾村里的人,河湾村里的茅屋,河湾村前的千河,河湾村里的小道,那里的一草一木,都深深地根植于我的记忆中,让我无法摆脱。我对我所蛰居的雍城几乎是漠不关心的,相反,从老家那边传来的每一个哪怕是芝麻小事的信息,都让我牵肠挂肚。因此,我只能说在这个雍城里,做着故乡的梦。
我是一个淡泊名利、远离官场、与世无争的人,那些争名夺利、拍马溜屁、与人争斗的事,我总是避而远之,即使走在繁华浮躁的雍城街道里,我也是破帽遮颜。我知道,我一直是将生我养我的河湾村当作一片绿洲,一个退路。我总是在想,也许有那么一天,当我在雍城里闯荡得伤痕累累、山穷水尽时,我就会回到故乡。对于我这个长年在外的飘泊游子来说,乡情可以治愈创伤。它就像一条温软的舌头,可以将我伤口上淋漓的鲜血舔净。
可是,我没有想到,有一天,我的这个梦也会破灭。这么多年,我几乎每年都要回老家一次。可是,我越来越感觉到,那个生我养我的那个河湾,与我梦中的那个河湾的距离越来越远了,它甚至不是物是人非,而是几乎成了人非物非了。我梦中的那些场景已彻底地从河湾村里消失了,那一茬又一茬长起来的后生门的面孔,已无法让我推断出他们的父辈们是张三还是李四。由于城乡距离的缩小,使他们几乎和城里人没有了差别。我还知道,他们中的许多人也和我一样,在我身处的雍城里干着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他们在河湾村里说着城里话,用手机发短信,也在网上聊天。所有的一切都让我明白,河湾村已不再属于我了。
我生活的雍城本不属于我。我心中的那个河湾村也不再属于我。我突然有了一种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感觉。在我生活的这个上百万人口的雍城里,几乎有一半的人都像我一样,是外来人口。我无法知道,他们是不是也有和我一样的感觉,他们会不会在逃离一个地方时,有迷失在另一个地方?
我想,他们会有的。
回乡探亲,适逢春暖花开时节。漫步河湾,休闲经冬的稻田冰化雪消,汪汪的水田里长出一株株一丛丛嫩绿的水草,引来无数小蝌蚪快乐的嬉游。不多日,秧苗们就星散四处了,秧田犹如一面面明亮的镜子,映出白云蓝天、山影桃花。有过了些时日,稻苗发芽长高,转眼间,这一面面境子就成了一方方绿茵茵的地毯。这时候,稻田里的活儿才正式开始:一大早,乡亲们就挽起裤腿下田,在泥水中挥楸抡锄,翻土耙地,的的确确是泥水一把汗一把。吃饭的时间到了,就一口菜馍,喝一碗稀糊米汤。这饭确实就是家常饭,但想到秋后的白生生的稻米,也就津津有味、甘之如饴,欣喜满脸。
乡亲们对坡下的池塘、芦苇沼完全“放手”,无所而治,是以逸待劳之势,面对这河湾稻田却绝不敢掉以轻心,定得精心伺候,那可是口里的饭啊!看那稻田的沙塄,用铁锨抹得笔直光滑;看那一把把秧苗,被分插得横成行纵成列,全部用拉线丈量,谁能不佩服农人们天生的这份敬业的精细、耐心和虔诚!秧苗插完,拣一个轻风细雨的日子,身披一袭衰衣,袋装几把黄豆,手持半根木撅,下田去,在平直光滑的沙塄上,捅洞点豆。百亩稻田,承载着乡亲多少的爱恋和期许!
盛夏,是河湾最热闹的季节。水稻抽穗时节,午间逮虫,半人深而不能透风的稻田,蒸腾的溽热和稻叶的细刺,一身身汗水,一道道划痕,那是庄稼人的苦;而在已是金黄的稻浪里吆喝麻雀,则是庄稼人的甜。那些日子,块块稻田都能见到一根插着的细棍,挂一件破衣、戴一顶破草帽的草人,无精打采地在热风中招摇。麻雀是何等聪明的灵禽,一次两次判断失误之后,醒悟了,也就放心大胆地扑入稻田,先尝为快。这时候,此起彼伏的悠长的吆喝声突然从四周响起,那些妇人和小孩的声音,悠长之中有稚嫩也有细软,惊飞一群群麻雀。柳荫下搭起的草棚里,响起孩子香甜的鼾声;河畔水渠里,扬起顽皮小子泼溅的水花;杨柳树下,妇人在说笑声中,缝缀着过冬的寒衣,时不时的站起身,瞭望稻田的上空,追寻着鸟雀的踪影。
记得小时候读唐诗宋词,大半俱已忘却,只有宋人辛弃疾的《西江月》,倒是深深镌刻在心上:“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乡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辛弃疾不就是在在写吾村吗?初秋之夜,扫得干干净净的小院里,铺上一张芦席,孩子偎在妈妈的怀里,遥看将圆的高天朗月,念起初学的儿歌:“月亮爷光光,把牛吆到梁上。梁上没草,把牛吆到沟垴,沟垴响雷,把牛吆回……”坐在泉边捶布青石上的奶奶笑了:“长大了,戳牛跨骨吗?这娃娃,好没出息啊!”“打牛后半截也没出息呀!”从稻田放水回来的父亲刚踏上房阶,靠起铁楸,接过奶奶的话茬。再端上早已泡好的茶壶,一饮而尽,抹抹嘴,抱起他那将来有“出息”的宝贝儿子站在院边,看月色下那不知流了多少人汗水的百亩稻田,那里也有他的汗水,月色下变得越发金黄。浓郁的稻花香袭来,此起彼伏的阵阵蛙鼓声,小院石缝里秋虫的引吭嘶鸣,萤火虫的微光明明灭灭,也都被百亩稻田稻花的芬芳所陶醉了吧?我小时候一直为河湾的稻香而骄傲,以为那是吾村所独有。回来和朋友聊天才知道,河湾两岸,年年秋日,都沉浸在稻花之香中,路上行人,衣沾稻香,三日不去。
漫步在秋日的河湾田间,放眼望去,农人们收获了大片玉米、豆子和稻谷,随后又撒上一层化肥,拖拉机就开始进庄稼地了。几台拖拉机的屁股上都装了一副大铁犁,像老母猪吃食似的,闷着头,疵牙咧嘴,从地头吃到地尾,偶尔也会使劲嚼几下,吐出一串串庄稼根子,偶尔也会绊住腿脚,老在原地打转,逗得跟在后边的孩子们“哈哈”大笑。五叔狠狠踹了一下拖拉机说:“这可是我们的电牛啊!”居信叔问:“它是公的还是母的?”五叔想了想。非常严肃的回答:“都可以。”
其实,我心里盼望它是个母的,将来能生一大堆拖拉机。但是,五叔的回答有他的道理:“用不了三五天,这块地就要被别人租去了,这辆跟了他们家十几年的东方红牌拖拉机,也该退休了。”居信叔说:“你种地种的再好,撑死了一年也就赚个一两千块钱!可人家外出打工的话,一个月不管好歹,吃了喝了,每个人起码挣一两千块钱。要是两个呢?要是三五个棒劳力呢?”居信叔还想滔滔不绝地往下说,但被五叔眼睛的余光快速扫了一下,就立马闭了嘴。五叔的这个动作被我扑捉到了,但我早已不是懵懂的三岁小孩,我懂他的意思,更理解他积攒在内心的愁闷。五叔在心疼他的六七亩地呀!
这块地在村庄前面的河岸边,土地肥沃,而且水利条件好,肥的流油,一年两料,种啥啥好。五叔从他爷爷时就家穷,养了五个小孩,对四邻又是穷大方,加上他老实,做事有远见,加上他经营有方,产量年年翻番。因土地多,等到麦收一罢,男女老少种玉米的时候,他爸就开始发愁了:这个家不要看人多,但大人只有两个,其他的都是些“虾兵蟹将”,多一个能阵前“扛枪”的劳动力也没有!怎么办?听他婆说:“有地就等于有了命,不管好歹,先活命吧!”有了这话,他爷爷才不再发愁。
到了五叔他爸这一辈,这块地被分成了两块,割麦收秋,一年两季,不论怎么种,麦子还是麦子,玉米还是玉米,可就是不产金子银子。五叔他爸不甘心种地,早些年就开始跑车、跑生意,只要能挣钱,什么都干。五叔他爸后来果然发财了,他那块地也不知不觉就荒了,草比庄稼长得都高。五叔与长辈不同,考虑这考虑那,始终没有放弃这块地,算起来粮食没有少打,可就是不值几个钱。记得后来,当我也做了一家之主,我才知道当父亲的不易。父是天!有父在,才能保住全家人的命。可是,父靠什么呢?我想,他靠的是土地。这块地我守了许多年,当了许多年的农民,土里摸爬滚打,打了许多年的粮食,老远就能闻到我身上的那股子土腥子味儿,说一千,道一万,土地是父的命根子啊!所以,后来我们家虽然没有发财,但有吃有喝。五叔家虽然不是上个世纪的“万元户”,但成为这个世纪的“万元户”也不赖,也可以一边干庄稼活,一边给南方打工的儿子打手机了。这中间,他的姐姐弟弟们也分别成家,选择在广东、苏州、深圳打工,他也只身闯北京。家里的土地整个交给了堂兄。是啊,把地交给堂兄,比交给谁都放心。
堂兄经营这块土地,加上自己家的土地,一年下来,就可以把人累趴下,就可以手上脚上磨出血泡。堂兄嫂说:“干活容易上瘾,几十年习惯了,如果现在一天不干了,心里好像空落落地。”堂兄却说:“你干了一辈子,难道你还没有干够吗?地有啥种的?从小到大,我曾听说过这专家、那博士,就是没有听说过种地专家、种地博士!”嫂子说:“有道是有,但不像你那么称呼,大概统称为农牧工作者、技术员什么的……”堂兄非常不高兴地说:“不管他是哪一级的官,反正他们月月发工资,六十岁以后就可以退休了。”嫂子惊讶地叫起来:“娃他爸,你……个农民………你还想退休?”我看见,隆隆响的拖拉机犁过,大块大块的黑土在开花,四下里响起了一阵阵对堂兄与嫂子的嘲笑声。
我吃了一惊,堂兄为什么说要退休呢?堂兄不是一直很爱很爱种地吗?堂兄难道不再是原来那个当农民的堂兄吗?
我转过头来,望着正在侍弄土块的堂兄背影,把我的种种疑问转述给了嫂子。嫂子说:“我娃他爸在胡说八道哩,他是看有人在咱村包地,他图懒省劲儿,也想把地包出去………”
我问:“如果包出去。地就没有了。全家人吃什么?”
嫂子解释道:“你听我说完,你着急个啥?………他们按照一亩地五百元的价格,包这块地,因为这块地肥沃,人家才肯出这个价。换了别处,最多也就值个三百元。”
我急了,慌忙问:“才给那么点儿!他们打算包多少年?”
嫂子答道:“五年。”
我问:“你说这样包出去,吃亏不吃亏?”
嫂子一脸正色道:“依我说不吃亏,你看吧,这一亩地租五百元,我们家的五亩地一年就能挣两千五百元,你算算,你种庄稼,一季能赚多少?依我说,不少了!”
我想想也是,两千五百多元真不算什么钱,才相当于我表弟在广州打工一个月的工钱,才相当于我一篇小说的稿费,才相当于我们在雍城请朋友吃五桌餐的费用……两千五百元,一个非常普通甚至非常渺小的数字,在今天这个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时代,真的很容易被我们忽视。可是,对于堂兄一家来说,它真的能上升到两千多元的经济高度。这样看来,我自然也就理解了一个想退休的堂兄了,理解了嫂子她们对堂兄的嘲笑声了,更理解了对这块肥沃的土地的万般不舍和无奈了。
“堂兄,你真的想退休吗?”我迎着“隆隆”开过来的拖拉机高声问堂兄。
“你说说。”堂兄紧贴着前方一条犁线,急匆匆甩下了一句话:“我不退休行吗?”没有等到说完,人已经出去老远了。
我无法回答堂兄,即使和他面对面、眼对眼底喝酒聊天,我一时也会想不出什么话来的,更何况针对这么深刻的问题。
堂兄嫂子气得“哼”了一声,反问道:“你……退休!我倒要看看,你今天能退到哪里去?”
是啊,堂兄这辈子真的无休可退,反过来想想,中国的农民能退休吗?
不能!在今天的中国,什么人都可以退休,只有农民不退休,他们将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劳动到死,他们把打下来的粮食一车车送到城里,但事实上,他们又是这个社会收入最低的人、最穷的人……如果有一天,农民都放弃了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都不种庄稼了,也就是中国的农民都退休以后,我们吃什么?我很难想象在这个拥有约数千年农耕史的国家,大片的土地被农民放弃后的可怕后果,更难以接受,却又不得不接受堂兄这一辈人对于土地的不舍!
地,终于犁完了,堂兄和嫂子慌忙擦着犁刀上的黑土。土的墒情不怎么好,有些板结的黑土坷垃,稍稍大一点的,大约两块砖头那么大,用脚使劲踩几下也踩不开。我只好挑出其中的一块,两脚各自踩了黑土坷垃的两头,猛地跳起来,落下去,落下一瞬,我把整个身体的重量集中在了脚上,使劲压下……压下……土坷垃裂成了三四瓣。这一幕,被许多小孩看见了,嫌我身上没有劲,捂住嘴偷笑。
堂兄不知什么时候已走了过来,和我一起蹲在大片大片的黑土坷垃里,随便拣起了一块,端详了很久很久,然后一点点开始掰它,好像在掰一个白面馍馍一样,左一块,右一块,上一撮,下一撮,越来越细小,一朵朵,一片片,宛如下大雪。这时,堂兄不说话,两眼紧盯着手里的黑东西,时间仿佛不存在了,全世界只剩下了堂兄一个人,“哗啦”、“哗啦”、“哗啦哗啦”……
天说黑就黑了,隐隐约约之间,只看见前面晃动着三三两两的人影、牛影、架子车、拖拉机时不时颠簸着的轮廓。我摸着回村子的路,凭着印象向前摸,只是想抢先一步到家。
归途中,听见几个村民“唧唧喳喳”的声音,好像在议论土地包出去划不划算的问题,好像全都是“包出去拉倒”之类的想法。
归途中,好像他们有人辨别出了是我的脚步声,就有人在后边喊:“薛教授、大作家,什么风把你给吹回来的,最近咱村好多人都把地包出去了。你老伴的地包出去了吧?”
堂兄悄悄拿胳膊肘子捣了捣我,意思是别出声,小步前进。我也捣捣堂兄,狠狠扯了他的袖子……。我们的想法是一致的。
然而,我担心到家之后,那块几乎被堂兄掰碎的土地,明天还是不是属于他们家呢?
夜阑人静,我的脑海里翻腾不已,想起五拐子说的话:“你们城里人很厉害哦,吃农民种的这些菜竟然不得病?”
是啊,如今的农村出现了这样的“现象”。有的农民不吃自己种的菜。那些形状规则,色泽鲜亮,没有虫眼的蔬菜被一车车运进城里,而农民自己吃的菜明显有点形象不佳。
农作物有没有用过药,只有种植者自己清楚,但用药的原因谁都明白,“为了生存,为了轻松,为了赚钱”。市场经济中的不二法则,让农民更像商人。
农村已经变样,虽然都通上了水泥路,但春天少了蜜蜂,夏天少了蛙声,秋天少了虫鸣。如果连土地都没有生命了,人还会健康吗?
我常想,当人们吃着一桌饭菜时,你很难想象它们是如何被种出来的。除草剂让土地寸草不生,杀虫剂将昆虫赶尽杀绝,取代昆虫授粉的是激素,而化肥彻底改变了土地的酸碱度。因此,当你将饭菜夹入口中的时候,你可能是凶手、试验品或受害者。难怪人们不厌其烦地说,我国人口众多,只有更高产才能满足所有人的需要;另一方面正被低得离谱的菜价压得喘不过气来,纷纷想要逃离。不管从哪个方面来看,高产似乎都是重要的,否则就会有人饿肚子,就会有人亏本。记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化肥、农药进入中国,彻底颠覆了农民的耕种方式。除草剂会危害孩子们的神经系统,引起智力障碍,但它带来的好处却让农民无法抗拒。它意味着每天至少可以省下三分之一的时间干与农业无关的事情,因为除杂草也是田间最辛苦的劳动项目之一。与除草剂相比,杀虫剂的种类就更多了,因为虫子的生殖交替速度极快,在杀虫剂的筛选下它们也飞快地变化着,这似乎大大加快了杀虫剂更新换代的速度,它们的毒性一代比一代强,持续给消费者带来健康危机。因为我们太爱没有虫眼的“干净”蔬菜,而农民又大憎恶虫子带来的减产。
相比之下,化肥似乎听起来温和一些,但就土地本身来说,它所造成的灾难绝不亚于前两者。在我的印象中,二十世纪中叶,科学家们发现氮、磷、钾是植物最重要的营养素,这个惊人的发现造就了浓缩这三种元素的化肥,它们让作物长得更快,叶子更绿更肥嫩,施过化肥的植物就像是喝过兴奋剂一样疯长,增产幅度甚至高达十倍。然而化肥所带来的农作物高产,却大幅度降低了农产品的营养价值。这使现代人虽然不乏食物,却大都缺乏微量元素。对农民而言,增产更大的危害在于农产品大幅贬值,人们回不到以往的农耕生活方式,只能进一步追逐极度高产的工业化农业生产方式,让这种恶性循环愈演愈烈。
有一种化合物的到来比前几种更晚一些,它叫“催熟剂”,是一种类雌性激素,它会作用于花的雌蕊并造成“假授粉”的效果,使茄果和瓜类在没有昆虫的情况下也能结出漂亮的果子来。人们使用它,是以往农药的使用让田间不再有足够多的虫子为花朵授粉,反季节种植更需要依赖非自然的授粉方式,而催熟后形成的果实往往嫩且无籽,倍受人们的青睐。遗憾的是,这类激素对人体同样会产生作用,造成孩子早熟、男性女性化,并使更多女性患上癌症。
当我们把这些“神奇发明”用在农产品上,并使产量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时,我们却完全忘记了当初为什么要高产了。农民的收入没有比以前更高,人们的健康却受到了极大的威胁,还产生了土地的退化、水资源的枯竭、生态链断裂、重度污染等许许多多环境问题。这就像我看过的蕾切尔。卡逊《静静的春天》里描绘的场景:农药泛滥,昆虫肢解,土壤板结,花草带毒,水质败坏,殃及鱼虾,鸟禽瘫痪,走兽灭绝,世界上只剩下自私的人类,一片寂静与所谓的自由到来了。
我常想,自然之物,自有自然的解决办法,那就是回归“自然农法”……生态农业。生态农业不是单纯的“有机种植”,因注重与自然的协调适应和真正的可持续发展。我想,也许有一天,我们可以不再为食物安全问题而忧心忡忡,不必为发臭的土地和河水而烦恼,也无须为选择怎样的农药而绞尽脑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