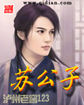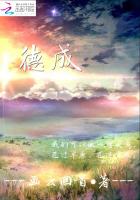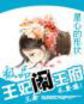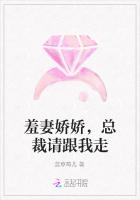大永三年(公元1523年),因国内战乱,幕府权力被大大削弱,以至于得到这一年与大明朝贡贸易勘合的,是日本的有力大名——大内家。
由于那会儿的日本还没到完全混乱的地步,因此拥有足以媲美幕府将军的大名也不多,粗略数来就两家:一家姓大内,一家姓细川,而明朝的贸易勘合也基本在这两家手里流转。
虽然老话说“十年风水轮流转”,可毕竟事关赚钱大业,因此细川家也不能由着他这么转去,在得知大内家拿了勘合之后,他们立刻决定也派出商队,前往中国参加朝贡贸易。
肯定有人会问,那么细川家没勘合怎么办?
没事儿,其实勘合是有的,只不过过期了而已。此时明朝在位的是明武宗朱厚照,而细川家手头上的勘合是之前明孝宗朱佑樘时代发放的,理论上是不能再用了。
但是细川家并不这么看,他们觉得这张勘合可以用,只是看怎么个用法了。
在说过期勘合的用法之前,我们先来简单介绍一下明代中日勘合贸易的一些情况。
这事儿的大致流程是这样的:首先,日本人带着勘合,领着船队自日本出发,在宁波登陆,然后由宁波的市舶司验过勘合跟货物之后,再北上去北京朝贡以及贩卖。
换言之,只要想办法让市舶司认可了这张过期勘合,那么就能顺利地进行贸易了。
至于认可的办法也很简单,行贿呗。
当时宁波市舶司主管叫赖恩,是个太监,爱财之名远播海内,所以细川家投其所好,派出家臣宋素卿前去塞钱。
宋素卿,原名朱缟,自幼能歌善舞长相出众,是个远近闻名的美少年。他有个叔叔叫朱澄,跟日本人做生意做亏了,没钱赔,于是就把漂亮侄子抵押给了对方,算是抵债。就这样,到了日本之后的朱缟改名宋素卿,还成了细川家的家臣,同时因为长相华美做事得体,还颇受重用。
说起来宋素卿代表细川家跟明朝打交道,那也不是第一次了,早在永正七年(公元1510年),他就以细川家特使的身份前往北京,谒见了当时权倾大明的“站皇帝”刘瑾,同时还赠上黄金千两,刘皇帝一高兴,还赏了他飞鱼服一套。
飞鱼服,就是明朝正服的一种,隆重程度仅次于蟒袍,一般只用于够一定级别的武官和锦衣卫。将飞鱼服赐予外国使者,绝对是开了前所未有的一个先例,但也由此可见这位宋素卿的外交能力的确不一般。
果然,在宋素卿的一番沟通和贿赂之下,宁波市舶司主管太监赖恩一口承应,表示别说你们细川家的勘合过期了,哪怕是没勘合,咱家也让你带着货物上北京。
于是到了朝贡的那一天,细川家和大内家的商船同时出现在了浙江的海域。
开始大内家的人还挺纳闷,互相之间议论说怎么那帮家伙也来了。等到上岸之后,更让他们看不懂的情况也发生了,那就是明明没有勘合的细川家,不仅顺利过了市舶司的开仓验货,而且在例行接待外国使臣的宴会上,他们的座位还在大内家之上。
大内商团的团长叫谦道宗设,是个很聪明的和尚,一下子就明白了问题所在,知道肯定是细川家使了钱。不过本着先礼后兵的规矩,他并没有当场发作,而是暗示市舶司主管赖恩,意思就是,赖公公我知道你收了钱了,也能理解你让没有勘合的细川家和我们一起去北京卖东西的行为,可毕竟我们才是有勘合的正主儿,你不能那么亏待我们吧?
赖公公还没发话,细川商团团长鸾冈端佐却开始冷嘲热讽了起来,说哎哟喂,你们大内家还真把自己当成名正言顺的使节团了?别忘了真正该拿着勘合来做生意的是足利将军家,咱俩说穿了都是一路人。
谦道宗设一下子就怒了,拍案而起。
鸾冈端佐毫不示弱,一脚踢翻了眼前的小桌子。
赖恩则一边喝着酒,一边表示你们要打出去打,外面地方大。然后还给细川家发还了武器——按照当时惯例,朝贡使节团所携带的武器,需由市舶司保管。
虽然这拉偏手拉得太明显,但谦道宗设丝毫不怵,因为保管武器对日本人根本没用,他们卖的商品里就有武士刀。
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多了,双方在门外拉开了场子,上演了一出全武行,因为大内家人多势众,所以细川家没打赢,逃了。
杀得兴起的谦道宗设一边下令全员追击,一边顺手点了一把火,把市舶司的宴会厅给烧了。
最后细川家众人一路逃到绍兴,然后躲进城里死活不肯露面,而闻讯追杀过来的大内家,考虑到强行攻城实在不可取,于是只好在城下大肆劫掠枪杀了一番后扬长而去。
在抢杀的过程中,他们还打死了前来追捕的大明备倭都指挥刘锦、千户张镗、执指挥袁班、百户刘恩以及士兵百姓若干。
这就是着名的“宁波争贡事件”。
事情发生之后,整个浙江为之震撼,明朝政府也极为重视,在查明原委之后,判了宋素卿死罪,然后又照会日本方面,要求他们交出在浙江撒野但已逃回国内的谦道宗设。
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战国乱世,足利将军家连勘合都被人冒领了,哪还有本事去抓大内家的人?于是也只能不了了之。
此次事件的后果应该讲是相当严重的,它直接导致了明朝方面作出废除浙江、福建两处市舶司的决定,接着又一口气停了日本之后十几年的朝贡贸易。
这又是一次因日本而影响到中国政府决策的事例。
可那又怎样?
虽然几乎所有人都觉得,宁波争贡是一起性质极为恶劣,后果极为严重的外交事件,可总体来讲这不过是一起无关痛痒的小插曲罢了,因为在明代,中日两国之间绝大多数的买卖都是靠走私来完成的。说难听点,几百年里的明日贸易本质上就是走私贸易,朝贡贸易废不废除,市舶司关不关门,都与大局无干,真要指望那十年等一回的勘合,还不如去喝西北风来得爽快。
不过凡事都有两面性,日本那边的战国时代对中国来说多少还是有点好处的。
比方让倭寇的战斗力大大减弱了。
早期的倭寇主要由日本人组成,这个之前说过,而要按出身成分划分的话,那么大致可以分为失地农民、破产商人以及失业武士——俗称“浪人”。
其中,失业武士象征着整个倭寇集团的最高战斗力,曾经有五十多个浪人出身的倭寇自浙江上岸,一路向北烧杀劫掠,导致中国数千军民死伤,一直打到南京城下,最后明朝方面实在是没了办法,不得已出动大炮,才将其镇压下来。
说实话这样的人要是来一千个,会发生什么就真的说不定了。不过好在自战国时代之后,因为日本国内战斗力和生产力日益紧缺,从而使得大批搞走私或打家劫舍的日本人纷纷回国,正儿八经地开始奔起了自己的前程。
可是这并不意味着就此天下无贼了,尽管日本人走了一大片,但大明东南沿海依然是匪患不绝,照样有人大规模地抢东西、放火、走私、掳人。
为什么日本人走了倭寇却还在?既然日本人都走了,那留下来作乱的是谁?
答案是中国人,以及包括日本人在内的其他一些外国人,如朝鲜人、葡萄牙人等等,但这些人所占的比例非常小,比方说日本人,若用《明史》的话来讲,就是:“真倭十之三,从者十之七。”
真倭,即真日本人;从者,则是其余的,其实就是中国人,你一定要觉得剩下那“十之七”是不远千里从欧罗巴赶来的葡萄牙人,那我也没辙。
也就是说,16世纪之后的倭寇,尤其是烧杀劫掠的那一批,绝大多数都是华夏同胞。
这并非瞎说。
话说有一位昆山人,被倭寇掳走,在船上当苦力,五十多天后逃走,跑到官府报案说遭倭寇绑架。
衙门老爷问他,倭寇人数多少,真倭几何?
回曰:倭寇两百余人,真倭十几个,其余的都是同胞。
两百个人里日本人二十个都不到,看来“真倭十之三”的说法还真是给了面子。
那么,到底是怎样的中国人才会去当倭寇呢?
有个姓郑的明朝书生是这样记载的:“凶徒、逸囚、罢吏、黠僧,及衣冠失职、书生不得志、群不逞者。”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去参加倭寇的,主要都是些地痞流氓、市井恶霸、逃犯、被罢免的官员,还有不得志不合群的书生,乃至宗教界败类。
比如倭寇界着名代表徐海,当年就是虎跑寺的和尚。
然而就是这群人,却把东南沿海闹得鸡犬不宁、怨声载道,几乎是所到之处无人生还。
最糟糕的是,因为倭寇杀得太狠了,所以很多受害者都觉得,与其自己天天这么被抢被烧,不如跟着他们一块儿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于是纷纷加入其中,这就使得倭寇的队伍迅速壮大,而当受害者成为加害者的时候,其手段往往更加残酷无道。
当时的东南沿海,基本上可以用这样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绝望”。曾有一个叫谢杰的人说过:“海滨人人皆贼,有诛之不可胜诛者。”
而时任南京刑部尚书的《金瓶梅》作者王世贞把话说得更绝:“自节帅而有司,一身之外皆寇也!”
什么意思?就是说除了总督巡抚之类的高官,之外全都可以认为是倭寇。
此外,他还用了“民寇一家”来形容当时的情况。
说到这里我们其实可以得出一个令人痛心的结论,那就是长期以来,被很多人当作抗日英雄崇拜的那些抗倭名将,诸如戚继光、俞大猷等人,他们的对手实际上大多是自己的同胞。
不过,话又得说回来,杀人放火的倭寇,毕竟是倭寇中的少数,大多数顶着这个名号的,不管中国人日本人,还是以干武装走私为主。
若是要在这些人里头找出一个值得一说的角色的话,那我想最合适的应该是一个叫王直的人。
对于这个人,评价趋向两极:喜欢的将其尊为毫不逊色于大航海时代任何一名冒险家的海贼王;而讨厌的,则直接以汉奸二字一言蔽之。
但世人认为王直是汉奸的唯一根据,仅仅只是因为他在做海贼的同时也跟日本人走得很近,可要是因为这个就把人当汉奸,那汉奸未免也太廉价了些。
王直,生于中国安徽,据说出生时,他娘梦见天上有星星陨落怀中。他年轻的时候虽然过得很落魄,但却一身侠气,乐善好施,仗义疏财,又文武兼备,所以深受周围人的信任,威望也很高。
自明朝嘉靖十九年(公元1540年)起,王直就跟着同乡徐惟学(徐海的叔叔)、叶宗满等人搞起了走私。一帮人先是在广东打造海船,然后再坐船游走于日本、泰国以及东南亚国家,走私贩卖硝黄丝绵等物品,赚了不少钱。
于是这就成了倭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