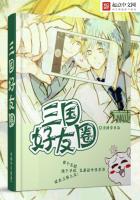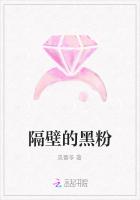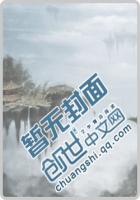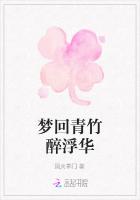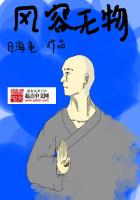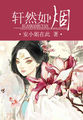事实上作为文章博士,藤原佐世当然知道阿衡到底有无实权,而他之所以要颠倒黑白提出那个惊世骇俗的结论,纯属是想拍一回马屁——既然藤原基经有心再矜持一把可又苦于找不到合适的由头,那就由自己来提供这个理论基础吧。
可他没想到的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藤原基经在听藤原佐世说完之后,第一个反应并非是暗自欢喜又能装一把矜持了,而是浑身毛发倒竖外加背脊阵阵发凉。
其实稍有历史常识的人还应该知道,所谓“位极人臣”这四个字背后的潜台词,实际上是“一手遮天”。
藤原基经是怎么做到太政大臣的我们这里就不详细说了,但即便是用膝盖也能琢磨明白,这家伙绝对不会是一盏省油的灯,其仕途过程一定满载了各种见不得人的黑历史。
但与此相对的,越是这种人,神经就越是敏感脆弱,只要稍稍听到一些或许会对自己不利的风声,就会防患于未然地大作起文章来。
更可悲的是,出身超级豪门藤原家的藤原基经,因为不需要像菅原道真那般靠考试来升官,所以对经史子集这种东西并无太深了解,所谓阿衡啊伊尹啊,也仅限于听过名字,至于详细的事迹,就全然不知了。
因此他把藤原佐世的话信以为真了,以为天皇要自己当关白实际上是想借升官之名,行收权之实。
藤原基经当时就怒了,撂下一句话:“既然天子如此不希望我掌权,那我就把这大权归还于他好了!”
一旁的藤原佐世瞬间就摸不着头脑了:这是怎么了?
次日,太政大臣藤原基经奏明宇多天皇,表示愿意接受关白一职,但与此同时,将不再处理任何政务。
于是天皇也傻了,这怎么就突然罢工了?
然后就让人去查,查了一圈发现原来是藤原佐世在搞鬼。
天皇还没来得及说什么,橘广相先拍案而起:“是可忍孰不可忍也!”
文化人一般最恨的,就是自己满腔热忱抖了半天书袋,自以为千古绝唱结果却被人歪曲成了垃圾,这在他们眼里堪比是杀父夺妻的侮辱。
所以橘广相要求和藤原佐世辩论,论题是伊尹阿衡到底是不是位高而无权。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纵然是藤原基经也明白过来,其实就是藤原佐世信口雌黄拍马屁,然后自己信以为真地小题大做。
可正因为事情已经发展到了这一步,所以绝对不能让步认输,即便伊尹拥有能够流放国王的实权,但在这风口浪尖上,咬了牙也不能承认这事,因为一旦承认橘广相说的是对的而藤原佐世说的是错的,那么自己这一罢工行为该如何解释?太政大臣藤原基经由于权欲熏心外加不学无术而上当受骗并大耍无赖?
于是藤原太政也不甘示弱,公开表示辩论就辩论。
这么一来橘广相倒有点困惑了,赶忙又翻了翻各种史书,确信自己掌握着真理之后,便也挺起胸膛,一副你要战我便战的架势。
辩论会的具体形式是这样的:橘广相和藤原佐世作为当事人,只负责亮明自己的观点,但并不参与辩论,详细的讨论交给九名以饱读经书而着称的博士,他们在一番论战后,将会各自投票选择自己所认为正确的观点,最后以票数多寡来决定胜负。
辩论的过程我们略去,直接说结果:9:0,藤原基经完胜。
这叫做强权战胜公理——博士也是人,大家都明白你把黑的说成白的没啥关系,但你要得罪了藤原基经那可是要遭殃的。
于是天皇只得被迫取消了先前发过的那道圣旨,接着再把橘广相给罢免。但与此同时,他也在日记里表达了自己万分不爽和屈辱的心情。
而藤原基经却并不肯到此为止,在橘左大弁被罢之后,他又进一步上奏天皇,要求将橘广相流放,以作为自己回来干活的交换条件。
这个实在忒过分了,因此天皇断然拒绝。
所以藤原基经继续罢工,双方就这么僵持了起来。
这种最高权力层之间的勾心斗角,在古今历史中很常见,从表面上来看跟此时正在讃岐过苦日子的菅原道真没有一毛钱的关系,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首先,菅原道真他爹菅原是善跟藤原基经有点交情。
其次,那个藤原佐世其实是道真的学生,他能当上文章博士,还亏了自己老师的举荐,不仅如此,这人实际上还是菅原家的姑爷,他老婆是菅原道真的女儿。
因为上述的这些关系,故而道真想要插手这次中央斗争也就名正言顺多了。
仁和四年(公元888年)七月,菅原道真修书一封,寄给了藤原基经。
信上先是对自己的倒霉女婿兼学生藤原佐世在京城弄出那么大的骚动表示了歉意,这纯属自己管教不严;接着又对藤原基经本人进行了高度赞扬,基本上能想出来的褒义词都给砌上了,活生生地把一个权奸给夸成了风华绝代的圣人君子,同时还不忘标榜一下自己,大意是我不在京城期间天子全靠您辅佐了,当然这话说得极为隐晦,并没有让基经本人感到任何不快;最后,道真笔锋一转,表示太政大人这几个月来您也该闹够了吧?差不多是收手的时候了吧?
之后,他再上了一道折子给天皇,表示藤原基经是难得的栋梁之臣,这次事件纯属意外,自己已经写信劝说太政大臣了,希望皇上在合适的时候给他一个台阶下,正所谓君臣和睦国之大幸。
宇多天皇当然是巴不得这事早一分钟解决,对他来讲给个台阶下压根就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没有台阶可下,藤原基经本人一直窝在家里闭门不出,满朝文武也无人敢出声劝架,现在唯独这个小小的讃岐守站了出来,也不知道他能不能劝得动太政大臣。
而另一方面,其实藤原基经也早就不想这么僵下去了,这家伙的初衷真的很简单,就是想单纯地摆个谱,他自己都没想到会闹成这副模样。自打双方卡在那儿之后,基经无一日不在等着天皇能来给自己一个台阶——比如学下刘备三顾茅庐什么的,可惜等了快几个月了都没等到,无奈之下只好为了面子而继续痛苦并僵持着。
现在既然菅原道真来信请求自己鸣金收兵了,那就干脆顺坡下驴买他个面子吧——谁知道这家伙是不是天皇背地里派来的求和使者?即便不是,他也不是外人,自己不仅跟他爹菅原是善勉强算个朋友,心腹加一族远亲的藤原佐世还是他的女婿,就算听他一回也不丢份。
数日后,藤原基经上奏天皇,表示自己不想再追究那橘广相了,而且也愿意以关白兼太政大臣的身份重新走出家门回到工作岗位,和以往一样地辅佐天子处理天下政务。
宇多天皇很感动——主要是对菅原道真。
因为此事的本质是藤原基经因为某件无聊的小事,和天皇闹了数月的别扭,不仅赶走了重臣橘广相还罢工示威,就在这紧要关头,讃岐守菅原道真一封信就解决了事情,恢复了和平。
你是天皇你也会感激他的。
宽平二年(公元890年),任期已满的菅原道真回到了阔别四年的京城,之后被任命为藏人头。
藏人头,就是天皇的秘书,主要工作是负责天子与大臣之间的各种沟通。
官不大,但地位很特别,属于皇上身边的贴心人。
宽平三年(公元891年),一代超级大权臣藤原基经因病医治无效在平安京去世,享年55岁。
这对于菅原道真而言堪称是春天降临的标志,因为原本一手抓着行政用人大权的基经现在蹬腿了,那么各种权力自然也就回归到了天皇手里,而天皇在掌权之后,第一个要提拔的,自然是当年帮过自己大忙的道真了。
宽平五年(公元893年),菅原道真出任参议。
所谓参议,系太政官一员,唐名平章事、谏议大夫,有参政朝议之权。简单而言,就是拥有能和天皇以及其他王公大臣坐在一个屋子里,讨论并参与国家大事的权力了。
也就是说,道真就此步入了最高权力的核心层。
他终于有机会来实现自己的梦想了。
在菅原道真的辅佐与建议下,宇多天皇开始把眼光投向了民间,为了更好地了解老百姓们到底过着怎样的日子,他还临时设立了问民苦使一职。
问民苦使其实是地方检察官,早在孝谦天皇时代就有了,不过那时候主要是为了监视藤原仲麻吕有没有勾结地方土豪造反,而宇多天皇时则更多的是想知道民间的具体情况。
不管哪个时代,民间疾苦总是触目惊心的,所以天皇在第一次知道了自己的子民到底生活在怎样的环境下后,痛下决心地表示,自己要通过努力,让老百姓们过上能吃大米能喝肉汤的好日子。
可惜没有了下文。
天皇其实也就是意思意思,所谓的努力,充其量是希望手底下那群当官的去努力,他自己本身实际上也就是三分钟热血,沸腾完了就该干吗干吗去了。
当年春夏,宇多天皇表示想派遣唐使去大唐,学习一下先进文化技术,最好再跑长安淘点儿稀罕宝贝回来。
纵观此时的日本,综合才华学识地位来看,最具备带领诸遣唐使赴唐,担任遣唐大使职务的,唯有菅原道真。
道真本人很兴奋,不是因为能当大使,而是觉得废除大唐制度的时候到了。
宽平六年(公元894年)九月十四日,左京大夫、左大弁兼参议兼第二十任遣唐全权大使菅原道真上奏宇多天皇,要求取消本次赴唐计划,不仅如此,他还认为,遣唐使这东西本身,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在奏折中,菅原道真表示,当年如日中天不可一世的大唐王朝如今已然是残花败柳了,说难听点就是坟中枯骨,灭亡就在眼前,所以压根就不再具备让日本学习的价值,这是其一;其二,大唐多年来藩镇割据四处战火,乱得很,一大堆日本人去了难保不被人砍死。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这条不在奏章上,而是菅原道真当面跟天皇说的,他提出了一个截止到当时,没有一个日本人想到或者敢说出口的观点,那就是迄今为止,日本所谓的以大唐为标杆全面仿照大唐,无非是水月镜花。这种不考虑本国情况一味追求模仿外国的做法,恰恰是导致了自己数百年来又穷又弱的根源。
综上所述,日本要做的,是放弃效仿大唐,通过走自己的道路来实现强国之梦,而实现这一梦想的第一步,就是废除遣唐使。
在我看来,如果没有这第三条,那么菅原道真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能够审时度势的实用主义者,最多被赞一声头脑聪明,冰雪无敌,而有了那第三条,那道真就不愧是被誉为文神的男人了。
大唐即将完蛋,这在当时的日本属于公开的小秘密。尽管在很多历史读物、官方资料甚至是教科书上写着,日本实际派遣成功的最后一次遣唐使是在承和五年(公元838年),此话虽不能说错,可事实上在日本贞观十六年(公元874年),平安京方面为了采购香料、草药等物,特地派遣了以大神己井、多治安江为首的使节团赴唐,虽然他们并没有被算在所谓的“二十次遣唐”名单里,但严格来说,其实是最后的一批遣唐使。
其中,副使多治安江在回国后就表示,大唐虽然还是大唐,但早已各种乱象丛生,估计用不了多久,就会出大事,再用不了多久,兴许就该灭亡了。
这话他逢人就说,不到三个月,便一传十十传百地变成了平安京里众人皆知的秘密。
果然,公元875年,河南长垣爆发了王仙芝民变。三年后,王仙芝战死,余部在安徽亳州和冲天大将军黄巢的军队合并一处,为推翻唐朝夺取天下而共同奋斗在了一起。
这位黄大将军的事迹在此我就不说了,一是和主题不符且篇幅不够,二是不好说也说不好,反正公元881年的时候,黄巢军攻入了长安,其本人称帝,建立大齐政权,年号金统,而唐皇僖宗则不得已逃往了巴蜀之地。
虽然黄巢在公元884年兵败身死于泰山,唐僖宗得以全身回到了长安继续当皇帝,但经过这么一闹,大唐实际上算是彻底没戏唱了。
黄巢之后的事情我们前面都说了,唐朝那边算是回光返照似的稍微平稳了一些,于是宇多天皇又想起遣唐这茬儿了,连封大使的圣旨都下了,结果却因为大使本人出来当横,故而终究没有去成。
不仅没去成,在菅原道真的力谏下,天皇又下了一道圣旨,表示从今往后再也不派遣唐使了。就这样,这一延续了三百年的交流活动最终变成了历史。而菅原道真也成了名义上最后的遣唐使。
公元907年,朱温废唐哀帝,建立大梁,唐朝正式宣告灭亡。
而另一边,在成功迈出了第一步后,菅原道真意气风发,准备再接再厉地大干一场。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堪称是他终生对手的人出现了。
那人的名字叫做藤原时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