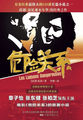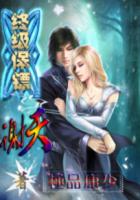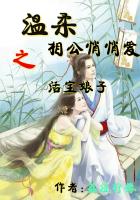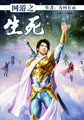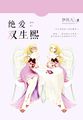显而易见的是,巴黎和会不是公平的辩论会,来参会的,都是为战利品撕扯的豺狼。尽管欧洲列强跟日本有矛盾,不过鉴于日本此时的实力和影响,谁会因为中国的主权问题去开罪日本呢?日本的要求得到了英、法的支持,美国虽同情中国,又不敢不尊重列强的意见。尽管会前相对超脱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了很多有关正义和公平的言语,调高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的期望值,但在实际操作中,即使作为大会主席的威尔逊,无论是在美国国内,还是在巴黎和会上,都不得不为某些事情作出妥协,有时候甚至陷入孤立无援的可怜境地。威尔逊率先倡导的国际联盟得不到自己国会的认可,在和会上他又不能不自食其言地牺牲弱小国家的利益,以换取列强之间的团结。当日本强硬地坚持占有德国在山东的各项权益,并以退出和会相威胁时,威尔逊想出的唯一解救办法就是暂时实行五国共管,之后再谋求交还给中国。然而,即使如此妥协,也难行得通。
4月22日,美、英、法三国首脑约见中国代表团,由威尔逊向中国代表团表达会议决定方案,基本同意中国提交的说帖,只是德国在山东的有关权益转交给日本:“日本将获得胶州租借地和中德条约所规定的全部权利,然后再由日本把租界地归还中国,但归还之后仍享有全部经济权利,包括胶济铁路在内。”威尔逊解释说:“现在提出的这个解决方案,最高会议希望能被中国接受,它也许不能令中国满意,但在目前情况下,这已是所能寻求的最佳方案了。”中国代表团竭力争辩,要求由德国直接向中国归还夺去的权利。争辩毫无效果,会议依然把方案列入巴黎和会的对德和约。
结果如此糟糕,中国代表力争之后,也只得徒叹奈何。中国谈判代表顾维钧表态只有得到政府的直接命令,才会在和约上签字。“我希望他们不要让我签字,这对我来说无异于死刑。”
5月1日,中国谈判首席代表陆徵祥电告北京政府和会的进程,他在给外交部的密电中提出三种解决办法:其一,全体代表离会回国;其二,不签字;其三,签字,但注明中国对山东问题条款不予承认。陆徵祥同时附上自己的意见,他认为,第一、二种都不现实,只能采取第三种。也就是说,陆徵祥主张有条件签字。不过让陆徵祥和北京政府都没有想到的是,在他拍发电报跟北京政府商讨最后方式之时,同在巴黎的梁启超已经在几小时前将情况发给国内,从而一发不可控地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
很难判断梁启超行为的全部动机到底是什么。梁启超的初衷,是想通过向政府和国民发出警告,要求他们向和谈代表施压,令其千万不要在和约上签字,爱国之心油然可见。不过梁启超在北京政府没有形成最后决策之前,将消息提前公布,似乎有超越程序之嫌。因此,梁启超的行动,被一些人认为是对于北京政府疏远和抛弃他的某种报复。
5月2日的《晨报》顷刻售罄。原先一直激昂澎湃,并且指望从巴黎和会分得一杯羹的中国人,好像被从头到脚浇上了一大盆冷水,一个个变得激愤起来。众议院在王揖唐主持下召开会议,决定向内阁施压。国民外交协会也作出几项决定:5月7日为国耻纪念日,在中央公园召开国民大会,如巴黎和会不能同意中国的主张,即请政府撤回专使。雪片似的电报发往巴黎中国代表团,警告代表团不得在巴黎和会公报上签字。国民外交协会在电报中干脆警告陆徵祥:“公果敢签者,请公不必生还!”
中国在巴黎代表团遭受到了巨大压力,即使是驻地外也经常有留学生示威。弱国外交的两难境地,这些代表算是真正体会到了。虽然战后巴黎在表面上一如既往地宁静平和,不过这些来自东方古国的代表们却如暴风雨前的蚂蚁一样,彻底乱了方寸,慌张无助,无所适从。
杜威来到中国
五四运动爆发前几天,也就是1919年4月30日,有一件事情对于中国知识界来说,尤为重要,当代最着名的美国大哲学家约翰·杜威应中国五所学术机构的联合邀请,由日本乘船抵达上海,开始了对中国的访问和讲学活动。踏上中国之后,上海的一切,让杜威感到很新鲜:鳞次栉比的西式小楼让人想起纽约长岛;街道两旁种满了欣欣向荣的植物;白色的玉兰花尽情绽放;南京路的晚上灯火闪烁,行人熙熙攘攘;黄浦江上,破旧的小渔船与远洋巨轮交错而过;大马路上,人力车夫们拉着洋车在小轿车中穿梭。除了比较多的黄色面孔以及相对杂乱之外,这个东方城市,跟美国的海滨城市并没有太多不同。至于北京,这里没有西方大都市里街道上那种拥挤和匆忙,所有人不论步行或者车,都表现得庄重沉稳,不慌不忙,仿佛自己相当了不起。大街上一簇簇的人,有的步行,有的骑马,有的乘着黄包车,中间混杂着驴车、骆驼队等,仿佛被赶往市场售卖或屠宰的成群牲畜。当然,也有着为数并不少的汽车,所有一切会使人产生一种印象,就是他们能够完美地控制行动和闪避。至于这座城市的表面,它体现出的力量和永恒,它破败中显示出的庄严、神秘,以及城墙的大小和规模,给杜威留下深刻印象。五四运动爆发那两天,杜威由陶行知等陪同,在南京江苏教育会会场,先后作了两场名为“平民主义的教育”的演讲,千余青年冒雨赶到现场聆听。两天之后,杜威知晓中国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又目睹中国宏大的学生运动在各大城市风起云涌,这位温文尔雅的西方知识分子十分震惊,由此感慨说:“这是一个奇怪的国家。……从某些方面说来,他们比我们有更多的民主……当舆论像这样真正表达出来时,它却有着显着的影响。”在中国讲学期间,杜威对于中国学生和社会运动表示了极大的关注,他希望通过眼前的事件,更进一步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人,了解中国文化。当中国学生希望他能在中国多待一些日子时,杜威表示出很乐意,他向哥伦比亚大学请假一年,后又续假一年。这样,杜威就有了两年零两个月之久与这个古老国家近距离接触的机会。
作为美国最知名的思想家,杜威在中国受到了热烈欢迎,这也反映了转型期的中国知识界对于新思想的饥渴,在很多中国知识人看来,西方新思想就像阿里巴巴的咒语一样有效。在中国的两年多时间里,杜威的足迹遍布奉天(今辽宁)、直隶(今河北)、山西、山东、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广东、湖北、湖南等十一个省和北京、上海两市,还应聘在北京大学担任客座教授一年。在学生胡适、陶行知、蒋梦麟的安排下,杜威马不停蹄地在教育部礼堂、清华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地作了十六次社会与政治哲学讲演,十六次教育哲学讲演,十五次伦理学讲演,八次思维类型讲演,三次关于詹姆士、柏格森和罗素的讲演。在湖南演讲期间,有一个叫作毛泽东的青年人认真倾听了杜威的讲座,不时写下笔记。这个青年当时在湖南开有一家书店,杜威的书和讲义全在他撰写的推荐书目里。后来,这个青年成为对中国现代影响最大的人。
不过杜威的讲演却让很多狂热的听众失望。这个被蔡元培誉为“美国孔子”的哲学家尽管光环明亮,但他实在不算一个优秀的演讲家,甚至不算一个很有魅力的知识人。杜威的演讲结结巴巴、拖拖沓沓,穿着也松松垮垮、邋里邋遢,毫无大学者风范。不过因为他的号召力,也因为其“科学权威代替传统权威”的主张,所到之处仍引起轰动。杜威每一次讲演,都整理成文字发表在《晨报》、《新潮》等报刊上,之后还汇编成书,由北京晨报社出版,每版印数都达一万册,离华前再版了十次,算是一个惊人的数字。杜威是典型美国思想的代表,不看重权威,讲究实际的认知和效度。在这些讲演中,杜威不厌其烦告诉中国人,现代西方文明的精髓在于精神文化,中国人若想从西方得到启示,就得从这一点着眼,改造自己的民族精神。杜威还毫不客气地指出了传统中国文化的痼疾所在,为中国人表现出来对国家问题的冷漠而震惊。在上海他问及一个中国人对日本占领“满洲”的看法,后者神色自若地答道:“哦,那是满洲人的事儿。”在北京,杜威看到一个行人被马车撞翻在街道上,受伤很重,但行人却不予理睬,最后还是一群外国人把伤者送到医院。这两件事让杜威觉得,中国人的冷漠属于一个民族的心理习惯。
对于中国的现状以及青年的任务,杜威虽然十分注意讲话的分寸和礼节,但也一以贯之表现了自己理性和客观的态度:“学生以学为目的,在于能以聪慧的爱国精神输入于政治。所研究追求的,都必须是为了增进国家秩序的稳定。务必做一分事,对国家就有一分利益。决不可感情用事,需有目的、有方法、有决心,志之所在,往而必达。否则五分钟的热血,固然能痛快一时,但如火药爆发,转瞬即灭,又如水汽蒸发,立即消散。但若加以智慧,则火药可以制成枪弹,水汽可以转动机械。其利益是无限的。更进一步讲,我们学界中的人,可以发扬自己的智慧,将社会各方面组成得像机械那样,一轮一钉互相组合,就能发挥极大的作用,如果拆散开来,齿轮螺钉,互不相关,那就成了废物。所以必须有正当团体,互相帮助,才可达到最好的目的。”对于学生的爱国热情,杜威也持肯定态度,但重点在于爱国热情的转化,杜威说:“大学学生为国家尽力,不顾利害,勃然发动,组织极大的团体,要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旅华外人见此举动,深表同情。这是共和国国民所应有的举动。因为共和国家的兴亡,责任全在国民。所以世界上无论共和专制,建设各种事业,全赖人民自己去办。这对于共和国尤为重要。……但欲有此共和的精神,必须有完善的教育,始可养成此真正共和的精神。”杜威的中心意思,还是劝慰学生要注意情感和理性的转化,风物长宜放眼量,对于历史进程,急躁不得。杜威说:“五四运动以来,我想学生比前应当更热心求学。他们因外交问题,激动爱国心,所以有新动机、新兴趣,对于学问自然更亲切有味了。爱国的动机又大,欲救同胞之心又切,对于进德修业自然欲罢不能了。总而言之,理智和情感不是相反,而是相成。情绪能帮助理智,鼓动理智,不至流于空虚或知行不一;理智能启导情绪,坚固情绪,不至流于盲目妄动或虎头蛇尾。……说到爱国,也要情智互用才好。救国救民,谈何容易,方法万千,各需专门知识,能够单依感情做事吗?要是单有感情而无知识,想讲卫生而不知怎样防止疾疫,想做买卖而不懂怎样经营店务,还有成功的希望吗?所以感情必须受理智的启导。若说感情在理智之先,未尝不对,因为感情是行为的原动力,但是一到实行,知识就更重要了。……所以使感情坚定,要有知识,问题看清楚了,然后能始终如一。”
杜威还强调,学习外国经验,要根据本国的国情和需要。杜威说:“吾人试观中国的教育,实根源于日本,是直接模仿日本的教育,间接模仿德国的教育,而不懂得要确定一国教育的宗旨和制度,必须根据国家的情况,考察国民的需要,而精心定之。决不可不根据国情,不考察需要,而胡乱地仿效他国,这是没有不失败的。这一点是中国一般教育应该注意的。”他进一步说:“一国的教育决不可胡乱摹仿别国。为什么呢?因为一切摹仿都只能学到别国的表面种种形式编制,决不能得到内部的特殊精神。况且现在各国都在逐渐改良教育,等到你们完全摹仿成功时,他们早已暗中把旧制度逐渐变换过了。你们还是落后赶不上。所以我希望中国的教育家一方面实地研究本国本地的社会需要,一方面用西洋的教育学说作为二种参考材料,如此做去,方才可以造成一种中国现代的新教育。”
作为旁观者的杜威,在中国期间,还见到了民国一系列事件的参与者和操纵者孙中山。1919年5月12日,在上海的孙中山亲赴沧州别墅,前去拜访杜威博士,并共进晚餐。颇有共同语言的两位东西方名人有了一次鲜为人知的会晤,并就哲学话题“知行合一”展开探讨。孙中山格外看重他与杜威的这一次见面,在《孙文学说》一书中,孙中山提到了与杜威会面一事。他说:“当此书第一版付梓之夕,适杜威博士至沪,予特以此质证之。博士曰:‘吾欧美之人,只知知之为难耳,未闻行之为难也。’”孙中山复述当初的谈话之意主要是以杜威的话作佐证,来证明自己所倡导的“知难行易”的正确性。杜威博士同样看重他与孙中山的谈话,第二天,杜威在给女儿的信中也讲述了当时的情景:“昨晚我与前总统孙逸仙共进晚餐,席间我发现,他是个哲学家。他新近有本着作即将出版,他认为,中国的弱点在于人们长久以来受制于古训‘知易行难’。他们总是不愿采取行动……所以孙先生希望通过他的书,引导中国人形成‘知难行易’的观点。”从此信的描述中可以发现,杜威对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有着浓厚的兴趣。杜威很快就发现,“知”与“行”对于中国来说,不仅是一个哲学问题,更是一个异常复杂的实践问题。
在中国的两年经历,使得杜威对于这个东方古国多了一份深刻的认识,除了对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有所了解之外,杜威还意识到美国和中国在认识方式上的差距,对于中国的事态保持着某种迟疑和期待。或许,在他看来,中国人更喜欢的,是跟他们有着同样君主专制的俄国人的方式,这也使得他后来对中国走向找到最根本的理由。在杜威看来,中国最好的策略,是给这个国家时间,要有耐心,让中国人慢慢解决自己的问题,让中国文明一步步转化。
与杜威来中国时爆发五四运动一样,同样具有巧合意义的,是杜威离开中国的日子——1921年7月11日,在中国盘桓了两年之久的杜威从上海乘轮船离开中国。恰巧在那些日子里,在上海,秘密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这个国家变得越来越激越,与杜威及其倡导的一切渐行渐远。这个东方古国,在最初选择以美国为师之后,开始慢慢挣脱美国的影响,与另一个熟悉而陌生的北方大国越来越近。
那个春天的人与事
波澜壮阔的1919年春天,作为教育部官员的鲁迅忙碌着两件事情:第一是在已客居七年的北京寻找一处大宅子;第二就是举家迁进京城。绍兴的祖宅已经出卖,必须在1920年春节前交出老宅。因此,鲁迅整个上半年都在四处奔波,寻觅适合的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