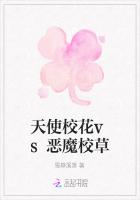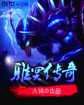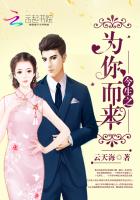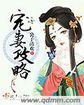《时代》选择吴佩孚作为第一个登上封面的中国人还有另一个潜在的原因——《时代》的创办者之一亨利·卢斯就出生于吴佩孚的家乡山东登州(今蓬莱)。吴佩孚生于1874年,二十四年后,卢斯也降临在登州一个美国传教士家中。一直到十四岁,卢斯才离开山东前往英国求学。在卢斯眼中,吴佩孚算是他的“老乡”。后来,卢斯和他的耶鲁同学布里顿·哈登从巴尔的摩《新闻报》双双辞职,并于1923年3月3日推出了第一期《时代》。因为卢斯的生活背景,他总是情不自禁地将目光投向那一片西方人尚觉陌生的东方土地。吴大帅,就这样出现在创办第二年的《时代》封面上。曾在上海主编英文刊物《密勒氏评论报》的美国人鲍威尔后来评价说:“从1922年到1928年蒋委员长建立南京政府之前,是中国的军阀混乱时期,在这一混乱的阶段,吴佩孚比其他任何人更有可能统一中国,在许多方面,他都是一个能干而有个性的人物。”
这一期《时代》出街之时,上海爆发了直系军阀齐燮元与皖系军阀卢永祥之间的争夺战,第二次直奉大战也一触即发。在此之前的1922年第一次直奉大战,吴佩孚率直系军队曾大获全胜,奉系军队撤回关外。此次张作霖率军南下,吴佩孚再度坐镇北京,调遣二十五万大军迎战。更多人相信,吴大帅获胜的历史将重演。并且,“八方风雨会中州”的吴佩孚会重拾武力统一中国的大旗,领导一场针对各地方军阀的征战。“吴将军,中国的最强者”——《时代》在封面上引用这几个字时,反映出的正是这一判断。吴大帅镇定的神态,仿佛透露出这样的信息:一个具有儒将风度的最强者,有可能决定中国未来的政局。
然而,让《时代》及其大多数读者大跌眼镜的是,吴佩孚登上《时代》封面不到一个月,就从声名的巅峰跌落了下来。这个被称为“中国最强者”的吴大帅遭到了别人的征服,从山顶一下子跌入深渊。
冯玉祥釜底抽薪
现在回首中华民国北京政府的历史,可以把1924年看作一个转折点——如果说此前局面还在控制范围内的话,那么,到了1924年,形势急转直下,苏俄加大了对于南方国民党的直接支持力度,局面变得为北京政府越来越不可控了。5月15日,外交总长顾维钧在北京的家中发现了炸弹,侦察人员没有查出结果,只是怀疑与苏联或者日本有关。当然,南方的国民党也是怀疑对象。26日,孙传芳也遭到炸弹的袭击,虽然没有危险,不过意味国内形势越来越紧急了。
1924年9月3日,最富庶的东南地区爆发了齐燮元与卢永祥之间的战争,双方各投入六万军队,激战于浏河、黄渡一带。冲突在于对上海的争夺;冲突的背景,是由于齐燮元归属直系,卢永祥属于张作霖、孙中山以及段祺瑞的三角联盟。围绕这一战事,《时代》报道说:卢永祥将军,浙江督军,曾任淞沪护军使。齐将军的敌人。他约五十七岁,在任浙江督军之后,他曾任命何丰林为淞沪护军使,而上海并不在他的地盘上。何丰林,任位于江苏地盘上的上海淞沪护军使,约四十七岁,受卢将军的指挥。
江浙战争很快引发了吴佩孚和张作霖这两大对手之间的武装冲突。江浙战事爆发的第二天,也即1924年9月4日,张作霖决定率兵入关,并发表了声援浙督卢永祥和讨伐直系的通电。5日,孙中山也在广州召集军事会议,决定北伐,命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职权,兼任广东省长。北伐军兵分两路:湘军总司令谭延闿任北伐军右翼总司令,入江西;军政部长程潜任左翼总司令,入湖南。军政府同时发表宣言声讨曹锟吴佩孚,声明此战不仅在覆灭曹吴,尤在使无同样继起之人,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9日,下野的内阁总理段祺瑞在天津通电讨伐曹锟。15日,张作霖乘江浙战起,率十七万大军入关。奉军分六路出动,第一军司令姜登选,副司令韩麟春;二军司令李景林,副司令张宗昌;三军司令张学良,副司令郭松龄;四军司令张作相,副司令汲金纯(丁超);五军司令吴俊升,副司令阚朝玺;六军司令许兰洲,副司令吴光新;张作霖自任总司令,号镇威军,设大本营于锦县(一、三路为主力,进攻山海关,四路为预备队,余均进向热河)。直奉第二次战争爆发。
有人在评价1924年下半年的形势时这样认为,第二次直奉大战大打出手的各方,其实都有着列强的背景:孙中山北伐的支持力量是苏联;张作霖背靠日本;吴佩孚身边或隐或现的力量则是英美。不过他们之间的关系又是错综复杂,很难一一对应。面对东部、南部以及北方的同时夹击,北京政府的曹锟与吴佩孚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曹锟发出讨伐令,以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王承斌为副司令,分前线三军,后援十路,共计二十五万大军应战。9月17日,自洛阳赶到北京的吴佩孚走马上任,召集直系大将王承斌、冯玉祥、王怀庆、陆锦等,在中南海的四照堂会商对奉军的作战计划。后来冯玉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提起这次着名的“四照堂点兵”,十分轻蔑地写道:
四照堂四面都是玻璃窗,电灯明如白昼,厅中置一长桌,挨挨挤挤,坐满了六十多人,大家坐了许久,才听到有人大声报告说:“总司令出来啦!”接着,吴佩孚摇摇摆摆走到堂中,且看他那副打扮:下面穿着一条白色裤子,身上穿的是紫色绸子的夹袄,外面一件黑色坎肩,胸口敞着,纽子也不扣,嘴里吸着一根纸烟。他走到座上,即盘腿在椅子上坐下,斜身靠着条桌,那种坐法,宛似以为懒散的乡下大姑娘!
接着,吴佩孚又念各路军任务,命令下完,吴即站起来说:“没有了吧?我们就这么办吧!”此时海军总长连忙站起来说:“报告总司令,命令上没有提到海军,我们的舰队怎么办?”吴答道:“哦哦,海军没有提,在命令上添一条吧,你们自由巡弋,以防意外。”航空署长也站起来说:“还有我们空军呢,怎么办?”吴又哦哦连声,说:“也添上一条,你们随时准备,相机出击。”接着,其他没有分派任务的将领也相继请示,吴佩孚搔了搔头,不耐烦地说:“这样尽着往下添,还成命令吗?今天就这样了,散了吧,散了吧!”大家才一哄而散了。
从这一段文字的描写看,吴佩孚哪里像一个具有现代思维和人文思想的扞卫共和的军人呢,分明是古代战争冷兵器时代的将军。冯玉祥极其不屑地评价道:“这样重大的事,办得如此轻率儿戏,吴之鲁莽灭裂,往往似此!”根据很多人的说法,吴佩孚与冯玉祥一直面和心不和,吴佩孚一直瞧不起冯玉祥貌似忠厚背后的多变和多虑,冯玉祥也对吴佩孚的神神鬼鬼心存看法。除了气场不合之外,双方还为河南的权力明争暗斗,不过至少在表面上,双方并没有失去和气,由于吴佩孚地位较高,冯玉祥更多是谦恭回避,唯恐激怒玉帅。吴佩孚除了经常表现对冯玉祥的不屑外,还对冯玉祥暗地里的扩张进行严厉压制,这也让冯玉祥愤懑压抑。冯玉祥对吴佩孚四照堂会议的描述,明显有丑化和戏谑的成分。不过可以管窥的是直军计划安排的匆忙和随意,以及吴佩孚过于传统的思维方式,形同话本小说般的做事风格。跟吴佩孚的行事风格一样,那些手握重兵的督军们,尽管有着某种程度的新思想,但总体上毕竟属于旧时代,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很大程度上带有那个时代的影子。以这样的理解力和作派,指望他们来操作和拥护民主宪政,结果可想而知。
这一次直奉大战远非四年前的直皖战争及两年前的第一次直奉大战所比,双方倾巢而出,张作霖出兵二十五万,吴佩孚出兵二十万,两军在热河、山海关等地正面交锋。当得知奉军的前线指挥是少帅张学良时,吴佩孚不屑地说:“张学良是个小毛孩子,我看他就是一个花花公子,上次在北京,他也是成天跳舞。他懂什么打仗!这次我们一定要痛击东北军,活捉张学良!”手下的人提醒道:“张学良的军队是张作霖的王牌军,听说他的装备都是从日本买来的,武器很好啊!”吴佩孚轻蔑地回答:“他小孩子能带什么好兵啊,武器好是不是,那我就缴了他的兵器!哼哼,省得我们到处买了!”吴佩孚自负地跟手下人开玩笑:“抓了张学良,我该怎么处置啊?”见手下人无从回答,吴佩孚幽默地说:“我根本看不起张作霖,我对他唯一的嫉妒,就是他有个好儿子!如果抓住张学良,我要把他送出国,我不会杀他。”
9月下旬至10月中旬,直奉双方在山海关一带发生激战。奉军攻势很猛,前线的陕军第一师张师长发电报向吴佩孚求援。吴佩孚心不在焉地回电:“张学良黄毛孺子算什么东西?本大帅明天抵达前线,他立刻就得逃掉。”这封率性直白的电报被奉军截获,少帅看后哭笑不得。战争进入到僵持阶段之后,吴佩孚军队沿长城一线进军顺利,眼看就有机会攻入沈阳了。没想到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10月19日,第三军司令冯玉祥与胡景翼的代表邓宝珊等在热河滦平会议,决定反戈一击,当晚,冯玉祥离滦平南下,以卫队旅旅长孙连仲任前锋,由鹿钟麟、刘郁芬、李鸣钟等带领大队人马兼程返京发动兵变。10月23日,北京城已到处都是佩戴“誓死救国,真爱民、不扰民”标志的冯玉祥兵马,北京与外联络的电话电报被切断,曹锟总统卫队在经过短暂的战斗之后,寡不敌众被缴械。冯玉祥、孙岳(第十五混成旅长京畿警备副司令)通电全国,要求曹锟下令停战,免吴佩孚本兼各职;曹锟下野,组织摄政内阁。国民军同时逮捕了传说中曹锟之宠幸李彦青。10月26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通电拥段祺瑞为国民军大元帅,并电请孙中山即日北上指导。后来,冯玉祥的幕僚石仁麟记录了兵变的全过程。“冯仅少数轻装前进。每到一地(冯)即以电报报告其行踪,取信曹、吴。并借口修路,把炮兵火力潜伏在沿路两旁的城镇,不露神色,待吴佩孚嫡系部队第三师开赴山海关前线后,立即班师回京,由孙部策应入城,包围总统府。胡部得讯亦由前线反戈,会师一处,驱曹倒吴,宣告主和,拥段。”
1924年10月26日《北京导报》的一篇文章评论冯玉祥发动的事变为“中国历史上最为杰出的一场政变”。不过确切到冯玉祥“反水”的原因,当时所有的媒体都不清楚。按照基督将军自己的说法,他发动政变,是要将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从进一步内战的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后来的资料显示,冯玉祥的“反水”,是早已谋划好的,“策反”冯玉祥的既有孙中山、段祺瑞,也有苏俄;此外还有奉系张作霖对于冯玉祥的支持。有关资料披露:早在1923年,孙中山就派汪精卫北上与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商量联合讨伐曹锟和吴佩孚;直奉第二次大战前,段祺瑞也派人游说冯玉祥。另外,1924年春天,苏联驻华公使加拉罕也通过共产国际中国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教授,说服冯玉祥伺机夺取北京政权。至于冯玉祥与张作霖的联系,有说最先开始于1924年2月冯玉祥续娶李德全的婚礼上,张作霖派了自己的亲信副官马炳南,带了一份厚厚的大礼去参加婚礼——一批军火和一百五十万的军饷。马炳南后来透露,他们与冯就联合倒直进行了实质性会谈。
战局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本来在战场上占据主动的直系,在遭遇老巢“反正”后,顿时人心浮动初现败意。冯玉祥的临阵反戈,让吴佩孚孤愤不已。很快,吴佩孚收到了曹锟被囚禁后发出的停战令——前方军队交王承斌、彭寿莘维持,免吴佩孚本兼各职,派为青海屯垦督办,颜惠庆内阁阁员除黄郛外均辞职。尽管吴佩孚情急之下一再告诫属下此为“伪电”,“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不过此时直军早已军心涣散战斗力大减。担任先锋的张学良趁机指挥奉军精锐突破直军防线,一举击溃吴佩孚主力,缴械纳降达三万余人。冯玉祥等部又向东进军包抄,吴佩孚只得率残部五千人从秦皇岛退至天津,盘踞在天津北站,等候江苏齐燮元和山东郑士琦的援军,期待杀回北京歼灭冯玉祥以解曹锟之围。让吴佩孚稍感欣慰的是,直系并未全败,东南战场的齐燮元和孙传芳取得了胜利,控制了上海江苏和浙江地区。至于皖系卢永祥,败逃后辗转日本去奉天投靠了张作霖。
寄居天津北站那一段时间,是心高气傲的吴佩孚一生中最为郁闷的时候,吴佩孚将自己幽闭在天津北站的专列上,整日借酒消愁。吴佩孚的酒量很大,传说不管是北方的二锅头、高粱酒,还是进口的白兰地,都来者不拒很难喝醉。不过这一次吴佩孚经常喝得酩酊大醉,然后像头丧家犬一样含混不清地咆哮。很快,吴佩孚企图以天津为据点进行反击的意图遭到了外国列强的干涉——驻天津的日本驻屯军司令以及美国驻屯军司令先后来到吴佩孚驻地,力劝吴佩孚离开天津,理由是天津系各国租界集中的地方,不宜作为内战的据点。以美日和列强的态度,这不是劝说,而是警告和威胁了。吴佩孚无奈何只好离开天津,因为大批粮草和弹药无法带走,吴佩孚临走之前故作洒脱地提笔写下纸条“移交段督办”,让人贴在火车上,算是送给段老爷子的大礼。然后,吴佩孚在第三方的安排下,自塘沽乘军舰沿海岸线南下,转道长江口从武汉回自己的老巢河南。步履沉重地临上甲板时,心高气傲的“常胜将军”环顾四周,如古代落魄英雄一样放声大笑。这一幕带点作秀的姿态,是一种极端忧郁的宣泄,还是一种“十年报仇不晚”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