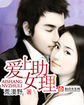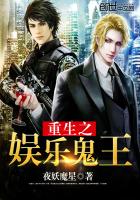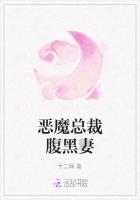来清楚说明故事时间的流逝,从而引出影片后半部分母亲与长大的儿子在同一个剧团里重逢的故事。孙瑜导演的《天明》也借助字幕“差不多又是一年了”来明确故事时间的进度,然后表现菱菱的变化和她与表哥在码头的巧遇。蔡楚生的《一江春水向东流》更是频繁使用字幕来交代故事时间的变化,“上海,九一八事变后”、“七七卢沟桥,抗战爆发”、“民国二十六年”、“民国二十八年”、“民国二十九年”、“民国三十年”等一系列字幕的运用使整部影片的时间进程异常清楚明了。此外,影片《翠岗红旗》中的字幕“1933年在江西老区,一个叫斗江的地方”、“1934年红军北上抗日,猛子随军离乡”、“匪军侵入江西”、“三年之后”,《草原晨曲》中的字幕“十几年过去了”,《丫丫》中的字幕“七年后”、“1959年3月19日深夜”,《舞台姐妹》中的字幕“1941年”、“三年之后”、“1946年”,《美人草》中的字幕“1955年开始的上山下乡运动”、“1974年”、“几年以后”、“又过了一些年”,《芳香之旅》中的字幕“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九十年代”、“二十一世纪”,《茉莉花开》中的字幕“十八年后”、“十三年后”等等,它们既起到了故事时间明确省略的作用,又由于这些影片分别是中国电影不同发展阶段的重要作品,所以它们又是借用字幕来达到故事时间明确省略这一艺术技巧在中国电影中绵延不绝的绝好证明。总之,使用字幕来明示故事时间的过渡成为中国电影悲欢离合叙事结构的鲜明特点。
与用字幕标示故事时间流逝能够起到同样作用的另外一种电影表现方式就是画外音。这一艺术技巧在中国电影的悲欢离合叙事结构中运用得也十分普遍。例如《第二次握手》就是通过丁洁琼的画外音“漂流异国二十多年的女儿,终于回到你的怀抱……”、“得到了博士学位……”、“抗日战争结束……”等来贯穿影片几十年的故事时间跨度;《归宿》也通过田丰仁的画外音“世界上有那么多悲欢离合……三十多年了……”来表明今天和过去之间的时间距离;《庐山恋》中用周筠的画外音“五年了,叫我到哪去找你呢?”来提示故事时间的跨度;《张铁匠的罗曼史》更是大量使用画外音“三年后,一个秋天的傍晚”、“60年代的困难日子里”、“打那以后,十多年……”等等来为腊月和张铁匠之间长达一生的爱恋做铭记;影片《我这一辈子》还通过字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与画外音(“这一晃就是八年……”等)相结合的方式来达到明确故事时间省略的目的。
此外,中国电影悲欢离合叙事结构的另外一种明确省略故事时间的处理方式就是累积式镜头剪辑。既然故事时间跨度很大从而使得影片不可能对每一个时间段都能加以表现,因此必然要有重点叙述的段落和省略的段落,对省略段落中国电影通常不太喜欢一笔带过,除了上文提到的通过字幕或者画外音来表明故事时间的省略之外,通过镜头的累积与叠加明确表示时间的流逝也是中国电影悲欢离合叙事结构非常喜欢的一种技巧和方式。例如《风云儿女》中通过一系列稿件和日历镜头的累积叠加来表示辛白华和梁质夫的生活历程,用马蹄和人的脚的镜头的累积叠加来表示日军侵华的过程;《一江春水向东流》中表现张忠良与素芬从相爱到结婚生子这一过程,也是使用二人双人照片、双人枕头、两双鞋子、树上果实、小宝宝等几个极简洁的镜头的叠印来表现;《我这一辈子》中“我”在秦府担任门卫的时间处理,通过把众多敬礼镜头剪辑在一起则达到了既表明时间的流逝又讽刺世事之荒谬可笑的效果,影片还通过不同时期学生街头游行镜头的叠印简洁传神地渲染了历史风云的变幻和学生运动的力量;《翠岗红旗》中五儿被迫离乡这个叙事段落,通过把向五儿的一系列近、中、远景镜头叠印在一起,不仅简要叙述了事件的发展过程,而且还蕴涵着一种咏叹历史苦难的抒情意味;《鸿雁》这部影片中充斥着众多李云飞工作镜头的累积剪辑,通过如此紧促和集中的镜头组织风格,既形象地传达了李云飞工作之忙碌,又表明他一如既往的热情和工作干劲,结尾段落老交通和女儿重逢的一系列镜头叠印,既是用来简洁地交代事件的发展过程,又明显地带有“从此,他们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的煞尾意味;此外,还有《芦笙恋歌》中以娜娃回忆的形式来叙述从前娜娃与扎托相恋的叙事段落以及扎托带领青年反抗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叙事段落,《冰山雪莲》中金珠与母亲相依为命、度过的苦难岁月的段落,《草原晨曲》中热火朝天的劳动段落,《丹凤朝阳》中二妹在美专上课的段落,《与魔鬼打交道的人》中于海宝回忆12年前生活情景的段落,《叛国者》中捕蛇专家回忆与妻子相见、相恋的叙事段落,《樱》中光子回忆幼年和哥哥在小溪边玩耍的叙事段落,《一江春水向东流》中分别表现素芬与张忠良各自在战争岁月中的生活的叙事段落等等,都是以镜头累积叠印的方式来实现的。通过镜头的叠化累积表示时间流逝是对时间的压缩而不是完全省略,这一手法在90年代之前的中国电影中使用得非常普遍,一直到张艺谋的《活着》在简要呈现40年代福贵的皮影戏生涯时还大量运用了叠化。
累积式镜头剪辑的作用除了表明时间的过渡和省略之外,其次就是抒情性,特别是当这一技巧被运用在回忆段落的时候就更为明显地带有咏叹的性质,而且,镜头的累积剪辑经常是同样动作的镜头剪辑在一起,反复地表现同一动作更加使之具有浓缩时空的主观抒情气息。
其二是时空距离很大的镜头之间的自由组接。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
中曾经把中国古代小说叙述的技巧之一概括为“捏合”。所谓“捏合”指的是中国小说因为追求叙事时间的整体性,即使在短短的一篇小文章里也力求概括一个人的一生,因此在叙事时间的处理上就需要特别的技巧,即叙述者充分介入叙事,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将彼此之间时空跨度很大的事件自由组合在一起,此即为“捏合”。这一“捏合”的叙事技巧在中国电影中的表现之一就是镜头时空的自由组合。李泽厚在研究中国文艺创作和接受的心理特点时,曾经指出“中国文艺在心理上重视想象的真实大于感觉的真实”[15,P366],“‘想象的真实’使中华文艺在创作和接受中可以非常自由地处理时空、因果、事物、现象,……将想象着重展示的感性偶然性的方面突现出来”[15,P367]。或许这应该是中国电影的悲欢离合叙事结构在有限的银幕持续时间中能够自如地处理相对漫长的故事持续时间的深层次的文化心理基础。在中国电影的悲欢离合叙事结构中,彼此之间时空跨度很大的镜头与镜头的连接非常普遍,镜头之间的组合相对自由。比如《天明》中灯红酒绿的上海与远洋的航船和革命策源地——广州之间的自由切换;《一江春水向东流》堪称镜头打破时空限制、自由组合的典范,比如影片中“民国二十九年”
这个叙事段落,城市车站离乱的人群叠印乡下田间素芬他们的劳作,张忠良在湖北被俘虏、被打骂、逃跑切乡下老父亲被杀害;再比如《飞来的仙鹤》中小翔弹琴这个叙事段落,由小翔在城里弹琴的场景切换到乡下养父母家再切换到小翔弹琴,完全是以主人公此时的情绪为依托进行剪辑;还有《乡情》中田桂初到城市的那个夜晚,房中辗转难眠的田桂与乡下桂花树下翘首企盼的老母亲的全景镜头交互剪辑在一起。如果说以上所举的例子都是空间的跨度大,那么《乡情》中田桂与城里妈妈上街买衣服的段落处理更可以看出“捏合”的时间自由度。田桂的城里妈妈给他买新衣服,他却不由自主地回忆起小时候与养母一起在小镇的集市上看中一件红色背心、养母却无钱给他买的情景;还有田桂和莉莉在公园划船的镜头与他小时候和妹妹一起放牛、划船的镜头剪辑在一起。《樱》对这一时空自由切换的手法运用得更为熟练,光子现时情景与儿时片断的自由穿插正是整部影片的剪辑思路。影片《云水谣》的结尾,纽约的老年王碧云通过国际互联网在电脑屏幕上与年轻的陈昆仑(同样由陈坤饰演)相见,这个叙事段落之所以极具张力和感染力正是源于被切换的镜头之间巨大的时空差距:纽约与西藏,老年王碧云与青年“陈秋水”。《夜奔》片头的处理或许可以看作是对这一手法的杰出运用和代表之作:年轻的拉大提琴的手、现代化的西方餐馆里的老人、黄包车夫、旧中国的影像、今天公交车上的老人、年轻的英儿骑着自行车,苍老的背影与昔日年轻的面孔、西方与中国、今天与过往交替剪辑在一起,时空的巨大间隔丝毫也没有成为它们组合在一起的障碍,镜头在这里似乎是飞翔的,颇具“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的审美特征。
总之,字幕、画外音、累积式的镜头剪辑方式以及对于时空跨度很大的镜头之间的自由捏合,这些电影艺术技巧在中国电影的悲欢离合叙事结构中频繁出现,而且我发现在中国电影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它们受重视的程度也有所不同。比如,“十七年”期间以及“十七年”之前的影片较少使用画外音来表示时间省略,字幕形式出现得比较多。而80年代前半期中国电影的悲欢离合叙事结构却大量使用画外音这一形式来提示时间流逝,字幕相对而言使用得很少,90年代以后,以字幕来说明影片的时代背景以及故事的时间过程的影片又多起来。累积式的镜头剪辑方式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的中国电影中非常流行,时空跨度很大的镜头之间的自由组合则在新时期以来愈加受到青睐。
三、影片叙事的动力
既然中国电影的悲欢离合叙事结构所关照的故事一般都具有较大时空跨度,物理的或者说是自然的时间流转就自然而然地成为故事发展变化的线索和推动力,特别是当这一自然时间与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动融合在一起,就更加具有清晰的发展脉络和力量。因此,中国电影的悲欢离合叙事结构通常是根据四季的变化、自然时间的消逝或者社会历史的发展来安排影片的叙事段落和节奏,从而在叙事上与经典好莱坞电影形成极大差异——影片叙事的动力不同。在分析电影的形式与风格时,波德威尔认为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要分析因果关系,弄明白叙事的动力。就像普洛普在分析俄国民间故事时指出贯穿其中的决定性动作就是寻找失去的宝物或者公主,“动作”同样也是古典好莱坞叙事的决定性因素。在经典好莱坞电影中,“自然原因(洪水、地震)或社会原因(制度、战争、萧条)可以充当动作的催化剂或前提,但叙事总是专注于个人的心理原因:他的决定、选择和性格特征”,“对叙事起推动作用的重要性格特征往往是欲望”[16,P145],影片最终的结局则是个人欲望的实现和满足。而在中国电影的悲欢离合叙事结构中,个人的动作和欲望很难成为故事发展的推动力,由于中国电影的悲欢离合叙事结构对故事时间的整体性把握,使得故事时间自然化、历史化,人物角色也成为自然中、历史中的个人,而与广袤无垠、无始无终的大自然和历史相比,个人的力量和欲望不仅是微不足道的,而且是暂时的,所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因此,在中国电影的悲欢离合叙事结构中,个人的欲望或者动作不再是叙事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而是代之以历史的变动、自然的变迁或者道德伦理的力量。如果说经典好莱坞电影中的人物是在“导致事件”、“与时间赛跑”(“与时间赛跑的原则……是好莱坞电影工业中常用的编剧技巧”[17,P13],“与时间赛跑”这一编剧原则在好莱坞大片中极为常见,像《泰坦尼克号》、《独立日》、《山崩地裂》等影片的叙事张力都来自于主人公要在极为有限的时间里完成拯救的任务),那么在具有相对漫长的故事时间跨度的中国电影的悲欢离合叙事结构中的人物则是在“经历事件”,在时间流转、历史变动中感受着生老病死、天理昭彰或者历史力量。
我们可以发现,由于悲欢离合叙事结构采取这样一种宏观的、历史的视角,由于故事时间的漫长,个人的力量或者欲望通常消融在时间的流逝和历史的变动之中,因此,影片透过时间的流逝展示给观众的就不是古典好莱坞电影中使得主人公终于梦想成真的个人力量,而是历史的定律、无常的命运或者某种抽象的力量,比如伦理道德。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孤儿救祖记》为代表的一大批家庭伦理片,就是通过好人的始遭离乱、终得团圆和坏人的恶有恶报来彰显道德的某种超越性力量。善良、品德高尚之人虽经卑鄙小人的诬蔑和陷害而备尝艰辛,但最终邪不胜正,他们必会一朝得洗冤情,重拾过去的幸福生活,而道德败坏的后母、侄儿们则落得个羞愧而死或者罪有应得的可耻下场。如1923年《孝妇羹》贤惠的儿媳珊瑚最终令婆母王氏羞愧交加、幡然醒悟。1925年《孤雏悲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