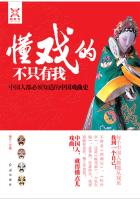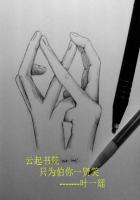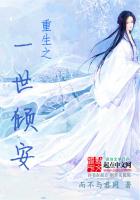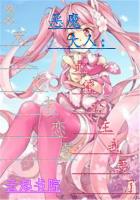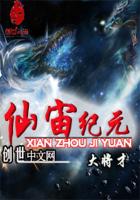由此可见,中国电影悲欢离合叙事结构的空间处理是倾向于营造一个稳固、圆满的叙事空间,无论是通过广阔的时空操作和某一空间的重复还是通过聚焦于时光流转中的某一固定空间,以及使用固定镜头和长镜头、对“缝合”式镜语的谨慎运用,都使影片的叙事空间显得相对稳固,特别是与影片中较长跨度的故事时间相对比,就更加突显了故事空间某种恒定和稳固的色彩,再加上影片中的人事相对于故事空间的改变,使得影片中这个见证了世事沧桑、人生离合的故事空间似乎超出了单纯的、实在的、物质空间的范畴,更类乎一个精神意义上的家园,或者哲学意义上的生存空间。空间在这一叙事中具有某种象征的意味,“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及其特点之一是象征……”[26,P96],一个类似于中国哲学中所谓的熙来攘往的人世间,一个道的境界。这在有的影片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其空间的象征色彩非常浓郁。例如倪震分析《巴山夜雨》的空间“波涛不息的江水、朦胧隐现的月色、三峡的雾气、漂流的航船……,象征着人在漫漫长夜中无尽的放逐”[27,P10]。再比如《活着》中福贵所生活的小镇似乎不仅是一个实在的故事空间,而且还可以看作现当代中国社会的缩影,甚至可以看作人所生存于世间的一个隐喻:这生生不息的大地见证了无数苦难,福贵的人生经历是人类苦难的代表和结晶。香港导演严浩的得意之作《似水流年》中的那个小村庄,既是姗姗和众多海外游子魂牵梦绕的家园,又似乎是中国古典哲学中“道”的某种隐喻:这里有人世的纷争,但是更有真淳的田园,大自然的韵律在这里袒露得那么清晰。严浩如此分析他的《鸳鸯蝴蝶》对西湖场景的运用,“在西湖这个美丽的地方,时间和空间是混合在一起的,现在就是未来,现在和未来是同时在里面的”[18,P780]。还有《霸王别姬》中的那个久经沧桑的舞台,程蝶衣和段小楼历经几番恩怨情仇,最终回到这个舞台上,并且在这里返回朦胧中生命最初的本真,这个舞台因此具有象征的意味:人们从这里开始,最终回到这里结束人生长途的表演。《孔雀》中姐姐在街头邂逅当年的解放军伞兵,这时他已经失却了曾经的神采、还原为路边一个边吃包子边等老婆买杂货的普通男人,在影片此前的情节中曾经特别介绍这个令姐姐钦羡的伞兵来自北京,那么按照一般的情节发展规律他在小镇安居生活的可能性似乎是微乎其微的,但是这次邂逅在影片中之所以显得不那么突兀,根本原因还是小镇这一空间在影片中兼具茫茫人世间的象征色彩。最悲情的莫过于关锦鹏的《胭脂扣》,当如花从阴间归来却再也找不到她所熟悉的城市和街道,借助鬼魂这一超自然的力量,影片传达了一种强烈的、沧海桑田的、时空变幻之感。杨德昌的《一一》中虽然故事发生在高楼大厦林立的现代都市,但是镜头对准高楼内一个三代同堂的小家庭,老人逝去了,父母各自遇到了人生中或事业或情感的问题,青春期女儿的情感在萌动,小儿子充满对这个世界童稚的困惑和追问,一方小天地竟也有大宇宙的格局和气度,与杨义对中国古典小说时空的分析异曲同工,“它力图贯通和超越‘天人’空间,‘古今’时间,以有限去思考和隐喻无限,省悟天理人心之精蕴,升华出艺术韵味来”[8,P297]。
(第三节)时空结构的流动回环
我们知道,电影是时空艺术,“电影的空间是时间化的空间;而如果没有视觉的空间和声音的空间,电影的时间也同样无从体现出来,所以说电影的时间又是空间化的时间”[28],“两者的结合……是如此密切,以致几乎造就了一种完全是独特的空间——延续时间的联续”[29,P182]。那么,中国电影中以大跨度、整体性的叙事时间和稳固的叙事空间相结合、专注于表现人生聚散离合的这类影片所呈现出来的独特时空联续是怎样的呢?
一、点与点连缀的流动
故事时间的漫长跨度使得这类影片在展开叙事时只能选取重要的时间片断来展示,即“一方面展开大幅度的时空推移,一方面把握住最有文化意义和生命意义的瞬间”[8,P431]。香港电影理论家林年同先生曾经指出“中国电影的情节组织,叙事结构是缀联性的段落结构,有一种连贯绵延的,交替的,变迁的,流动的空间和时间的观念,具有‘游’的美学性质的‘离合引生’的思想”[30,P57]。如果说“流动的空间和时间的观念”是某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中国电影的叙事特点,那么可以说,这一时空结构特点在中国电影的悲欢离合叙事结构中体现得非常之鲜明。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电影的悲欢离合叙事结构的时空安排通常呈现为“点与点”的连缀,根据不同人生阶段、不同历史时期选取不同的人生片断来组织叙事是这类影片最常用的时空结构方式,即“流动性是中国艺术结构的一个鲜明特征,维此方能将中国艺术的变易无滞、品物流行的文化品性呈现出来”[31,P70]。
譬如《渔光曲》就是通过徐母生产,徐母去何家做奶妈,小猫和小猴的童年,小猫和小猴的少年,小猫和小猴流落上海、遇见何子英等一系列不同时空的连缀来构成整部影片。《桃花泣血记》也是以琳姑降生、儿时琳姑和德恩、少女琳姑和德恩、琳姑被逐、琳姑与父亲艰难谋生、琳姑去世等各个时空片断的流动来结构影片。《风云儿女》从1932年辛白华和梁质夫在上海的生活场面开始,然后是他们对小凤的帮助、辛白华与富孀的青岛之行、小凤回东北看望爷爷、辛白华在北京得知梁质夫的死讯、辛白华和小凤在战场重逢等情节,影片似乎是从时间的流程中截取一些重要的生活片断,把它们组织在一起,从而构成了整部影片。《城南旧事》中绣贞的故事、小偷的故事、宋妈的故事、爸爸的去世,通过小英子的眼睛一一摄入,故事彼此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影片的时空安排因此显得疏朗有致。《活着》这部影片则分别选取民国早期、解放战争时期、大跃进时期、“文革”期间、新时期作为叙事段落,福贵在不同时期的经历,既是故事的发展,又是故事的循环往复,段与段之间不仅有着时序上的递进,更有着多声部合唱的错落和映衬。《茉莉花》讲述了一个家庭、三代女人的的故事,她们的故事彼此之间既是一种绵延,又是一种对比,在同与异中暗含着创作者的历史眼光和人生感慨。
杨义认为“宏观的时空安排,变换着叙事时间和历史时间之间的比例尺度,牵动了叙事节奏的疏密张弛。两种时间比例的调度,实际上包含了叙事者对历史人物事件的选择和评价”[8,P267]。因此,中国电影的悲欢离合叙事结构一方面以大跨度的故事时间、广阔的故事空间和某一空间的重复出现来涵盖相当规模的人生或者社会画卷,另一方面又撷取和连缀画卷中一个个重要的瞬间来结构影片,从而使得这一叙事结构模式呈现为一种流动的美感的时空安排方式,其实与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对时空的体悟有着密切的关系。张爱玲在她的小说《半生缘》里曾经说道,“原来人生看起来很长,其实紧要的就那几个黄昏。原来世界看起来很大,其实切实的就那几个低檐。”那么,我们对于广阔的人生和世界的观照,或许也只要把握住那几个紧要的“黄昏”或者“低檐”就够了。因此,中国电影的悲欢离合叙事结构的流动性时空结构蕴涵着某种中国式的抽象和哲思。
流动性时空结构对具体电影语言的选择和使用也产生了影响。我发现,在流动性时空结构的影片中,对大全景和特写这种两极镜头的运用非常突出、也非常有规律。影片中那些宏观的时空观照多用远景或者大全景(俯拍的角度也很受青睐),表现浓墨重彩的瞬间时则毫不吝惜对特写镜头的运用(升格镜头也是此时经常的选择),“运用两极镜头,发挥极远景和特写结合的力量”[32],“为了展示人物情绪骤然跌宕,……应用了两极镜头和大俯大仰的对跳组接”[33,P370]。比如《一江春水向东流》,当影片叙事发展到每个不同的历史阶段时,都以大俯拍的街头或者车站的全景镜头来开始,以营造一种宏观的历史氛围和时代环境;《活着》每一个新的叙事段落的开始也是小镇街道的全景镜头;像《云水谣》中既有全景镜头中对场面的铺陈(比如20世纪40年代的台湾街头、炮火纷飞的朝鲜战场以及今天光线暧昧的酒吧等),更有特写镜头中对细节的抓取和强调(比如陈秋水与王碧云初次相遇时使用高速摄影,给这个瞬间来一个特写)。大的时间跨度与浓墨重彩的瞬间相结合,使中国电影在时空安排上既留有足够的空白又细腻到足以抒情传神,颇有中国传统艺术“虚实相涵而可游”[9,P224]的美感。
二、首与尾衔接的回环
在中国电影的悲欢离合叙事结构中,某一空间的重复出现、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物之间的分与合又使其时空结构呈现为首尾衔接的回环。
比如,影片《劫后桃花》中在那个桃花盛开的家,刘花匠归来与昔日他爱慕的东家小姐见面。《天云山传奇》中宋薇再次回到天云山,远远看到肃立在冯晴岚墓前的罗群。吴贻弓在谈到他创作《城南旧事》的时候尤其注重的艺术手段时曾指出“我感到我们至少在表现形式上抓住了‘艺术的重复’这个重要的手段。……前半部井窝子,井台打水共反复出现了四次,机位相同,内容相同,但‘质’有所不同;后半部操场放学也反复出现了四次,机位相同,内容相同,但‘质’
也有所不同。虽然,井窝子和操场在直观形象上是差别很大的,但在心理感受的因素上却是完全相同的,它们造成了一种生活的流逝感……这种‘重复’的感觉在影片中起到了始所未料的巨大作用,它们就像一条无形的纽带一样,把影片所叙述的一桩桩一件件生活琐事,原来是分散的,不关联的,却一下子结到一起来了。不管观众是否那么有意识,甚至最好是无意识的,但他们都会被这种意图所左右,他们会感觉到从银幕上看到的是一个生活的总体”[34,P125]。在陈凯歌导演的《霸王别姬》这部影片中,成名之后的程蝶衣遇到了一个像他一样幼时被抛弃、对学戏也特别痴迷和倔强的小四,于是他开始像昔日师父教自己一样严厉地要求小四,但是小四没有变成又一个程蝶衣,而是在历史浪潮中成长为一个格外“骁勇”的红卫兵;影片结尾,老迈的霸王和虞姬在一束灰尘飞舞的光的映照下站在陈旧的舞台上,空旷的剧场没有一个人,痴迷一生的程蝶衣突然返还生命的本真,与小石头重拾少年时的对话。“相似”与终于“不似”,“少年”与“老去”,世事的迷离、时光的流转,令人霍然惊觉其中所蕴藏的某种人生哲理,而又怅然若失。
《孔雀》中一家五口坐在走廊上吃饭的场景在影片中多次出现,它既是主人公永远挥之不去的少年记忆又是人生琐碎呆滞的无言写照,而弟弟在舞厅遇见哥哥当年暗恋的陶美玲、姐姐街头邂逅曾经的伞兵的场景又强烈地传达出人事的变迁和命运的荒谬无奈。还有《芳香之旅》中那辆来来往往的向阳号客车,车厢是承载影片故事情节的主要空间,主人公几乎在这里度过了一生,当她做了司机,又来了一个如她当年一样年轻的售票姑娘,可是这个姑娘和她却是那么不同。
《情人结》影片开始是小时候的侯嘉和屈然在大楼台阶上玩“石头剪刀布”的游戏,后来两个人长大了,经历了人生中苦涩的爱与恨,侯嘉远赴美国,等待中的屈然看见有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在楼道里玩当年她和侯嘉一起玩的游戏。
《活着》中福贵与儿子的对话“鸡长大了变成鹅,鹅长大了变成羊……”在片尾再次出现,只不过这次发生在福贵和小外孙之间。苍老的福贵与天真的外孙,满布灰尘的木箱与稚嫩的小鸡,生命的老去与新生,在影片展开大幅度的时空跨越的同时,却又回环往复、复沓轮回,实现了时空的圆满与绵延。侯咏导演的《美人草》中的一个经典场景就是桥上铁轨,正是在这个铁轨纵横交错的地方(人生路途的某种隐喻?),青年叶星雨和刘思蒙曾路遇三个麻风病人和一个和尚,当时刘思蒙曾向和尚询问二人的姻缘;若干年过去之后,年老的叶星雨和刘思蒙再次相遇在桥上铁轨,同一场景中还有一个衣衫褴褛极似当年的狗屁的少年,同样也有三个麻风病人和一个与当年一模一样的和尚走过他们身旁。场景的相似和人物的老去令人产生恍然隔世、今兮何兮之感。特别是影片的开头和结尾的设计:开头是叶星雨追赶客车、并在刘思蒙的帮助下上了车,影片结尾则是叶星雨追车,车顶的刘思蒙只是探头看了她一眼,客车远去,叶星雨没能赶上远去的客车。影片的这个结尾在表示影片故事情节结束的一个黑场之后出现,犹如一部新影片的开头,使观众产生强烈的时空循环之感。无独有偶,香港电影《甜蜜蜜》也有着与《美人草》异曲同工的时空设计。其开始场景是一辆由大陆赴港的列车,黎小军乘车来香港,然后影片顺时序叙述黎小军和李翘十几年的人生经历,他们经过了多次错失之后终于在美国街头因为邓丽君的一曲《甜蜜蜜》重逢,表示影片故事情节结束的黑场之后却又是影片开始时的赴港列车场景,只是这次镜头转了一个角度,给观众看影片开头画面背后的内容,原来坐在黎小军背后的乘客正是李翘。如果说《美人草》的结尾是在设想人生的另一种可能,那么《甜蜜蜜》的结尾则是在思考人生诸多巧遇的神奇和奥妙,但它们的共同之处则在于都是以时空的首尾咬合来结构影片。王家卫通常被认为是一位颇为前卫和现代的电影导演,但是在炫目的电影技巧和前卫的电影形式背后,王家卫电影的时空塑造其实却是颇为古典和传统的回环往复。对此,研究者似乎很有共识,“在王家卫的电影中,时间序列并不是直线式的(过去→现在→将来),而是不断的轮回复始”[35,P167],“《东邪西毒》没有精准的时间刻度,但一样是反反复复周而复始(跟空间一样,沙漠之后也是沙漠)。不同者是这里的时间更添了一种苍茫的宿命意味”[36,P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