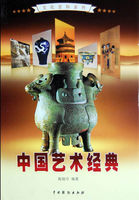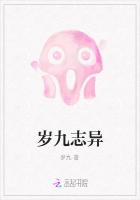杨义在分析中国文学叙事特点时曾经指出其“以地点重复而强化人事反差的方式”[6,P50],那么反过来,人事的变化自然也强化了空间的稳固。在影片中,人物角色有的变老、死去,有的离开、归来,但是故事空间却始终在那里,它只见证这份变化。例如,1925年裘芑香导演的《不堪回首》,男主人公朱光文背弃初恋情人素云与富家女结婚,在影片结尾时他回到了原来的家,一个喻义着美好和纯洁感情的家,但是素云和她的老父亲都已经离世,朱光文只见到满眼的荒草萋萋,物是人非;《桃花泣血记》中桃花灿烂依旧,但是琳姑已经在贫病交加中死去;《人道》
中当浪荡天津游乐场所的赵民杰终于醒悟,回到家乡,他的父母都已经饿死,幼子失散,妻子也已处于弥留之中;影片《白毛女》中,大春最终回来重建家园;《柳堡的故事》结尾班长归来与二妹子在明媚的水乡重逢;《女篮五号》中的教练回到了旧社会他曾经做运动员的上海,带领一支新的球队;《天云山传奇》的结尾,宋薇终于回到寄托了她的青春和梦想的天云山;《芙蓉镇》、《活着》中的小镇犹如一个“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舞台,见证了不同时期、各色人等的表演;在顾长卫的《孔雀》中,曾经离去的兄妹姐弟最终归来,一起生活在家乡小镇。
中国电影悲欢离合叙事结构中,故事空间的稳固性还体现在影片对具体空间和场景的镜头处理以及对于固定镜头的偏爱。例如,《春桃》这部影片就是以开头和结尾镜头语言的彼此呼应和微妙差异来营造了一个圆满闭合、稳定恒久的叙事空间。在影片开始,春桃背向观众走向故宫,下一个镜头是画面中大面积的故宫宫墙,春桃由画面右边走向画面左边、出镜,在影片结尾,先是大面积的故宫宫墙画面,春桃由画面左边走向画面右边、出镜,最后一个镜头是春桃面向观众从故宫走出。影片通过相似镜头语言和相似场景的重置来强化故事空间的稳固。《活着》以渐显的方式出现的第一个镜头就是纵深走向、空寂的、冷色调的小镇街道,紧接的下一个镜头是暖色调的、拥挤的、福贵在赌场的场景,这两个镜头所展示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空间:无生命的街道与有生命的人、空寂与拥挤、清冷与热闹的强烈对比揭示了整部影片的叙述基调。我们发现,“纵深走向的街道”
这一空间形式在影片中反复出现:福贵从赌场回家、家珍离福贵而去、福贵从战场归来、镇长拉着炼出的第一块钢铁游行、万二喜领着工人阶级弟兄来修房子、万二喜来接凤霞、春生深夜离去的背影、福贵与外孙送水归来,几乎影片中所有的重要情节都在“街道”发生。而且,“街道”这一空间在影片中是以几乎完全相似的景别(全景)和角度(始终是纵深走向)在影片中反复出现。影片对空间的稳定性的刻意强调由此可以看出。《孔雀》的空间构思与《活着》有相似之处。影片的第一个镜头也是俯拍的小镇街道,街道这一空间在影片中同样反复出现:姐姐骑车带着自制的降落伞、弟弟裸身在冬天的街道奔跑、姐姐在街上遇到曾经英气勃勃、现在邋遢家常的伞兵,等等。在《孔雀》中更加多次重复出现的就是家中的客厅:他们在这里分糖、做皮蛋、看电视、母亲给哥哥扎针、等陶美玲来吃饭、送姐姐结婚等等,同样景别的客厅场景在影片中的频繁出现,使这一场景具有超越具体叙事情景的意义。为了强调空间的稳定性,《孔雀》的镜头运动也非常克制,对固定长镜头的使用成为影片的突出风格,而人则从固定镜头摄入的空间中进出。
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全家在屋顶做煤球突遇大雨,母亲在徒劳的铲泥堵水,姐姐走过来在泥巴上摔了一跤然后出镜,姐姐对镜头空间的突破与其他人被局限在镜头空间之内形成了鲜明对比。我们可以发现在影片中姐姐通常是挣脱固定空间的人物。影片的绝大多数场景都是街道和小镇,唯一挣脱小镇这个空间的就是天空中的飞机和伞兵,而天空、伞兵这个空间的出现紧接在姐姐仰视天空的镜头之后,这个空间属于姐姐,仰起头来看天空这个动作只有姐姐做出来了,只有她把目光投向了小镇之外的空间。还有结尾镜头,孔雀笼后的一个大全景,姐姐、哥哥、弟弟分别入镜、滞留一段时间然后出镜,镜头依然固定不变,一个不明显的叠化(我猜测这个叠化或许是由于孔雀开屏的难以人为控制而被迫加入的,因为从影片整体来看,无疑一个自始至终的长镜头更为理想)之后孔雀开屏了,尴尬的背面与华丽的正面并陈。无独有偶,《活着》的结尾镜头也是一个固定机位的长镜头,万二喜出镜、入镜,然后渐隐,通过固定机位的长镜头和人的出入来表示空间的超稳定和人与空间的关系以及人事相对于空间的变化。
二、镜头空间的非“缝合”
电影镜头的“缝合”这个概念是美国电影研究者达杨提出的。他指出“叙事电影把它自己表现为一个‘主观性’的电影。……这些影片认为影像是被精巧地设计并被直观地觉察为是和一个人物或另一人物的视点相一致的。这个视点是有变化的。也有这样一些时刻,影像没有表现任何人的视点;但是在经典叙事电影中,这是相当例外的,非常快地,影像被再确定为某一个人的视点。……这个体系就是缝合体系”,而“这个体系依赖于两个领域的根本的对立:(1)我们在银幕上所看到的空间,(2)另一个补充的空间,它可以被界定为缺席者正从那里在看的地方。因此,任何一个由摄影机限定的电影空间,都和另一个由不在场的空间相对应”[25]。中国电影学者刘一兵认为“影片叙述者通过在画面上表现正反打镜头,来‘缝合那个打开观众想象和缺席者的感知所提供的电影场面的关系中的缺口……并为了自己的目的而操纵观众的想象。’这也正是好莱坞镜语的立足之本”[23,P128129]。应该说,电影镜头的“缝合”是一个普遍现象,代表观众视点的镜头与影片中人物视点相一致、从而使观众产生分别占有电影中不同角色视点的感觉正是电影给予观众梦幻般奇妙体验的原因之一,中国电影自然也不例外。
不过,如果说“缝合”式镜头体系是好莱坞镜语的立足之本的话,那么在中国电影的悲欢离合叙事结构中,“缝合”式镜语并没有达到如此重要的程度,我倒是在许多影片中找到了众多非“缝合”式镜头语言的例子。当然,非“缝合”式镜语并不仅限于悲欢离合叙事结构模式,更不限于中国电影,它与“缝合”式镜语体系一样,都是具有普遍适应性的电影语言。我在这里探讨中国电影悲欢离合叙事结构对非“缝合”式镜语的运用,一是因为在我读解影片的过程中发现它非常突出,二是因为它确实体现了中国电影在空间处理上的一些特点。
我们知道,决定“缝合”式镜头语言的因素有两个:镜头拍摄所选取的空间和剪辑。如果说好莱坞电影在处理一个场景时通常倾向于依靠占有角色视点拍摄不同区域,然后通过镜头剪辑来“缝合”一个完整空间的话,那么在中国电影的悲欢离合叙事结构中呈现为反缝合的镜头拍摄方式和剪辑方式的影片并不鲜见,这突出表现在影片对某些叙事段落的处理上。譬如在《姊妹花》这部影片中,即使是几场重要的、角色情感冲突非常激烈的叙事段落也很少采用“缝合”式镜语体系:二宝与钱督军吵架段落,多是二人全景或中景镜头的切换,完全没有来自于角色视点的镜头空间的组接;影片在处理大宝被抓到处长(她的父亲)面前这个叙事段落时,完全是全景镜头之间的切换,场景空间无需通过镜头“缝合”来实现;二宝与母亲相认这个叙事的高潮段落也仍然以一个母亲、父亲、二宝三个人的全景镜头来表现。“缝合”式镜语在《姊妹花》中也有少量运用(比如大宝与桃哥夜晚躺在床上谈话这个场景就使用了二人近景的正反打,钱小姐发现大宝偷金锁时也分别用了一个小姐和大宝近景的正反打,然后很快就转到二人站在摇篮前的中景镜头),但是与影片中大量使用全景和中景来处理场景空间相比显然不占重要位置。如果说拍摄于1933年的《姊妹花》在镜头语言的运用上稍嫌不成熟的话,那么在1947年拍摄的《一江春水向东流》这部影片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创作者对使用“缝合”式镜语的克制。《一江春水向东流》中占有角色视点的镜头明显增多,在处理某些场景的时候,依据“缝合”式镜语体系的思路来组合镜头的意识也体现得比较明显,但是一方面影片中通过镜头运动或者同机位、不同景别的镜头之间的切换来处理场景相比之下更为突出,更多的叙事段落采用的是这种非“缝合”的空间表现方式;另一方面即使是运用“缝合”式镜语的叙事段落,镜头语言也不纯粹,完全代表角色视点的正反打在影片中运用的并不多。譬如在影片开始不久工人为抗日募捐、张忠良讲话这个重要场景中,舞台上的张忠良、观众、舞台侧面的素芬之间彼此的镜头切换思路完全符合“缝合”式镜语体系,但是影片创作者似乎有意识地避免单纯“缝合”式镜语中单个镜头空间的封闭,例如,作为素芬视点镜头的张忠良中景也总是会尽量出现台下观众的身影。
而且,在这个叙事段落之前,后台张忠良扶王丽珍下台阶段落,以及这个段落之后,张忠良被老板训斥段落和随后的张忠良与素芬在家中吃晚饭段落,都是通过全景镜头或者同机位镜头切换来完成的。可以说,在《一江春水向东流》中,非“缝合”的镜语体系仍是影片结构空间的主导。在中国电影的悲欢离合叙事结构中,这种以非“缝合”的镜语来把握空间的方式始终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如《飞来的仙鹤》中感人至深的乡下养父母为小翔过生日准备礼物、夜晚在灯光下对坐剥瓜子的叙事段落,就多是全景、远景或镜头的推、拉,完全不遵守好莱坞的“全、特、全”的场景拍摄和剪辑方式;再比如《祭红》中冯家宝回家宴请各色人等这个叙事段落,影片也没有对主与宾或各路宾客之间的关系用镜头的切分来表现,而是使用了一个绕着圆桌的长摇镜头;还有《祭红》中冯家宝与敌军官密谋对付徐红宇的叙事段落,在这个二人场景中,似乎完全可以使用“缝合”式镜头体系、通过分切坐在书桌后的敌军官和站在桌前的冯家宝的近景或者特写来传达给观众必要的紧张情绪,但影片依然采用了二人全景、中景的同机位互切和镜头推、拉的空间处理方式;《第二次握手》中丁洁琼与苏冠兰海边谈情的镜头更完全是全景、远景的互切,我们只听到二人的声音,看不到他们的神情,整个场面洋溢着一种悠远含蓄的抒情气息;在《归宿》田丰仁去杭州大哥家受到热烈欢迎这个叙事段落中,大哥全家人与田丰仁坐在一起吃饭的场景也主要是通过镜头的长摇运动来表现;还有《乡情》田桂初到城市里的家见到自己的生母这一场情感积蓄极为强烈的戏,影片在处理的时候仍然没有采用对切的镜头剪辑方式,特别是田桂与其生父坐在一起喝酒这个段落,父子二人的交流很少使用对切,多是镜头的长摇和推拉;《长空比翼》中张雷从医院里偷偷跑出来探望生病的师长,并与战友们团聚这一颇为热烈和欢快的叙事段落也是多为全景或中景的切换,而很少张雷的特写或者近景与战友们的对切。
通过“非缝合式”镜头拍摄方式和剪辑方式来处理一个场景,通过同机位全景、中景的互切和镜头的运动来表现一个空间,相对来说维护了空间本身的稳定和圆满,观众的位置也被放在相对客观的地方,而不是占有某个剧中人的主观视线,时刻产生融入镜中的心理体验。这种对固有空间的稳定和圆满的维持和尊重最为极端的镜头运用方式或许就是长镜头。毋庸置疑,长镜头美学在中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而且中国电影对长镜头的出色运用很早就出现了,不独发生在“文革”结束后张暖忻等人提倡电影语言的现代化之后,香港电影学者林年同、黄爱玲等对中国三、四十年代电影中单镜头的研究就非常引人注目。长镜头美学在中国的发展似乎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它与中国传统绘画的空间观念颇为契合。郑君里在介绍他创作《枯木逢春》时指出,影片开头的长镜头运用就受到了古典名画《清明上河图》的启发,林年同在其力作《中国电影美学》中也特别提到了中国古典绘画的“游”视点对中国电影长镜头的影响。确实,长镜头在中国电影中很早就作为一种美学手段被有意识地加以运用,到了以侯孝贤、杨德昌等人为代表的台湾新电影运动、中国第六代电影,固定长镜头的运用更是蔚为大观,成为具有突出的美学风格和产生很大国际影响的镜头运用方式。而且,中国的长镜头运用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以及安德烈·巴赞提倡的长镜头有着微妙的差别,对此,已经有研究者做了不少阐释。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中长镜头对现实的逼视相比,中国电影的长镜头似乎总带着一股静观和超然的气息,特别是侯孝贤、后期杨德昌电影中的长镜头,带有某种静看云卷云舒的达观和悲悯的哲理色彩,或许这与中国的美学传统不无关系。
三、叙事空间的象征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