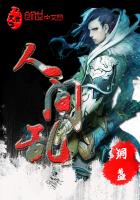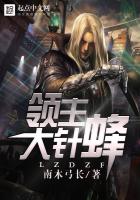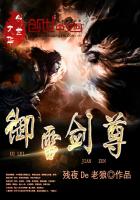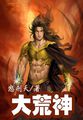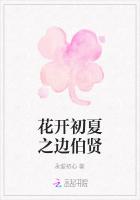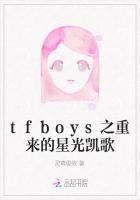可是,类似分析仍然体现了严重的知识盲点:“如果说一元论会导致极权主义,那么应该指的是善一元论而不是正义一元论。善一元论为了避免极权主义之嫌,往往以文化一价值多元论的面目出现,但恰恰是文化一价值多元论成为极权主义的根源。”基督教既是善一元论,又是正义一元论,那么基督教到底是导致极权主义,还是导致宪政主义呢?在中世纪晚期,罗马教廷曾经专制过,然而,这样的暂时堕落很快就被基督教会本身成功自我克服。新教徒尤其是受加尔文神学思想影响的英美新教徒,更是有意无意地成功培育出了世界上最健康的宪政民主政体;即使是天主教,在新教徒和部分天主教教徒为了纯正教义和信仰自由而进行的浴血奋战之后,“墙外开花墙内香”,也被迫接受了信仰自由和政教分立这样的普世价值,进而整个被作为政治文明全盘接受。基督信仰从来都是自称为普世主义的,从来就没有自卑地以文化一价值多元论的面目出现。只有正视基督教话语,超越伯林后,顾先生的理论才更富有历史感的意义和更富有层次感的分析。
基督信仰奠定了宪政民主的基础。一个政治学者如果整全地理解基督教教义及其逻辑,就能水到渠成地得出宪政主义的某些结论。就历史进程影响最大的事实而言,基督教社会,天然地倾向宪政民主。基督教善一元论如何成全正义一元论,并最终成全宪政民主政体,其中的细节究竟如何,当然非常复杂。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是从显性道德向隐性道德的法政性转变,还是律法与恩典的整全关系之于法政理论的逻辑起点意义,以及善一元论与正义一元论的分野所带来的“开放社会”的伦理结构,核心都是基督信仰特性,即神作为独一真神公义与恩典的统一性,以及人作为受造物所体现的罪性和有限性。
在这样一个体系中,诸多的后来可以导致为公民不服从、多中心秩序与司法程序正义的原则,都源自于耶稣基督对人类每个个体的灵魂之爱,对独特救恩的深切的关注。这是一种至善论:司法正义不是本来就成为必要,而是由耶稣基督的独特救恩所顺理成章塑造的“副产品”。如果脱离这个特性去谈论正义一元论的实现,去评论新教改革和文艺复兴的意义,就很容易步入歧途。也是基于独特的难以被其他社群理解的逻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厦的前门,这样宣告,“世人哪,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弥迦书》6:8)。
三、公民不服从催生政教分立:新教改革塑造法政国家体制
曾经担任外交部部长一职的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托克维尔一生具有传奇色彩,着有《论美国的民主》、《旧制度与大革命》、《托克维尔回忆录》等经典作品。令人钦佩的是,作为天主教保守者,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里热情赞美基督新教对美国民主的促进;在《旧制度与大革命》里,托克维尔则严厉批评了天主教贵族掌握特权后成为大革命敌人的可怕恶果。在该书的两篇附录中,托克维尔还热情洋溢地赞美了法国的一个外省,“由于有了朗格多克这种特殊政体,新的时代精神才得以平稳地渗透到这古老的制度中,它什么也不破坏,就改变了一切。其他各处本来也是可以这样办的。倘若当初那些君主不是仅仅考虑坐稳江山,他们只要把用于取消或歪曲省三级会议的一部分的顽固劲头和气力拿出来,就足以使省三级会议依照朗格多克方式臻于完善,并使之全部适合现代文明的需要”。191在这里,托克维尔并没有介绍朗格多克的主流宗教思想。
我不清楚托克维尔为何不在《旧制度与大革命》里认真介绍朗格多克的主流宗教文化,就像他在《论美国的民主》里那样探讨基督新教如何深刻地促进了美国的立宪政治。也许托克维尔本人面临着他所在的信仰社群(这是一个以天主教为民族宗教的国家)的一个困境,也即当下中国常常遭遇的一个悲凉境遇,即“政治正确”:如果在一个自由派人士主导的聚会中发表批评自由主义和某个自由派老人的观点,无论批评者多么深刻且富有哲理,都无从避免招致一群浅薄的、也许还别有用心的人物群起而攻之;在一个基督教教会,尤其是那些独立思考意识不强的教会,如果我们在团契中批评讲坛上胡言乱语的传道人和牧师,也很容易遭受到一个独立思考的自由派思想者在类似的聚会中那样的待遇。这种限制乃至剥夺异见人士的言论自由,进而发展为政治正确名义下的信仰钳制和宗教迫害的行为,无疑是人的罪性和有限性所导致的,也是《圣经》所反对的。托克维尔显然是一个真诚的、勇敢的、毫不庸俗的学者,他多大程度上在乎并畏惧这种“多数人的暴政”(或许纯粹是为了方便而进行的一时安排)?坦率地说,我不知道。
不过,《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这个遗憾在斯金纳所着的《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一书的下卷得到了很好的弥补。在第三部分《加尔文主义和革命理论》第八章《胡格诺派革命的来龙去脉》里,针对“在新教的理论之中,将反抗看作是宗教责任这个概念何时开始转变成为将它看作是道义权利这个纯粹政治性的近代概念的”这一疑问,斯金纳指出:“对这个问题可以迅速作答。关于反抗的近代理论是16世纪下半叶法国宗教战争期间胡格诺派首先十分明确地阐明的。然后又被荷兰的加尔文主义者所继承,此后这个理论进入英国,并开始成为17世纪40年代英国革命的意识形态背景的一个重要部分”。—在第九章《反抗的权利》中,斯金纳提到:“在1572年8月底法兰西全国大屠杀之后,使积极反抗与保卫君主国调和起来的任何企图终于被放弃。胡格诺教派的根据地拉罗歇尔随即停止效忠国王。对这种反抗行为,南方的若干城市也群起效尤。不出一年,朗格多克已经实际上成为王国内的一个独立的胡格诺教派飞地,运作它独有的联邦政府体系并要求得到承认和容忍。”胡格诺派战争是在法国天主教势力与新教胡格诺派之间进行的一场长期战争。针对天主教会的腐败、专制和远离《圣经》精神这一现象,15世纪和16世纪,人文主义思想和加尔文神学思想在法国迅速传播。基督教人文主义的杰出代表埃普塔尔宣扬“信仰得救”和“回到《圣经》上去”的理论,以莫城为中心积极宣传新思想。加尔文教强调信仰得救,否认罗马教廷权威和封建等级观念,主张废除繁琐的宗教礼仪,取消偶像崇拜、朝圣和斋戒,信徒选举产生神职人员,建立简化、纯洁和廉价的民主教会。大批手工业者尤其是印刷工人同小商人、农民以及下层教士成为加尔文派新教教徒,被称为胡格诺派。16世纪40年代,亨利二世指定特别法庭惩办异端,大批胡格诺派人士被处以火刑。虽然人口(100万)仅占法国总人口(1800万)的极小部分,36年的战争后,胡格诺派还是取得了局部的胜利。1598年4月,亨利四世颁布“永久性”的“南特敕令”:虽然宣布天主教为国教,但是胡格诺教徒在法国全境有信仰新教的自由,在担任公职方面享有同天主教教徒同等的权利。失败的一面则是,胡格诺战争的结束,使法国王权得到振兴。战争期间,巴黎和外省的高等法院经常抵制王命,各地贵族不同程度地恢复了“自由”特权,如征税和募兵。很快,臣民自由权利逐步被剥夺。可见,胡格诺派的抗争运动客观上促成了世俗政权内部的近代因素的生长。另外一个意义是,“南特敕令”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是基督教欧洲国家实行宗教宽容政策的第一个范例。
胡格诺派战争来龙去脉非常复杂,需要专着才能说到细节上。《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等着作已有描述,这里无须再次长篇介绍。对这段历史,凯利有一短精彩结论:“胡格诺派思想家的重心,逐渐从严格的《圣经》和基督信仰意义上的圣约观念,向着更为普遍和世俗化的政治与宪法理论转变。这种转变标志着加尔文主义关于政教关系的思想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本文之所以重视这段话,是因为有一种机遇史观、英雄史观或者二者兼而有之的观点认为,西方宪政民主的这些成功乃是若干种政治力量博弈的结果(也就是说,西方宪政民主制度的发展确立纯粹是在利益与利益的较量、权利与权力的对抗、权力与权力的制约中形成的,或者说,纯粹系人类历史发展的偶然性所致),与基督教信仰所塑造的政治社会结构的逻辑性毫无关系,或者至少关系不大。”
应该承认,无论是观念史的演变还是实践史的博弈,都是以一种非常纷繁复杂的状态交织呈现在人类历史发展的细节中去的。如果没有一种观念史的变迁,也即基督教教义内部有利于宪政民主的整全因素的重申,单纯的“利益与利益的较量、权利与权利的对抗、权力与权力的制约”不足以完全支撑起宪政民主制度在一个文明体系中的形成。
不是说利益博弈变得不重要了,而是说,浸淫了基督信仰的西方文明,经过宗教战争和新教改革这样的殊死抗争之后,更容易意识到:除非在更大层面上反思在场性政治的局限性,寻求超越性,人类别无更好的生活方式。这里需要强调,在亚非拉很多非基督教文化的第三世界国家,利益、权利、权力等诸要素未必比盎格鲁·撒克逊民族要少,但是这些国家并没有发展出宪政民主制度来。中国曾经有过多少次的底层抗争,又有过多少次的宫廷屠戮,中国人吸取教训了吗?是宗教迫害的血与火以及宗教自由缺失的苦闷,才督促人们回到了纯正教义,进而反思教会自身的组织体系和整个国家的法律体系。
今天流行着一种“文化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及其对立观点。这些观点都有其益处,也有其显然的局限。组织、制度、文化、思维、语言、礼仪等一切的人类活动都是互相影响乃至可以互相转变的。譬如广义基督教对教义的不同理解,完全可以导致产生不同的组织形式和政治模式,如天主教强调一种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的组织模式,崇尚罗马教廷在整个天主教中的最高组织地位,而基督新教则是一种相对扁平化的组织形式,各个教会、各个信徒相对平等。扩展到儒家的宗祠、佛教的寺庙、伊斯兰教的清真寺,这种差异还会更显明。那种以文化与政治不能化约这个理由来拒绝宗教思想内部的教义,进而放弃对各种文明的特质进行有效讨论的思维,不仅经不起哲学逻辑的验证,甚至连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简单的实证都经受不起。
我们进入新教内部,就新教的两个最大派别(以加尔文神学思想为指导的改革宗和以路德神学思想为指导的路德宗)对圣经的理解,尤其是政教关系的理解来看,它们对人类文明史所起的作用截然不同。路德宗也称信义宗,信义宗肯定“唯独因信称义”,即认为人是凭信心蒙恩得以称义,而不必得到神的代表教会的喜爱和足够的善行去得救。可以说,路德宗是对天主教的抗议。然而,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至少产生了两大麻烦:1.由于罗马教廷在世俗事务干预太多,路德宗干脆主张教会纯属信仰机构,从世俗领域彻底退出,由此开始了基督徒从公共领域退出的历程,否定了“政治与宗教的相互渗透与相互分立”这一在美国非常流行的政教模式,走向了法国式的政治归政治、宗教归宗教的政教模式。2.更为糟糕的是,由于罗马教廷本身就曾是一个机构,为了反抗教廷,路德宗不得不过分依赖于各地诸侯的庇护与支持。这种对掌权者的过分依赖,似乎获得了《圣经》的支持。各种试探和诸多危险即在这里产生:当片面理解《圣经》教义后,原本对国家崇拜、政府崇拜和各种世俗崇拜密不透风的防堵最后居然走向了对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包容与臣服。故在世俗政治中,路德宗无意中走向了新教改革精神的反面。
这种政教关系观俨然获得了《圣经》的支持。这里介绍一段经文,也即常常被人提起的《罗马书》十三章。其第一节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彼得前书》2:13也说:“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在《歌罗西书》3:22和《以弗所书》6:5,使徒多次指出在家庭生活中仆人应该顺服“肉身的主人”。分析《圣经》相关经文的逻辑结构安排,不难发现,这些“分工体系”都是从神人关系而被规范的。同样重要的是,相关的经文是以书信的方式呈现出来的,其收信人是教会与信徒,而不是无神论者和异教徒。书信这么强调,是希望收信人认识到此岸的暂时性,以福音使命为核心关注。这么说,毫无疑义地具有其合乎《圣经》的真理性。
然而,经文也反复强调,基督徒应当服从神,而不是服从人。《罗马书》和其他经文是有特定语境的。《圣经》里的统治者都是经神义基础上的特定程序而产生的:祭司、先知、君王三者的职分是分开的,是某种形式的分权与制衡制度。基于“约”的一般规定,《圣经》支持立宪君主制,但不支持政教合一的君主专制制度。此外,同样重要的是,立宪君主的形成,绝对不是中国传统政治观里的“成王败寇”式的丛林暴力加意识形态谎言的治理法则:政府合法地收税与非法地抢劫在性质上完全不同;顺从神的政府和对抗神的政府在政体精神上也截然相反。倘若承认必须绝对顺服一切掌权者,无异于绝对承认丛林暴力法则和谎言的正当性。就其逻辑而言,倘若君臣、主仆的关系,真如使徒所教导的那样,还具备依约而治、分权制衡等这些属性,奴隶制是可以接受的;或者说,此时奴隶制已经不存在了一一然而,由于罪,如此良善的外在秩序显然从来都未曾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