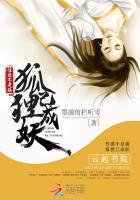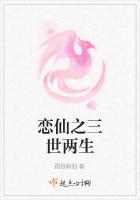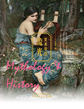粱漱溟还指出,要从事乡村建设,使乡村社会组织起来并引进科学技术,单靠乡村居民自己是不能办到的,需要"推动(或推进)社会,组织乡村",且"非组不能推,非推不能组",力量的来源即在知识分子和乡村居民打成一片。他指出:"中国问题之解决,其发动主动以至于完成,全在其社会中知识分子与乡村居民打并一起,所构成之一力量。"其中乡村居民是主体,需充分注意发挥他们的主动性,知识分子不能越俎代庖,只能先用一些旧道理鼓起他们的自信心,然后在和他们时常的接触中发现问题,适时提出问题并商量解决办法,从而逐步解决问题并提高他们的觉悟,逐渐输入一些适合新时代的道理和一些适合他们情况的科学技术。而这样的知识分子,即乡村建设运动者,是需要经过培养以使之具有乡村建设的觉悟和技能。梁漱溟办乡治讲习所,河南村治学院、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其目的就是为了培养乡村建设人才。其中山东乡建院办院7年,成效较大。它分为乡村建设研究部和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研究部招收大专毕业生予以专业训练,培养乡村建设的指导人才;训练部招收中学毕业生授以普通训练,培养乡学、村学或乡农学校的教师或指导人才。其课程切合乡村需要,生活作风上也适合乡村,没有星期天,寒暑假等。学生毕业后仍有乡村服务人员指导处进行联络,并出版《乡村建设》旬刊或半月刊予以指导。并办有农场,从事良种饲养、品种改良等,供学生实习用,然后把实用技术,良种等通过他们普及到乡村。此外,还举办教师训练班、自卫训练班及各种职业培训班,培养相应的乡村建设人才。梁漱溟说的乡村居民是一个整体,因而在他设计的构造中,地主、士绅仍占有利地位,这是被诟最多的原因所在。他想以这种构造达到和平革命(包括土地革命)的目标显然是不可能的,但他充分重视两者结合并重视发挥乡村居民的主动性和知识分子的系统网络作用的思想却是值得肯定和借鉴的。
梁漱溟基于对中国文化的独特认识和如下三个"根本见地",提出了社会本位教育系统。这三个"根本见地"是: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不可分;教育宜放长及于成年乃至终身;教育应尽其推进文化改造社会之功。社会本位的教育系统基本按行政区划设学,分国学、省学、县学、区学、乡学及市(分行政院直辖和省直辖二种)学、坊学。
梁漱溟特别重视成人教育,这与他对当时中国社会的认识有关。他认为中国当时正处在社会改造时期,"社会改造期之教育宜著重于成人",因为社会改造时期"整个社会生活企图转进于一新方式,大多数成人虽届成年,而对于此新生活方式所需之习惯能力则方为未成熟者,势非经教育不可"。梁漱溟重视成人教育还与他借鉴当时研究成果有关。美国桑戴克进行"成人与学习"的研究,认为"年龄实在对于学习之成功失败是一件小的因素。能力、兴趣、精力和时间乃是重要原因"。梁漱溟认为这是一种"重要根本见地"。
梁漱溟还提出了"教育宜放长及于成人乃至终身"的观点,并提出了三个重要理由:
1.现代生活日益繁复,人生所需要学习者随以倍增,卒非集中童年一期所得尽学,由此而教育延及成年之趋势,日见重迫。
2.社会生活既繁密复杂,而儿童较远于社会生活,未及参加,在此种学习上以缺少直接经验,效率转低,或至于不可能,势必延至成年而后可。又唯需要为能启学习之机,而唯成人乃感需要。借令集中此种学习于童年,亦徒费精力与时间,势必待成年需要,卒又以成人教育行之。
3.以现代文化进步社会变迁之速,若学习于早,俟后过时即不适用,其势非时时不断以学之不可。
梁漱溟很重视精神陶炼,认为精神陶炼比知识技能教育更为重要。这是因为他认为中国近百年的乡村破坏不仅造成了物质破产,而且造成了精神破产,而他所从事的乡村建设不是一般的乡村建设,是要谋文化改造,民族复兴,因而非使乡村的人活起来不可。因此在乡农学校或村学、乡学中均有精神陶炼这种科目,在普通学校中也有类似科目,更有音乐,武装训练等辅助之。梁漱溟认为,乡村居民活起来,是要乡村建设人员去推动的,故乡村服务人员尤其要进行精神陶炼。
乡村服务人员的精神陶炼是要"启发同学大家的深心大愿"。梁漱溟注解说,"深心即悲悯","大愿即深心",即启发大家深深地悲悯中国社会,从而立大志愿改造现实的中国社会,积极地投身到乡村建设运动中去。
精神陶炼包括三方面内容:"即合理的人生态度与修养方法的指点,人生实际问题的讨论,及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分析"。三者皆以中国民族精神为核心。历史文化分析的意义在于指出中国文化的特别处--长处和短处,从而领会民族精神,合理人生态度的指点是正面讲明民族精神,人生实际问题的解决则是指点如何运用民族精神。
过去人们往往以为梁漱溟所提倡的精神陶炼是进行封建道德教育,其实不尽然。梁漱溟对旧道德持批判继承态度,他讲的民族精神,他讲的中国文化的老根,是指人类的理性,即人之所以为人的东西。他认为周公孔子等古人发现的即在于此。其精神陶炼方法是,为适应农村环境,先用一些旧道理去鼓起乡民的自信心,然后再输入适合新时代的道理,使他们逐渐适合新的潮流。再者,他认为一种文化是不会完全消灭的,其落后了,需要新的生命,这新的生命是必须在老根上发新芽,终至于达到此种文化的复兴,等等。这些显然是与封建道德教育大相径庭的。
梁漱溟的教育思想是时代的产物,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其根本局限在于他错误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当时的形势,对乡村激烈的阶级斗争形势缺乏认识,认为阶级分化不明显,故把乡村建设亦即乡村教育作为救中国的唯一正确的道路。这种不触动旧的生产关系和政治关系,单凭乡村教育去改变社会的做法,在当时只能是一种幻想。他的乡村建设最终未能成功,也从反面说明了这一点。
但是,他把乡村教育作为改造中国社会的重要途径,注重教育对改造社会的能动作用,主张教育和社会紧密联系,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紧密结合,以及重视成人教育和精神陶炼等思想,对我们不乏借鉴意义,值得认真研究。1917年秋,梁漱溟应蔡元培之邀到北京大学执教。当时,正是举国仇孔之时,梁漱溟独行其道,打出了复兴儒学,走孔家路的旗帜。他说:"我看着西洋人可怜,他们当此物质的疲敝,要想得精神的恢复,而他们所谓精神又不过是希伯来那点东西,左冲右突,不出此圈,真是所谓未闻大道,我不应当导他们于孔子这一条路来吗!我又看见中国人蹈袭西方的浅薄,或乱七八糟,弄那不对的佛学,粗恶的同善社,以及到处流行种种怪秘的东西,东觅西求,都可见其人生的无着落,我不应当导他们于至好至美的孔子路上来吗!无论西洋人从来生活的猥琐狭劣,东方人的荒谬糊涂,都一言以蔽之.可以说他们都未曾尝过人生的真味,我不应当把我看到的孔子人生贡献给他们吗!然而西洋人无从寻得孔子,是不必论的;乃至今天的中国,西学有人提倡,佛学有人提倡,只有谈到孔子羞涩不能出口,也是一样无从为人晓得。孔子之真若非我出头倡导,可有那个出头?这是迫得我自己来做孔家生活的缘故。"
1921年,梁漱溟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把非理性的"意识"作为其哲学的立脚点,从文化哲学、心理学、人生哲学入手,比较中、西、印三大文化系统的优劣得失,得出三路向的文化结论。他认为"意欲向前"的西洋文化、"意欲调和持中"的中国文化、"意欲反身向后"的印度文化是人类文化发展的三条路向,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三个步骤或三个层次。"现在是西洋文化的时代,下去便是中国文化复兴成为世界文化的时代",而"印度文化"尽管有高明之处,但现在还不宜在中国提倡。梁漱溟的"三路向"说并不符合人类文化史的实际。事实上,西方文化除了"意欲向前"的唯物主义派别外,也有"意欲调和持中"的唯心主义派别:中国文化也不只是儒家文化,印度文化也不能仅为佛教;人类的历史发展也不可能是由科学到玄学再到宗教,或者由理智到直觉再到"现量"的退化路线。梁漱溟的"三路向"说其旨在颂扬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这种对传统文化的眷恋之情,迎合了复古主义者抵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情绪。
梁漱溟的"新孔学"道德思想有以下几方面内容:在道德的来源和体认上,梁漱溟把宇宙归结为"生命"或"生活",而体认"生命"本体的唯一途径是直觉,所以人类的道德无不来自"生命",无不出此直觉。并且把孔子的所谓"仁"也说成是"直觉"。他说:"人类所有的一切诸德,本无不出自此直觉,即无不出自孔子所谓"仁",所以一个"仁"字,就将种种美德都可代表了。"又说:"这个知和能,也就是孟子所说的不虑而知的良能,不学而能的良能,在今日我们谓之直觉。"在道德的作用上,梁漱溟主张"以道德代宗教,以礼俗代法律"的"德治"主义。他说:"从来中国社会秩序所赖以维持者,不在武力统治而宁在教化,不在国家法律而宁在社会礼俗。质言之,不在他力而宁在自力。贯乎其中者,盖有一种自反的精神,或曰向里用力的人生。"在道德理想上,梁漱溟认为,人生各种关系中,家庭关系乃是天然基本关系,此即孝悌、慈家、友恭等。唯有出于家庭生活而又高于家庭生活的"伦理本位主义"最合乎人性,是"至美至好,普遍适用的伦理道德"。
理性态度
梁漱溟提出,社会的礼俗制度的创造、形成、沿革、变化,"要莫非人类生命的活动表现,既见出人类的聪明,亦复时时流露愚蠢于其间。"而人的聪明则由理智和理性决定,因此,理智与理性之力决定了礼俗制度。
梁漱溟又进一步论断,礼俗制度所以得其成效用者,由利、理、力、惰这四种力量所决定。所谓利,指人从自身利害得失计虑上同意遵从接受礼俗制,这正好是理智之力;所谓理,指人因其公平合理,虽不尽符合自身利益,却也乐于支持拥护之,这正好是理性之力;所谓力,指人在强制之下,不得不忍受服从,这是以强霸之力令人服从者;再有一种是借习惯之力推行礼俗制度,这种习惯往往则是惰性之力。
只靠理性与理智建起的礼俗制度,只能到共产主义社会,此时没有国家、没有法制、没有矛盾和利害冲突,人心自觉自律,以理智取得生活所需,以理性处理人际关系。以往的社会礼俗虽没有仅靠理性和理智建立起来者,但"中国传统文化虽未能以理智制胜于物,独能以理性互通于人"。转了一个大圈,粱漱溟仍旧回到了颂扬儒家思想和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方面来。中国传统礼俗是"理"起了大作用。
中国传统礼俗重在理性,而西方礼俗制度则偏于理智,其"文化发达升高主要在智力强锐有以征服自然,利用自然"。因此西方的社会是"利"起了大作用。古往今来,历史舞台上不断争杀;当今社会列国仍耀武扬威,战争也成了一种重要制度,正所谓"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强霸之力,的确也是社会的一个决定之力。
梁漱溟举例说:有如印度、日本等处的贱民制度,北美、南非各地的种族歧视陋习,国际间痛加反对,国家亦有明令取消之举措。但禁而不止,正是惰性之力在起作用。生命本性是要活动的,但同时又有惰性的一面,惰性成了习惯,影响社会的习俗和制度,这也是司空见惯之事。
梁漱溟分析:用理用利,即理性、理智决定的礼俗制度,见出了人类的聪明;而用力依惰的礼俗制度,则见出了人类的愚蠢。社会发展虽有好多因素在起作用,而"力反乎闭塞隔阂不通,向着开通畅达灵活自由前进",社会的生活制度只有顺着这一方向才算对,才算好。到了共产主义,实现人类大同,便是达到了这一标准。
梁漱溟特别称赞孔子的所谓"人生哲学"。在他看来,孔子的人生哲学最符合生命的进程、人生的真谛。他一叹三赞地说:"孔子就因为把握得人类生命更深处作根据,而开出无穷无尽可发挥的前途。"
梁漱溟竭力地为宋儒的"存天理,去人欲"的反动说教辩护。在他看来,人类之所以异于一般生物者,就在一般生物只知满足自己的生活欲望,而人类则有强烈的"向上之心"。他所说的"向上之心",实际上是一种天生的神秘的自我完善的道德感。他说:"向上心,即不甘于错误底心,即是非之心,好善服善底心"。"从之则坦然泰然,怡然自得而殊不见其所得;违之则歉恨不安,仿佛若有所失而不见其所失。在中国古人,即谓之"义",谓之"理"。这原是人所本有底。"(《中国文化要义》)他不仅把人类对于物质利益的正当要求说成是"私欲",而且把人类对于真理和正义的追求也说成是"私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