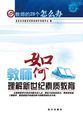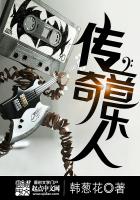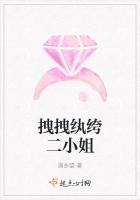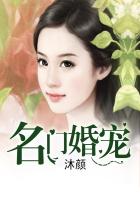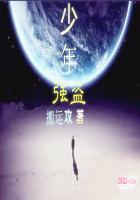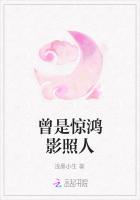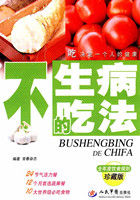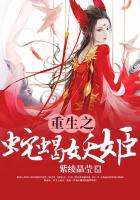能让部队在如此恶劣的天气和地形条件下坚定不移地向前挺进,证明前一阶段的训练是成功的。伍德豪斯后来回忆道,那两天他们已经对疲劳和疼痛麻木了,只剩下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意志。他们机械地在攀上山岩,从泥泞的山坡上滑下来,踉踉跄跄地涉过河床,一路披荆斩棘穿过茂密的丛林。
然而B连的空投却因为天气原因被推迟了。伍德豪斯部队已赶到了白兰河前的一座山头上,他们接到命令,在B连于9日上午9时伞降后再下山渡河。到了9日,伍德豪斯发现天气没有好转,而且起了大雾,等到9点也没有听到任何B连动静。他以为行动又推迟了,让部队暂时休息,并命令通信员关掉电台以节约电池,可就在一刻钟后,他们听到了头顶上飞机的轰鸣声。
等待已久的官兵们激动不已,他们如饿虎一般扑下山去。但到达河边时,他们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在暴雨过后,白兰河已涨到了36米宽、1.8米深,咆哮着的河水看上去十分湍急。这时,除了强渡别无选择。一名叫彼尔曼的队员自告奋勇要游过去。他在身上拴了根绳子就一头扎进涛涛河水。岸上的人见他许久不出来,害怕他被旋涡带下去,便拚命把他从水里拽出来,没想到这让他十分恼火,说原本他是想从水流较缓的深水处潜游过去的,同伴们这么一拉反而让他差点被淹死。他的第二次尝试成功了。凭借彼尔曼牵过岸的一根绳子和两艘临时扎的竹筏;部队终于安全渡过了白兰河。
可是,在过了河后伍德豪斯才发现,他们的位置偏移了,还必需再走一天才能到达预定地点,这就意味着在B连伞降当日不可能有任何联合行动了。
事实上,B连的伞降行动也不太顺利。恶劣的天气差点让人失去了耐心,当侦察机发现云海中露出一小块晴天时,指挥员果断地命令实施伞降。但近地面的风仍旧很大,很多降落伞都被吹偏了方向,落下来时挂到了树上,一些人不得不从30米高的树上胆战心惊地爬下来。不管怎么样,伞降奇迹般地成功了,除了3人轻伤外,整个伞降部队安全来到了结集地点。
丛林中的确有游击队,C连在前往目的地的途中就与敌人交了火。两个连会合后,伍德豪斯立即派出多支巡逻队,开始追捕在丛林中四处躲藏的游击队员。就在这时,几个意想不到的人出现在伍德豪斯眼前,他们就是脚上受伤的莫斯利秘他的两位同伴。他们没有回到镇上,而是沿着前面部队的足迹,一路追赶了过来。望着精疲力竭却面挂笑容的这3个男子汉,伍德豪斯哽咽无语。
部队随后接到命令,要求他们遣散居住在河谷地带的老百姓,这么做的目的是彻底切断游击队在丛林中的供给线。与此同时,英军继续追剿已被打散了的游击队。他们遇上了几次游击队的伏击,但只有两三个人受伤,其中一名士兵是在蹲下来方便时被冷枪打中了屁股。许多游击队被打死,有一名游击队的交通员被英军活捉,可是因受伤过重,不久后也死了。
赫尔斯贝行动使游击队暂时失去了一处活动据点,尽管英军后来的空中侦察表明,在英军撤走几个月又有游击队回到河谷活动,但英军上层对SAS这些行动的成绩是满意的。它证明了空降行动的可行性,并令人相信SAS在后勤保障有限、地理环境险恶的条件下仍有很强的作战能力。
3、高原上的秘密武器
阿曼是位于阿拉伯半岛东南部的一个独立的苏丹王国。它西面与也门共和国接壤,东边和南边濒临阿拉伯海。这里土地贫瘠,气候恶劣。1954年的阿曼处在塔木尔苏丹的残酷统治下,他的臣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当地伊斯兰教教长的鼓励下,住在被称为“绿色山脉”地区的人们开始奋起反抗。
“绿色山脉”是一片方圆约350平方公里的高原地带,四周悬崖围绕,惟一的通道是一条狭窄的山间小路。到1957年年底,起义军已经装备了0.5布朗宁机枪和地雷,而苏丹的军队只不过是由英国人率领的几百人而已。根据双方早些时候签署的协议,英国派出了皇家空军和一个营的步兵来帮助苏丹剿灭叛军。他们对“绿色山脉”地区进行了炮轰,但无功而返。接着两次企图以步兵占领该地区的行动也告失败。到1958年3~11月间,共有150辆汽车(包括8辆英国侦察车)被地雷炸毁。
总结了几次失败的原因,弗兰克·基特松少校想到调用特别空勤团,不仅因为此时的英军和阿曼军队都急需攀登专家和具有很强攻击力的部队,而且,因为英国政府根本上不可能冒着风险派遣大规模部队前来增援,在当时的情况下,大规模海外出兵在政治上是不能被接受的。苏伊士运河事件发生后,英国在国际上受到了来自多方面的压力。当时尚在马来亚的第二十二特别空勤团D连的42人奉命被调往阿曼。下面是一名叫拉奇的士兵对阿曼行动的自述。
我刚刚在马来亚通过了专业考核,就接到通知要调到另一战区。前往的目的地开始时是保密的,我们谁也不知道要去哪儿。我们不能透露自已是特别空勤团的人,他们发给我们蓝色贝雷帽。我们先飞到新加坡,再到锡兰,然后换机到达阿曼南部海岸的一个名叫马斯拉的小岛,这里设有皇家空军的基地。在基地,我们换乘一架特殊的军用飞机,飞往马斯喀特。这些都是后来才知道的,当时,我们只能试图通过看星星来判断自己所在的方位。我们在一片沙漠中降落了,并直接来到一座搭好的帐篷中参加情况介绍会。据说,就连带队的沃尔兹少校事先也不知道目的地,只是在途中接到密电才知道。他打开地图,向大家宣布说:“你们现在位于马攒喀特。你们一定听说过这地方吧?”
没有人听说过这里。
“这里的政府碰上些麻烦,”他先给我们介绍了友军的情况,一个营的苏丹步兵,约200人,几门大炮,再有就是我们这42个人。之后,他又给我们分析了敌军的情况。“对敌军,我们的了解不多,但至少我们知道,他们有一支大概500人的队伍,他们装备精良,是一支训练有素(曾受训于美军)的队伍,还有一支不明数量的当地部落武装,他们的装备也不错。我们面对的敌军加起来大致有2000—5000人,他们居高临下,出没于3000米高的高原;四处是悬崖绝壁。自两千年前波斯人付出损兵过半的代价征服这里后,再没有什么人敢来染指。还有一个小问题,那里所有的道路都埋有地雷。”
没有人眨一下眼,有人说道:“别相信那些鬼话,我们能打赢他们。”
我们决定兵分两路,北路派两支部队,分别为十六分队和十七分队,南路派两支队伍,分别为十八分队和十九分队。我被分在十六分队。我们没有直升飞机,没有后援,除了两辆卡车之外没有任何后勤保障。我们一下卡车,就开始攀登。天一片漆黑,敌人没发现我们的到来,事实上任何思维正常的人都不会想到我们会跳下卡车径直攀上山来。
我们是轻装上山的,一直爬到山顶也没有遇到任何反抗,我们相信,我们是能够占领住这块阵地的。第十七分队先行下山取回他们的随身装备,然后轮到我们。山顶上天寒地冻,我们水瓶里的水都要结冰了。我原本对在寒冷环境里作战感到发悚,但是既然老天保佑我们顺利登顶了,我相信,再往后我也一定能顶到底。
第二天晚上,山顶上只有我们13个人,接着就发生了令人虚惊一场的事。我正在值班,忽然传来一片嘈杂声,在漆黑的夜色下,仿佛看见一大群敌军向我们冲来,我随即踢醒了身边的人,同时举枪瞄准,我记得当时自言自语,“上帝啊,人可真不少!”我正要开枪时,我们头儿命令道:“且慢。不要开火。”我幸亏没有开枪,因为被我错以为是敌军的不过是4个农民,他们赶着一群驴,想抄近道上山。后来,他们还为我们提供了水和其他给养。我们的目的是要震摄住敌军。头一个星期,他们被我们吓着了,再过一个月,他们见到我们就闻风丧胆。我们占领了一座称为“赌场”的小山,距离敌军的主阵地只有不到1000米之遥。这时,敌军开始意识到他们的天然屏障已被我们攻破。
敌军的大营扎在一道峡谷中,峡谷横穿山脉,两面是15—30米高的悬崖峭壁,悬崖上和峡谷中布满了荷枪实弹的士兵。我们曾经远远地侦察过,发现最好的破敌方案是先攀上悬崖,绕到敌人背后,再发起进攻。我们开始出发寻找最佳的攀登路线。第一次努力失败了,我们的人只爬到4米多时就被卡住了,只好借助绳索下山。正准备再做一次尝试,我听到旁边有人在拉开手榴弹,紧接着听到他说;“让他们尝尝燃烧弹的滋味。”燃烧弹炸开了,照亮了周围一切,包括我们自己。一阵阵尖叫声传入我们的耳鼓。
这下坏了,我们完全暴露在了敌人工事的正面。你可以想象当时是怎样的情景,我们仿佛站在大街当中,两边高楼大厦的每一扇窗户里都伸出枪来向我们射击。那情形简直不可思议。我们竭尽全力应付从各个方向射来的机枪子弹,并瞅准机会还击。在一阵混战后,枪声突然停寂下来,原来是敌军用完了弹药,这时我可以清楚地听见敌军受伤者的呻吟声。就这样我们毫发无损地撤了出来。敌人龟缩在工事里,没敢冲出来追我们,他们没想到我们只有4人,而他们至少有50人。
到1958年12月,已有约40名叛军被打死,我方需要增加兵力才能拿下高原,攻下敌军的主要据点。1959年1月9日,A连抵达了。1月26日,他们会同D连,花了9个小时,每人负重45公斤,攀上2500米高的山崖。黄昏前,两个连在山顶会合了,他们的弹药和给养由飞机空投,敌人看见降落伞,以为是大规模的空降部队来了,逃到了沙特阿拉伯边境地区,特别空勤团乘势直捣敌人老巢,结束了战斗。
虽然战争结束了,阿曼却仍为贫穷与落后所困。在60年代,这里又发生过几次起义,同样被血腥地镇压了。苏丹本人遭受过数次暗杀,虽然幸免于难,但其统治的日子已屈指可数。
阿曼行动巩固了SAS在英军的地位,让人们知道这支部队在走出丛林后仍有存在的价值。
三、特别空勤团的选训体制
英国人至今仍将大卫·斯特林当作民族英雄,他所创立的特种部队模式没有仅仅成为夹在暗黄书页中的传奇,而是恒久地驻留在了特别空勤团的精神之中。一代又一代的特空团成员,无比虔诚地传承着勇敢、坚韧和智慧,由此他们也得以完整地传承了光荣、骄傲和胜利。今天的人们在景仰之余,或许会发现特别空勤团辉煌的内核也许正是由一些它最基本、最原始的元素构成的。
1、斯特林模式
英国特别空勤团的每一名成员都有极强的单兵作战能力。他们能熟练使用各种各样的武器,能在常人难以想象的不利的环境下生存并保持战斗力,能驾车、操舟、跳伞、潜水,可谓上天入地、无所不能。但是,无论特别空勤团的队员们如何挠勇善战,他们都不可能仅凭个人的能力赢得胜利,而必须依靠团队的力量。但特种部队毕竟有别于普通常规部队,他们往往有独特的组织方法。在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的特种部队在战术组成方面也不尽相同,但目的都是相同的,就是最大限度地发挥特种部队强大的打击力,最合理地将掌握多种技能的特种兵组织起来,最有效地提高部队的灵话性。
在英国特别空勤团里,最小的战术编制是四人一组的小分队,这是由特别空勤团的创建人大卫·斯特林提出的。大卫·斯特林总结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早期特种部队的经验,他发现,凡是大规模的哥曼德式的军事行动,大多避免不了灾难性的结果。大卫·斯特林本人就亲历了1941年在北非海岸的一次并不奏效的攻击行动。当时,他是英军突击队的一员。斯特林认为,英国特种部队的有些行动,如果采用小规模作战的方式会比大规模行动更加有效,他在自己的书中写道:经过适当挑选的200人,若假之以时日,进行培训,并配备足够的装备,把他们组成较小的作战单位,他们完全可以在同一个夜晚,同时攻击10个不同的目标,而如果用当时哥曼德部队的大规模进攻方式,则只可能在同一个夜晚进攻一个目标。斯特林后来有机会实践自己的理论,并逐步摸索出特种部队最小战斗单位应该有多少人。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英军特种部队开始将四人一组的小分队,作为最小作战单位并形成了传统。英军认为,四人一组是比较理想的战术组合,因为它使某一局部的突袭能力最大化,同时,又保证了战术设计中有充是的火力与是够的机动性。在战后;四人一组的斯特林小分队模式被延续了下来,并在几十年的实战中,被证明仍然是适用的和有效的。而且依然是特别空勤团的战术基础。
英国特别空勤团也许是世界上扮演角色范围最广的一支特种部队,它可以用于压制恐怖主义活动,也可以用于长途侦察、敌后渗透破坏活动等,它能够适应丛林、高山、极地、海岸、城市等多种地形作战。上述任务样式和作战环境对战术有不同的要求,但英国特空团的四人编组都能应付自如,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从战斗火力的角度上来说,通常的逻辑是人数越多,当然火力越强。但是,我们不能忽视武器装备精良程度和单兵使用多种武器能力这两个因素。事实上,小规模的特种部队由于配备了具有高度杀伤力的武器弹药,加上出众的操作能力,其火力有时反而胜过那些人数超过他们的部队。
重火力配备通常会受到特种部队的青睐,原因有很多方面。第一,重火力配备能提高特种部队的自救能力,一旦小股侦察部队遭到伏击,队员们可以凭借充足的火力杀出一条逃身之路;第二,重火力配备能提高特种部队的攻击力,当需要发起主动进攻,如袭击或伏击敌人时,重火力就显得非常重要;第三,重火力可以给予队员们更多的安全感,这种心理上的强势,在行动中也是不可或缺的;第四,重火力配备能迷惑敌人,使他们误以为是遇上了大部队。
但特种部队配备重火力会遇到不少制约因素。首先,要熟练掌握多种先进武器的使用方法并非想象中的那么容易。英国特别空勤团队员们都经过长期艰苦的武器训练,他们在射击精确度、反应时间、使用武器多样化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就为特空团配备先进武器装备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