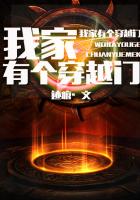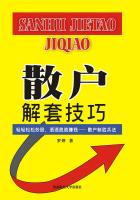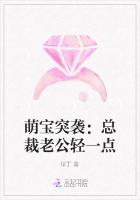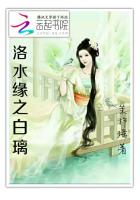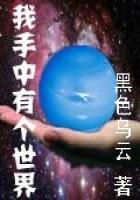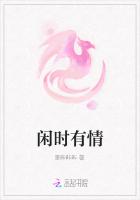对于从事人质营救作战的特种部队来说,手枪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武器。70年代,总参侦察营主要使用意大利制造的0.22英寸“贝雷塔”小口径手枪。主要是因为这种枪威力小,即使误伤人质也不易致命。但在1973的“少年之春”和1976年的恩德培行动中,小口径手枪的缺点暴露了出来:突击队用装了消音器的“贝雷塔”手枪向哨兵射击,两次均未能一枪致命,从而使哨兵来得及发出警报。从此以后,以军特种部队基本不再使用这种手枪。目前主要使用的是瑞士与德国合资制造的9毫米“西格绍尔”P226手枪和比利时FN“勃朗宁”手枪。
狙击步枪也是特种部队的重要武器,侦察营对于这一点尤为重视——根据以色列反恐怖作战大纲,侦察营担负反恐怖作战任务,因此,其每个小队中都配有4名狙击手,是一般特种部队的2倍。根据作战距离和要求的不同,各狙击手分别配备“毛瑟”SR86型、美制7.62毫米M24型和12.7毫米“巴雷特”82A1等型号的狙击步枪。有独立预算的总参侦察营还拥有其他部队想都不敢想的名贵武器——德制“黑克勒一科赫”PSGl半自动狙击步枪,每支单价在15000美元以上。
总参侦察营和其他两支担任人质营救值班任务的部队(海军13中队和警方的”雅曼”特警队)都有3套武器装备:第一套是日常训练和作战的标准装备,称为“蓝色装备”,由队员随身携带。另外两套是在进行人质营救作战时使用的装备,一套存放在值班直升机内,称为“红色装备”,另一套存放在值班机动车里,称为“黄色装备”。在进行人质营救时,首先考虑用直升机赶往现场,在不能使用直升机时则乘车前往。
总参侦察营当前的驻地是以色列中部的希尔金基地,总参侦察营的实力一直是对这支部队感兴趣的人们关心的问题。但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种猜测和说法是有现实依据的。下面所说的也仅是一个推测。
以色列特种部队的编制以小队为基础。但各支部队的小队人数差别很大,通常为10—15人,近似一个班的规模。在一些规模较大的特种部队里,小队以上还有近似连级分队的建制,可称之为“连”。
1973年“赎罪日战争”时,侦察营下辖4—5个连,每连下辖几个小队,全营实力约200—250人(其中半数为预备役),接近正规步兵营的规模。
次年的马阿洛特事件后,总参授权侦察营增招40名人员,组建专门的人质营救分队——269部队。至此,侦察营的规模得到进一步扩大。现在应该已超过300人。
侦察营营长为中校,营部设有作战、情报、通信、后勤、军械等部门。营下设连,连长为上尉。连下辖小队,小队长为少尉或中尉,每个小队约14人,其中10名是侦察兵,4人是狙击手。
1999年,以色列进行了“跨越2000”军队改革计划,将原地面部队司令部改为陆军司令部,在陆军司令部下增设野战侦察司令部,总参侦察营和其他一些部队被划归到这个司令部之下。此举表明,以色列陆军特种部队已正式获得了兵种地位。
六、“萨耶雷特”
以色列的特种部队在全球闻名,但有趣的是,以色列没有“特种部队”这个词,所有执行特殊任务的部队都被统称为“萨耶雷特”(Sayeret),在希伯莱语中,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侦察队”或“巡逻队”。虽然有些部队的性质离侦察和巡逻实在是差得太远了些,但也这么叫。因此,从称呼上,以色列的特种部队是看不出实际建制的。
传统的影响和现实的需要,使得以色列特别侧重选拔精干人员,组成规模小而效率高的特种部队,以至于今天在以色列国防军中充斥着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特种部队,代号名称更令人难以琢磨。要分清楚这些部队,的确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
情报部队在以军中是一个独立的兵种,经过以军“跨越2000”改革后,其所属的特种侦察部队统一划入在陆军下新成立的野战侦察司令部。该司令部下辖的部队中,除总参侦察营(SayeretMatkI)是以色列无可争议的头号特种部队外,另两支部队规模并不大:“亚赫曼”(目标情报)部队是一支远程侦察部队,平时作为以色列北部边境的边界观察部队,战时为以色列炮兵搜索炮击目标。特种侦察组则是一支受过特种作战训练的目视观察情报部队,可以渗入敌后对重要目标进行目视侦察。
以色列国土面积不大,人口也较少,因此,其国防体制的一个明显特点是常备军少,预备役部队众多,以备战时迅速扩充。陆军只有4个常备步兵旅,属步、伞兵司令部。(以色列原来一直没有专门的特种作战司令部,步、伞兵司令部在相当程度上担负了这个职能,尤其是在指挥联合特种作战时。)这4个旅各有一个旅属侦察连,即戈兰旅(步1旅)侦察连(Sayeret Golany)、吉瓦提旅(步84旅)侦察连(Sayeret Givaty)、纳哈尔旅侦察连(Sayeret Nahal)和伞兵旅(空降步兵第35旅)侦察连(Sayeret Tzanhanim)。从字面看,很容易将这4个步兵侦察连的职能联想为单纯的侦察兵,实际上,这4支部队都接受过反恐怖作战训练,担负反恐怖作战任务。
戈兰旅组建于1948年,以色列独立战争期间,全旅将士戴土黄色军帽,是目前国防军战斗序列中历史最悠久的部队,在独立战争中,从最北方的黎巴嫩边界,一直打到最南方的红海之滨,赢得了国防军第一旅的称号。独立战争后,戈兰旅在历次中东战争中,均立下了汗马功劳,现驻北部军区(以色列全国分为北、中、南三个军区)。戈兰旅侦察连以带飞翼的银色虎头为标志,号称“飞虎”,起源于独立战争中建立的特种侦察排,和这个旅一样,是国防军中历史最长的步兵侦察分队。在反恐怖作战方面,曾参加过1976年恩德培机场人质拯救行动。与其他步兵旅不同的是,戈兰旅还下辖一个“胡桃”侦察营(Sayeret Egoz),但这个营与旅侦察连担负的任务不同,主要是在以占南黎地区进行反游击作战。
第35空降步兵旅通常称伞兵旅,戴红色贝雷帽,是以军两支王牌旅之一。1948年,国防军建立了第一支伞兵部队,后发展为伞兵890营。1954年,890营与一支名声不佳,然而却是军中精锐的101部队合并,并于次年扩编为202伞兵部队,参加了1956年的西奈战役。由于指挥官沙龙的轻敌冒进,202部队在米特拉山口遭受重大伤亡。战后,202部队的两个现役营——890营和“纳哈尔”空降88营合编为伞兵35旅。由于继承了特种部队101部队的血统,这个旅在战争中以机动灵活著称,现驻中部军区。伞兵旅侦察连源于101部队的侦察分队,建旅时成为旅侦察连,是特种部队中的特种部队,参加过多次著名的作战行动。
吉瓦提,意为山丘。这个旅组建于1983年,继承了独立战争中的老吉瓦提旅(第5旅)的称号,现驻南部军区,建旅时被授予紫色军帽。独立战争中的吉瓦提旅侦察连,是一个在沙漠中神出鬼没的吉普车突击连,到处突袭埃及部队,号称“参孙之狐”。新建的吉瓦提旅侦察连也继承了这一称号。
以浅绿色军帽为标志的纳哈尔旅,是建于1983年的一支新部队,驻中部军区。“纳哈尔”是“青年战斗先锋队”的简称,其前身是以建国初期建立的,一支担负军垦戍边任务的生产兵团。1983年“纳哈尔”部队建立了一个独立步兵旅,担负总部作战值班任务。以后由于部队任务的变化,纳哈尔步兵旅已经不再具有军垦部队的性质,并最终于1999年脱离“纳哈尔”部队序列,仅保留原有的“纳哈尔”称号。该旅侦察连曾在约旦河谷地带参加过边界反游击作战。
以色列的特种部队虽不像美、英等一些国家那样庞大,在国防军中也未形成统一的编制,但其发展历史却很久远,
七、反恐行动、战例
1、21小时和90秒
1972年5月8月,星期一。由布鲁塞尔飞往以色列卢德国际机场(即后来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的比利时“萨贝纳”航空公司571航班正在飞越南斯拉夫上空时,驾驶舱门突然被打开了。一名瘦小的男子用手枪对准机长拉杰兰德·利维的头,告诉他飞机被劫持了。
这位其貌不扬的劫机者名叫阿里·塔哈,阿布·萨尼纳,是“黑九月”组织中的劫机专家,4年前指挥了将以航班机劫往阿尔及尔的行动,迫使以色列政府释放了被其囚禁的“法塔赫”成员。3个月前,他又劫持了一架飞往阿登的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班机,让西德政府破费了500万美元赎金。本次劫机是这位专家指挥的第3次行动。这次,他决定来一个更刺激的——不让飞机转向阿拉伯国家,而是继续飞往卢德机场降落。
飞机上还有他的三个同伙,一男二女:阿卜杜勒·阿齐兹·阿特拉什、莉玛·伊萨·塔努斯和特雷莎·阿斯哈克·哈尔莎。两位女士把手枪、手榴弹、2个2公斤的炸药包、电雷管和电池等好一大堆东西藏在化妆包和内衣里带上了飞机。飞机起飞后,她们到洗手间里取出了武器,两个男人持手枪,女人则持手榴弹。在萨尼纳控制驾驶舱的同时,他们分别占据了飞机上的要害位置,控制了乘客。
控制了飞机后,恐怖分子收缴了机上所有人质的护照,从99名乘客和10名机组成员中找出了67名犹太人,将他们押到飞机后部看管起来,而非犹太人坐在前排。
18时许,阿布·萨尼纳向塞浦路斯尼科西亚机场塔台通报了571航班被劫持的消息。5分钟后,尼科西亚机场塔台将此情况通报了卢德机场塔台。不久后,571航班与卢德塔台直接建立了无线电通联,通知他们飞机将在卢德降落。一个小时后;这架庞大的波音707飞机驶入了距卢德机场主楼约3公里的16号滑行道。
经过4年前以航班机被劫事件后,以色列人对类似的事件已经有所准备。安全部门在接到571航班被劫持消息后,立即向有关部门发出了警报信号——“同位素”。这是以色列处理飞机被劫持,并迫降在卢德机场时的行动预案代号。不一会儿,机场塔台底层的房间里便坐满了国家安全的决策人物:国防部长摩西·达扬、交通部长西蒙·佩雷斯、总参谋长大卫·埃拉扎尔、副总参谋长兼作战部长,以色列·塔尔、空军司令莫蒂·霍德、中部军区司令拉哈万·扎维、南部军区司令阿里尔,沙龙、总参情报部长阿哈龙·雅里夫;步伞兵司令拉菲尔·艾坦……从塔台到总理梅厄夫人的办公室架起了直通军用电话线路。与此同时,总参侦察营值班应急分队也在营长埃胡德·巴拉克中校的带领下火速赶到了机场。
外面,阿布·萨尼纳正向塔台宣读一份冗长的、包括317名被以色列关押的巴勒斯坦人的名单。以色列必须释放这些人来交换人质。但他似乎没有想到,这时以色列的总理已经换成了以强硬著称的梅厄夫人,她选择的国防部长则是以色列的名将摩西·达扬。达扬首先确定的原则便是,绝不答应恐怖分子的要挟。
然后,达扬等人决定了一个三部曲式的方案:第一步让飞机无法起飞,然后尽量拖延时间,等各方面准备好后,在合适的时机发动突袭。
巴拉克带领一队侦察兵,从劫机者看不到的方向悄悄接近了飞机,打开了仍发动着的飞机引擎的油管。飞机下面的滑行道上立即聚起了一汪黑色的机油。然后,他们不声不响地悄悄撤了回来。几个小时后,巴拉克率侦察兵再次出动,破坏了飞机的滑行操纵系统,还在飞机前轮钉进了钉子,放掉了轮胎里的气。
21时65分,总参情报部长雅里夫出面与阿布,萨尼纳对话,后者要求以色列在2小时内放人,再用两架飞机把他们送往开罗。而雅里夫称,在2小时内他只能找到名单上的15个人。后来阿布·萨尼纳要求用阿拉伯语谈判。于是,被占领土事务协调人什洛莫·加泽特准将(后任总参情报部长)把这方面的专家——国家安全总局调研处长维克托;科恩从家里召往机场;但阿布·萨尼纳显然没那个耐心去等,22时30分;他宣布飞机上已被安放了一小时之内爆炸的定时炸弹。塔台里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科恩恰好在这时赶到,开始用阿拉伯语和阿布·萨尼纳对话。
“我对他们讲,”科恩后来回忆说:“我讨厌那些只会用武力的粗人。我会帮助他们,按他们的要求把红十字会的人找来。我的言谈彬彬有礼,甚至称他们为‘先生们,(gentlemen),从不向他们施加压力,也不说他们威胁无辜者和妇女儿童的做法不道德。如果达扬要我停一会,我就对他们说我有事必须离开,并提出必须离开的理由,但再三强调我会回来和他继续对话,以免使他绝望。这种做法很荒唐,但是我们互有所求:我清楚他想活着出去,而我们也想让他活着,免得他把飞机和旅客一起炸上天。
科恩肩负着一个重任:他必须把握住适于对恐怖分子采取行动的关键时机。“曾有一刻,达扬问我进行突击是否合适,我回答说时机还不成熟。”
在科恩把恐怖分子说得无暇他顾的时候,塔台里的人们在忙着他们的工作:国家安全总局飞机保安小组强烈要求承担突袭任务,这本来也是他们分内的工作。但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还是选中了以行动敏捷著称的总参侦察营。第一个设想的突击方案是,让突击队员身着军装,在精心选择的时机突然出现在飞机上,用威慑火力慑服恐怖分子。但这样做很容易误伤到人质。经考虑再三之后,指挥部最终决定让突击队员假扮成去检修飞机的以航机械师,接近飞机后再发动进攻。在行动中,突击队使用0.22英寸口径的“贝雷塔”手枪。这种枪的威力小,即使误伤人质也不易致命。
巴拉克立即着手确定参加突袭的人员名单,他刚刚定好,营里又有3名军官匆匆赶到机场,要求参加突击队,巴拉克说不过他们,只得调整名单,把他们加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