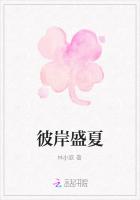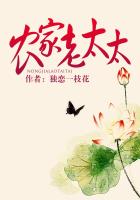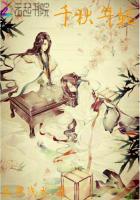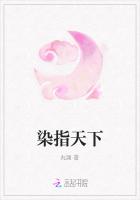文学复古运动在正德、嘉靖之际发生新变,表现为六朝、初唐体的盛行。从杨慎和薛蕙开始,六朝初唐派就展现出“沉博绝丽”和“淡泊为宗”两种不同审美旨趣。在“嘉靖十才子”的酬唱过程中,六朝体的“艳丽”和初唐体的“雍容”交映生辉,最后,落尽繁华,向着崇尚“古澹”的中唐派转移。六朝初唐派的活动展现了复古思潮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在诗体选择、审美理想、文化底蕴、艺术风格和表现特征诸方面,阐释着古典诗文传统的丰富内涵。
(第一节)以六朝、初唐为审美典范的创作趋向
嘉靖前期诗文思想的主要问题是文学典范的转移。正、嘉之际,杨慎与薛蕙对早期文学复古运动“拆洗少陵”的书写风气表现出不满,为重构汉魏诗学与盛唐诗学的连续性,他们推崇六朝、初唐文学,形成了系统的文学史述。这种观念首先在与何景明的诗学探讨中透露出来,最终影响到嘉靖前期的文学走向。不过,杨慎和薛蕙有着不同的审美追求,杨慎的创作倾向于“沉博绝丽”的风格,薛蕙和嘉靖初年的高叔嗣则明确地向“淡泊为宗”的方向发展,由此展开了六朝、初唐派发展的双重线索。
一、向六朝、初唐的典范转移
六朝文学和宋诗学一起,曾是古学复兴中受到抑制的师法对象。李东阳《麓堂诗话》说:“六朝宋元诗,就其佳者,亦各有兴致,但非本色,只是禅家所谓小乘,道家所谓尸解仙耳。”六朝文体与吴中文风向来互为表里,所以李东阳论诗讲究脱去“宋人气习”和“吴中习尚”。他说:“王介甫点景处,自谓得意,然不脱宋人气习。”而“六朝所制则出于偏安僭据之域,君子固有讥焉。”“原博之诗醲郁深厚,自成一家,与亨父、鼎仪皆脱去吴中习尚,天下重之。”随后,鼓吹复古的李梦阳责难吴中才子和任职南都的边贡说:“今百年化成,人士咸于六朝之文,是习是尚,其在南都为尤盛。予所知者顾华玉、升之、元瑞皆是也。南都本六朝地,习而尚之固宜。廷实,齐人也,亦不免何也!”汉魏古学、六朝习尚和宋人气习构成不同的审美类型。历史地看,嘉靖时期的六朝初唐体和号称崇宋的唐宋派的流行,无疑是古学复兴的兴替和变革。
李梦阳和何景明虽然为复古方法和思路争论不休,但是他们在“文必先秦两汉,诗必汉魏盛唐”的典范选择上心存默契。何景明《汉魏诗集序》说:“汉兴,不尚文,而诗有古风。岂非风气规模,犹有朴略宏远者哉!继汉作者,于魏为盛,然其风斯衰矣。晋逮六朝,作者益盛,而风益衰。其志流,其政倾,其俗放,靡靡乎不可止也。”李梦阳《章园饯会诗引》说:“文气与世运相盛衰,六朝偏安,故其文藻以弱”,“大抵六朝之调凄宛,故其弊靡;其字俊逸,故其弊媚。”复古运动的巨子们倾心赞叹“朴略宏远”的汉魏之风,不满意六朝靡靡之音。然而,即使在古学复兴如日中天的弘、正时期,“是习是尚”,仍然如缕不绝。特别是经杨慎和薛蕙在正德、嘉靖之际的提倡,六朝与初唐体竟然蔚然盛行。
作为文学复古运动中的新趋向,六朝初唐派的肇始必须从何景明与杨慎、薛蕙的关系说起。杨慎是正德六年(1511)状元,服丧家居,直到正德八年始授翰林修撰,第二年,薛蕙进士及第。这基本可以视为六朝初唐派文学活动的开端。嘉靖三年(1524)七月,杨慎因大礼仪事件贬谪滇中,薛蕙则在这一年稍早的时候《为人后解》下狱,次年以他事罢归。从正德八九年到嘉靖三四年,大约十年时间,是他们交游和创作的活跃期,也是新思潮的形成期。《四库总目》说:“慎博洽冠一时,其诗含吐六朝,于明代独立门户。”沈德潜《说诗啐语》说:“杨用修负高明之才,沉博绝丽之学,随物赋形,空所依傍,读《金沙江》、《锦江舟中》诸篇,令人对此茫茫,百端交集。李、何诸子之外,拔戟自成一队。五言非用修所长。过于浓丽,转落凡近。同时有薛君采蕙,稍后高子业叔嗣,并以冲淡为宗,五言古风,独饶高韵。后华子潜希韦柳之风,四皇甫仰三谢之体,虽未穿溟津,而氛垢已离。正嘉之际,独称尔雅。”从杨慎、薛蕙到高叔嗣,再到华察和四皇甫,沈德潜勾勒出了初唐之朝派的发展脉络和风格取向。但他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拔戟自成一队”的六朝初唐派与“李、何诸子”不仅有对立关系,更存在着藕断丝连的亲缘性和赓续性。
杨慎和薛蕙在京活动时期,京城的文学领袖是复古派巨子何景明。从正德六年到十三年,一直任职京师的何景明,成为薛、杨的主要唱和者。王廷相描述当时京城词林的状况是:“彼时才杰游帝傍,信阳之何棠陵方,大梁翩翩李川甫,吏部薛生犹擅场。”信阳之何是指何景明,吏部薛生就是薛蕙,棠陵之方是指方豪,李川甫是指李濂。李濂追忆说:“往正德丁丑春正月,余以沔阳守,人觐都下,而汶上尹孟望之洋亦以职事至,维时崔子钟铣为翰林侍读,何仲默景明为中书舍人,薛君采蕙为刑部主事,咸在京邸余五人者,文字之会,杯酒赓和,朝夕胥晤,甚欢也。”这种唱和活动理所当然是文学复古运动的一部分,同时也隐匿着新的思想苗头,孕育着复古思潮分化的趋向。
杨慎《升庵诗话》记载了他与何景明、薛蕙交游的佚事,展现了他们在文学方面的相互启发与影响:
吾亡友何仲默一日读《焦仲卿妻乐府》,谓予曰:“古今唯此一篇。更无第二篇也。凡歌辞简则古,此篇愈繁愈古。子庶几焉。可做一篇与此相对。”予谢不遑,然亦未有兹奇事可当之也。去今二十年,屏吾滇云,复忆仲默言,乃操觚试为之。
何仲默枕藉杜诗,不观余家,其于六朝、初唐,未数数然也。与予及薛君采言及六朝、初唐,始恍然自失,乃作《明月》、《流萤》二篇拟之,然终不若其效杜诸作也。
宋严沧浪取崔颢《黄鹤楼诗》为唐人七言律第一。近日,何仲默、薛君采取沈俭期“卢家少妇郁金堂”一首为第一。二诗未易优劣。或以问予,予曰:“崔诗赋体多,沈诗比兴多,以画家法论之,沈诗披麻皴,崔诗大斧劈皴也。”
亡友何仲默尝言:宋人书不必收,宋人书不必观。余一日书此四诗讯之曰:“此何人诗?”答曰:“唐诗也。”余笑曰:“此乃吾子不观宋人之诗也。”仲默沉吟久之曰:“细看亦不佳。”可谓倔强矣。
这些诗话记述了他们对汉乐府以下历代诗篇的评价倾向,体现了这个酬唱群体内部的分歧与诗学典范的重构过程。杨慎秉持较为公允、通脱的文学史观,不断地在六朝、初唐和宋诗诸方面挑战何景明的思想底线。何景明虽兀自“倔强”,偶尔也不免“恍然若失”。新的思想苗头还是浮现出来。此前的何景明“枕藉杜诗,不观余家”,不欣赏六朝和初唐习尚。然而,在杨慎、薛蕙的怂恿下,开始对初唐诗兴趣盎然。
今存何景明《明月篇》,其序云:
仆始读杜子七言诗歌,爱其陈事切实,布辞沉著。鄙心窃效之。以为长篇圣于子美矣。既而读汉魏以来歌诗及唐初四子者之所为,而反复之,则知汉魏固承三百篇之后,流风犹可征焉。而四子虽工富丽,去古远甚,至其音节,往往可歌。乃知子美辞固沉著,而调失流转,虽成一家语,实则诗歌之变体也。
夫诗本性情之发者也。其切而易见者,莫如夫妇之间,是以三百篇首乎雎鸠,六义首乎风。而汉魏作者,义关君臣、朋友,辞必托诸夫妇,以宣郁而达情焉。其旨远矣。由是观之,子关之诗,博涉世故,出于夫妇者常少,致兼雅颂,而风人之义或缺,此其调反在四子之下欤!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何景明后期的文学思想存在明确的转向,至少在歌行创作方面从“枕藉杜诗”转向崇尚“初唐四子”的文学风格。何景明认为杜甫的七言诗有两种缺失:一是以沉著之辞破坏了诗歌声调流转的音乐美和自然美;二是虽兼雅颂之致却遗失了古典诗学托诸夫妇、宣达性情的风人之义。前者是形式因素,后者是形式中寄寓的意义因素。那么在七言长篇名家里,谁是内涵风人之义的书写典范呢?何景明早期选择了杜甫,后期转向了初唐四子和沈俭期。他认为,初唐四子的文学藻饰富丽,“去古甚远”,但其“转韵之格”中浸润着温柔敦厚的艺术感染力与德性之美,继承和发扬了汉魏诗歌的流风遗韵,而直陈事实、言辞沉著的杜甫因其诗缺少风人之义,不过只是“别子为宗”。
胡应麟《诗薮》认为,“自北地宗师老杜,信阳和之,海岱名流,驰赴云合”。而“嘉靖诸子见谓不情,改创初唐,斐然溢目”。在宗法老杜和改师初唐之间,何景明的历史位置耐人寻味。正德十二年进士王廷陈“为庶吉士,诗有名,其意不可一世,仅推何景明而好薛蕙、郑善夫”。皇甫汸为王廷陈的《梦泽集》作序,褒扬他“潘陆齐轨,下拟阴何,五七言律,沈杜比肩,参之卢骆”。何良俊《四友斋丛说》评价正嘉之际的诗人说:“薛西原规模大复,时出入初唐,而过于精洁,失其本色,便觉太枯;高子业是学中唐者,故愈淡而愈见其工耳;马西玄极重戴时亮,二公皆工初唐故也。”何景明、薛蕙以后,王廷陈、马汝骥、戴时亮、江晖诸公皆好初唐诗学。正德后期学习六朝初唐的风气渐露端倪,作为文学复古运动的领袖,何景明对杜诗学的质疑和对初唐体的认同极具启示意义。
同时的张含对何景明、杨慎的讨论有如下跋语:
六朝、初唐之作,绝响久矣。往年吾友何仲默尝云:三百篇首雎鸠。六艺首乎风,初唐四子音节往往可歌,而病子美缺风人之义。盖名言也。故作《明月》、《流萤》诸篇拟之,然微有累句,未能醇肖也。升庵太史公,增损梁简文帝《华烛引》一篇,又别拟作此一篇,此二篇者幽情发乎藻绘,天机荡于灵聪。宛焉永明、大同之声调,不杂垂拱、景云以后之语言。
初唐诗不仅兼具流转之调和风人之义,而且还有着重视藻绘的修辞倾向。后者更显著地体现在六朝诗风之中。张含以为,杨慎所作精深华妙,宛然在六朝、初唐之间,比何景明所作更为“醇肖”。杨慎是六朝初唐诗的主要倡导者,他以为,六朝诗虽然“缘情绮靡之说胜,而温柔敦厚之意荒矣”,但“以艺论之,杜陵诗宗也,固已赏夫人之清新俊逸,而戒后生之指点流传,乃知六代之作其旨趣虽不足影响大雅,而其体裁实景云、垂拱之先驱,天宝、开元之滥觞也。独可少哉!”既然如此,杨慎理所当然要为“近日雕龙名家,凌云鸿笔,寻滥觞于景云、垂拱之上,著先鞭于延清、必简之前,远取宋齐梁陈,径造阴何沈范”的写作趋向溯源导流,推波助澜。正、嘉之际,何景明对初唐诗的赞扬,无疑为杨慎、薛蕙等倡导六朝初唐体起到积极的影响,而杨慎及其追随者则堂而皇之把六朝习尚推到了诗文思想的前沿。
二,从“拆洗少陵”到学习“六朝俪篇”
从正德十年到嘉靖三年间,杨慎至少有六年在京城度过。与何景明、薛蕙对初唐诗共同探讨和倡导,是他这一时期文学活动的重要内容。但这样的时光对杨慎来说太短暂了。在愈演愈烈的大礼议事件中,他完成了其政治生命惊鸿一瞥的演出。嘉靖三年七月左顺门哭谏事件,杨慎两遭杖责,毙而复苏。最终谪戍云南,开始了三十五年的流放生涯。他自嘲说:“千钧之弩,一发不鹄,则可永谢焉。复效枉矢飞流,嚆箭妄鸣乎!”政治的博弈中。生命宛如离弦的箭,在一次未能中鹄的射击之后,便被掷向荒原。
杨慎虽远离政治中心,但他的思想与言说穿越时空,对嘉靖文学产生着持久的影响。他的文学思想保存在其《诗话》及少数书信跋序中,这些文献多数完成于滇南,在嘉靖士人中广为传播,影响着嘉靖文学思潮的流向。其中,他对复古思潮的反省和对杜诗的批评,尤为引人注目。他说:
谓诗歌至杜陵而畅,然诗之衰飒实自杜始。经学至朱子而明,然经之拘晦实自朱始,是非杜、朱之罪也。玩瓶中之牡丹,看担上之桃李,效之者之罪也。夫鸾辂生于椎轮,龙舟起于落叶,山则原于覆篑,江则原于滥觞。今也,譬则乞丐。沾其剩馥残膏,犹之瞽史,诵其坠言衍论,何惑乎道之日芜而文之日下也!何景明在《与李梦阳论诗书》说:“夫文靡于隋,韩力振之,然古文之法亡于韩;诗弱于陶,谢力振之,而古诗之法亡于谢。”这句话因断语鲜明,矫枉过正,成为复古派文学史观的代表观点。杨慎以类似的方式言说杜诗,表达标新立异与改弦更张的强烈信心。杜甫是文学复古运动最主要的模仿对象。李梦阳说:“做诗必学杜,诗至杜,如至圆不能加规,至方不能加矩也。”何景明则“枕藉杜诗,不观余家,其于六朝初唐未数数然也”。杨慎总体上给这位伟大诗人以颇高的评价,但对其弱点也往往有直言不讳的批评。
在杨慎看来,作为诗圣的杜甫不仅会偶然有“太露”、“偏枯”的情况,而且近体律绝亦有可议之处,其七言律诗虽然雄壮铿锵,却“古意少衰”;至于绝句,更是“本无所解”,何必效之。让人惊讶的是,当他看到青年士子熟读杜诗时,竟然这么说:“近有士人熟读杜诗。余闻之曰:‘此人诗必不佳。’所记是棋势残着,元无金鹏变起手局也。”可以这样理解杨慎的意思:他的杜诗批评源于对流行风尚的反省,是一种当代批评。此前,经过李、何提倡,杜诗成为人们学诗的门径,但是若无对古典诗歌“真识冥契”的体验,门径就变成窠臼,诗人也只能成为捕风捉影、人云亦云的门外汉。杨慎对杜诗挑刺式的评价表明其并非杜诗的盲目崇拜者,对熙熙攘攘的东施效颦之流更为不满,痛下针砭。他在这里用自己的“狂谈异论”与流行的“俗谈”旗帜鲜明地区别开了。
杨慎对李梦阳、何景明的创作有着中肯的赞赏,但也不无微词。他这样评价李梦阳:“余评空同诗,五言绝句胜七言绝句,五言古、七言古胜七言律、五言律,乐府学汉魏似童谣者又绝胜。世徒学其七言律,是徒学其下者耳。”文学复古运动主张古体学汉魏,近体学盛唐,特别是学杜甫七律,杨慎认定李梦阳古诗优于近体,其七律写得并不优秀,就是说其学杜的部分是失败的。《明诗综》记载杨慎的话说:“空同以复古鸣弘、德间,观古乐府幽秀古艳,有铙歌童谣之风,其古诗缘情绮靡有徐、庾、颜、谢之韵,而人但称其七律,予谓空同之可传者不在律,空同之律,少陵之遗梯耳。”他认为李梦阳的乐府古诗皆臻妙境,唯独七律拾人余唾。何况那些闻风响应的追随者,皆如瞽如丐,不能自拔。《静志居诗话》说:“(薛蕙)与杨用修论诗曰:‘近日作者,摹拟蹈袭,致有拆洗少陵,生吞子美之谑。求近性情,无若古调。’直以沿流讨源自许。”杨慎与薛蕙具有同识。他们认为杜诗“古意少衰”,尝试“沿流讨源”,回归少陵以前的诗歌传统。
杨慎对杜甫、李梦阳的微言讽喻,彰显出他对先唐诗歌的偏爱。他强调李白和杜甫从《文选》中汲取了丰富的艺术营养:
李白前后三拟《文选》,不如意,悉焚之,惟留恨别赋。
古人谓李诗出自乐府古《选》,信矣。其《杨叛儿》一篇即“暂出白门前”之郑笺也。因其拈用而古乐府之意益显,其妙益见。如李光弼将子仪军,旗帜益精明,又如神僧拈佛祖语,信口无非妙道,岂生吞义山、拆洗杜诗者比乎。
谢宣远诗:“离会虽相杂。”杜子美“忽漫相逢是别筵”之句,实祖之。颜延年诗:“春江壮风涛。”杜子美“春江不可渡。二月已风涛”之句实衍之。故子美谕儿诗曰:熟精《文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