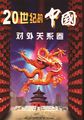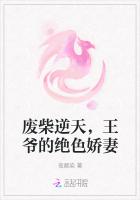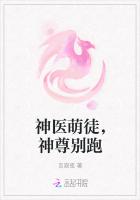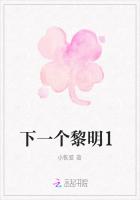自法国大革命发生那一天起,便存在着褒贬之间的激烈对抗。不过对于它是一场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大变局,却是几乎不存争议的,大多数争论也正是围绕这个共同点展开的。分析其中原因,这场开启现代革命史的事件,诚如托克维尔所言,有着与过去的动乱迥然不同之处。它并非改朝换代那样的周期性灾变,而是裹挟着大量所谓的现代性问题,其世界观和意识形态因素有着划时代的意义。这使当时和后来的许多思想和政治精英认为,人类的全部历史,似乎就包含在这场大革命所承诺的希望之中。换言之,它不是城头变换大王旗的寻常事,而是关系到人类向何处去的大问题。
过去受单线进步史观的影响,对于发生在二百多年前的这场大动荡,因其标举自由、平等、民主、人权这些现代人极为看重的价值,大体上肯定者多而反对者寡。近些年的风向则渐趋相反了,这跟我们正在向后革命时代或执政党时代的转变,想必有一定的关联。政治、社会和文化思考的需要有变,史学叙事的调子也会随之而变,再次印证了“历史的科学性”靠不住的老话。记录在案的史实和文献固然是客观的,可是人的眼睛并非实验室里一动不动的显微镜,它喜欢随着自己的兴致,在漫长的历史画卷前四处打量,说不定会凝神于何处。用历史编纂学的说法,尘封的史实和文本好像仍在不停地“做着什么”,成为一个具有连续性、充满戏剧性和“原创性”的重构过程。它会随着时代布景——无论是历史的还是话语的——而变化,使单一的历史写作成为不可能。文艺复兴的意大利语人有感于此,曾把文本作者在后世的遭遇称为他的“命运女神”(Fortuna),而法国人则称之为“分娩”(travail),当代法国革命史大家傅勒说得更妙,把它喻为“由现代殃及古人的传染病”。
这种现象的一个具体反映,便是近些年来反思法国革命的着作不时出现。张芝联等新老学者的大量文章自不待言,在专着方面,国内先有朱学勤先生那本被高调的黄万盛诨称为“思想炼金术”的《道德理想国的覆灭》和最近王养冲等先生主编、力求摒弃过去苏俄史观影响的《法国大革命史》。在翻译文献方面,虽然我们依然看不到泰纳或梯也尔的汉译,但毕竟已有托克维尔的《旧制度和大革命》、柏克的《论法国革命》、迈斯特的《论法国》和傅勒的《思考法国大革命》等着作近年来相继问世。当然,这其中也不可忽略阿克顿的《法国大革命讲稿》。
阿克顿勋爵在1895年当上剑桥大学的“钦定史学教授”后,便开设了一门讲授法国革命史的课。他每周下午在剑桥三一学院开讲,一讲就是四年(1895-1899)。其间他不时对讲稿做些修改增删,但最终还是觉得它“非常粗糙”,取消了原定的出版计划。因此,直到他去世后的1907年这些讲稿才得以问世。拜秋风先生的译笔,我们现在可以一睹这位下笔一贯吝啬、说历史掌故比严肃的史学写作更为出色的史家的风采了。
过去读阿克顿时,便留下了一个强烈的印象。与许多现代史家有一显着差别,他的笔端总为宗教信仰留出不可动摇的位置。他相信历史并非纯粹的事实,而是有道德与信仰的法则贯穿于始终。史学虽以记述历史真相为本分,但它是一门事关信仰的学科,必须承载起高贵的精神使命。它当以自身的责任,去弥补政治和法律规范的不足。它既要借助信仰以辨明善恶,又要为信仰提供经验的佐证,以完成传递宗教和政治真理的职守。
这种史观显然是与他师承德国大史学家兰克有关。后人常将阿克顿与兰克加以比对,认为师徒二人一尚科学,一尚信仰,而信仰史学显然与现代人讲究科学精神不合,故多宗兰克而弃阿氏。然而这多半是受兰克方法论所迷惑,并未充分注意兰克是继承与创新兼而为之的。他虽为近代“科学的史学方法”的开先河者,在历史观念上却依然十分传统。他以史料的精湛运用而着称,但其视野仍囿于权贵精英和各国间的纵横捭阖,从不涉及对社会和经济因素的分析。他曾明确说过,从国家的历史中,他看到的是“上帝的想法”,要在“每一个存在中寻找上帝的永恒因素”。就此而言,阿克顿的《近代史讲义》和这本《法国大革命史讲稿》的师承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只不过他把兰克更为看重的“民族实体”,置换成了带有普遍性的“信仰自由”。
从这种史观出发,阿克顿给史家提出了两项十分苛刻的要求。一方面,他必须保持史学的尊严和自律,以审慎超然的姿态,高居于各种纷争之上,努力逼近史学所要求的正义境界——在谈论尤里安时,他当力求公正,使基督徒和异教徒皆能认可;他应当提供一个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皆可理解的路德,以辉格党和托利党的共同语言去描述华盛顿;用法国和德国的爱国者都能接受的标准去评判拿破仑。这种论调,显然与他那个时代如火如荼、并且至今余威犹存的“民族史学”大异其趣,符合此一水准的史乘我们也难得一见——想想如今中日韩三国的教科书之争,或可体认出个中三昧。
此外,史家又要做好“神启”的仆人,向世人揭示自由,尤其是信仰自由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在阿克顿看来,古往今来,人的欲望和感情使世间摆脱不了邪恶,唯有信仰的存在才使人类没有陷入绝望,唯有自由的壮大过程为人类提供了企盼于未来的勇气。故史家察既往之兴衰,当以铸造将来之法戒为主旨,切不可文过饰非,只去考虑人们所属的阶级、时代和环境,从“人生邪恶秘密的体验中编造出各种例外,让罪行消弥于群体责任之中”。这或可让我们想到中土的史家之言:“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令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刘知己,《史通》)不过,阿克顿这种史学上的道德观,并非只为让“乱臣贼子惧”,而是无分善人恶人,意在警示整个人类弱点的。对阿克顿推崇备至的哈耶克便认为,阿氏“极严格地把普遍道德标准用于一切时代和条件”的做法,大概是他最不易为崇尚多元的现代人所接受的原因。
今人在解释各种事物时,喜欢建立某种“模型”。阿克顿这种力求融信仰与真理于一体的做法,曾被韦伯称为能使个人成为神意之“容器”的“理性化伦理行为”,或可视为他解读历史的“模型”。
按傅勒所言,对于法国革命这场能勾起人们复杂感情的大事件,只有精湛的史学技艺是不够的。面对这场革命,一个人必须表明自己的观点,他的研究免不了某种立场。这对于研究墨洛温王朝的人也许不那么突出,但对于1789年或1793年却不可或缺。因此,不管法国大革命的研究者自觉与否,他都会变成保王党、自由派或雅各宾主义者,此乃使其历史叙事获得正当性的通行证。
如果从这个角度为阿克顿笔下的法国革命史定位,则他不但是个推崇古典自由的保守派,而且是个联邦主义者(这鲜明地表现为他在美国内战期间为南方所做的辩护上)。他判断法国革命之得失的一个重要坐标,便是先于法国大革命而发生的美国联邦主义立国原则。因此,讲稿的第一讲交代了作为革命先声的启蒙运动和柏克对它的批判之后,接下来便分析美国革命对法国的影响。
在阿克顿看来,法国人的问题是,他们尽管受到美国革命的深刻影响,对美国的立宪过程却浑然不觉。以他之见,如果笼而统之地讨论美国革命,会把一些互相抵触的不同因素混为一谈。美国革命至少可分为两阶段。从1761年开始与宗主国的激辩,经过《独立宣言》的发表,直到1782年战争结束,美国人确实态度激烈,喜欢谈论抽象原则和极具批判性的普适理论,正是这些初期的东西引起了法国人的关注,并由拉法耶特、诺埃利斯、拉梅特这些后来成为革命领袖的人传播到法国。然而,他们所体验到的美国,仅仅是杰弗逊和《人权宣言》思想大行其道的美国,而不是1787年以后进入了制宪过程的美国。
其间有十来年的光景。也就是说,从独立战争爆发到着手立宪,要比法国大革命持续的时间还长,这足以使美国的政客们激情减退,坐下来耐心权衡利弊了。他们虽然依然保留着反抗暴政的理想,更多的功夫却用在了设计种种方案以防备不受约束的民主制度上。用阿克顿的话说,参加费城制宪会议的,都是审慎机敏之士,他们不喜欢走极端,他们“最令人难忘的成果,都是不彻底的办法和互相妥协的产物”。这些做法皆出于为美国人所有而为法国人所无的一种清醒认识:民主政体不仅有可能“虚弱无力和缺少智慧”,而且有可能专横无道。因此美国人选择了联邦制,只授予中央政府若干明确列举的权力,而由各州保留其他一切权力。十分推崇罗马帝制时代的阿克顿说,就像罗马人知道如何用权力分散让皇帝变得无害一样,美国用“地方主义”驯化了民主。
在法国革命之初,诚然有不少法国人相信,联邦制是唯一能够保障自由的制度,但这种设想却没人听得进去,很快便被国民公会抛到了一边。不过,阿克顿并没有为此而苛责于法国人。他说,美国的宪法成效如何,只是后来才逐渐显现出来的,当时包括美国人自己在内的整个世界,尚未切实看到它的优越。美国人不断解释宪法的意图和内涵,提出修正案,再辅之以法官的各种意见书和公众辩论,才使得“美国宪法成为比最初的印刷文本更为厚重的东西”,其中那些最值得珍视的规定,都是以这种零打碎敲的方式发展出来。当法国人迫切需要其他国家的经验指导时,这些发展的意义还根本看不出来。阿克顿这一番解释,其实同样可以从反面适用于法国1789年《人权宣言》的缺失:它也罗列了一些有关生命、平等、自由、财产权的基本信条,但其“意图和内涵”此后并未得的司法实践或修正案的不断解释和充实,使之成为政治生活的有机成分,而是一直只作为空洞口号而存在。诚如今日法学家所言,宪法若缺了司法适用的不断滋养,则宪法便成了一纸空文。
英国是另一个可供法国借鉴的国家,它依靠的是人们尚不熟悉的信念:“神学之争不会分散国家的力量,政见不同正是其繁荣昌盛的奥秘所在。”可是,对“七年战争”(1756-1763)之耻依然耿耿于怀的法国,却不屑于以英为师,于是他们便只能自己去开创未来了。在从事这项事业时,他们不明白“一种势力应受另一势力制衡”的道理;在政治这个古老而昏暗的世界里,他们夜半临池而不自知,希望只用一盏路灯就能照亮整座城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