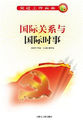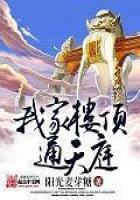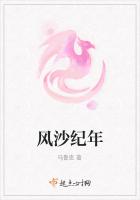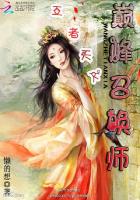可见,自由精神的原理就在于,它足以保障民族的活力,维护民族文化的创造力。这种对于“自由”的理解,是所谓“内在”的自由,或者“形式上”的自由(innerormetaphysicalfreedom)。张君劢深受德国哲学的影响,而以精神、理性之自主的方式来理解“自由”,乃是黑格尔等德国哲学家所长。这种对于自由的阐释,也正与中国人历来对于自由的追求暗合。正如精神自由是一个民族生存的基本条件,保持思想上的自由,也是保障社会正常发展的基本条件。张东荪说,“自由主义不是一种主义,乃是保障一切主义的条件。”也就是说,各种主义的表达和提倡,必须具备一个自由的前提,张东荪是这样解释“思想自由”的:
因此我们可以说就思想本身来讲本来没有自由与不自由的问题。这个问题乃是起于思想的外部。就是思想而受外来力量的干涉,于是乃有不自由。有不自由,然后才争自由。所以思想自由不是一个关于思想本身内容的问题,乃是一个思想在社会上的关系的问题。
张东荪要讨论的是思想如何可能自由表达,而不受外力的压迫,因此便成为了一个政治问题。张君劢也认为思想自由和民主政治是相生相伴的,只有民主政治才能保证思想自由,“思想自由是保障一切主义的条件,而实现思想自由的政治必是民主政治。所以思想自由与民主政治乃是立国的常轨”,“一切主义由思想自由孳乳出来,一切政党由民主政治孳乳出来。但所孳乳出来的任何主义却决不可把这个保障一切主义的条件打碎,同时所孳乳出来的一切政党也决不可转回身来把这个保障一切政党的常轨拆毁。”国民党以党治国,自然是反对民主政治的,如此也就无法保障思想自由。
对于思想的外在限制,可以来自许多因素,比如政治的、宗教的以及经济的,张东荪把近代以来西方文明的成就,都归功于思想上争自由的运动。他认为思想先是与宗教争自由,进而对于政治上的种种独裁专制而争自由,现在则是第三个阶段,即对于经济而争自由了。自由经过种种的斗争,终于造就了今天西方的文明,无疑是把“自由”理解为一种创造社会进步的“能力”了。在这一点上,中国的不同派别的知识分子是相通的,胡适也大为赞赏“自由”之于一国文明的创造力,“因为这种人格(个人主义)是社会进步的最大动力。欧洲十八世纪的个人主义造出了无数爱自由过于面包,爱真理过于生命的特立独行之士,方才有今日的文明世界”,他进而认为,“一个新社会、新国家,总是一些爱自由爱真理的人造成的,而不是一班奴才造成的。”在胡适为自由主义划定的谱系中,都是类似易卜生等“特立独行”之士,而在张东荪等人笔下,也屡屡提及布鲁诺、斯宾诺莎等人,无疑都是一些敢于坚持真理、不屈服于权威的人物。“自由”首先是一种人格理想和精神力量,自由的个体在理智上体现为对于真理的把握,并敢于坚持真理,从而表现为思想上的自主;在道德上自由的个人不会屈从于强势的压迫,体现出独立自尊的气质。个体似乎往往站在政府以及各种社会组织的对立面,而这些个体的存在才是一个社会进步的动力。这种对于“自由”的理解确实带有张佛泉所检讨的绝对“个人主义”的味道。
(三)“自由”:理性力量与道德精神。就理智上之自由而言,就是要求以个体的理性来考察一切事物,摆脱迷信和盲从,不随意附和别人的意见,并且进而克制情感的因素,以免为情绪所役使。当时,知识分子大都标榜以“理性”(或理智)的态度来观察和分析问题,张君劢常常强调,“我之立场,谓之理性主义可也。”此种“理智”也就是对于社会问题,有自己的见解和看法,保持思想上的“自主权”。但是以张君劢的观察,由于30年代中西方思想的交融激荡,各种社会思潮和政治解决方案的层出不穷,使得思想界一片混乱,在此背景下,时人又大多盲目地追随国外思潮学说的新动向,而不假思索地大力宣传,如此就失去了思想上的“自主权”。张君劢说:
须知甲国人之思想,决不能离开自己国内的地理、历史、风俗、人情。甲国无论如何的追随外人之后,决不能离开本国的面目。……唯有自己能思想,乃能有自己的发明,自己的途径;……既已号为独立的民族,而思想上决不自求独立,是有独立之名,而无独立之实。我的意思,不是说完全不要学人家,贵乎以人家的好处,来作参考,来消化他,然后自出心裁,而有一种合乎国家社会的主张,此我所谓思想自主的意义。
一般由于迷信和知识的缺乏,往往会引发思想上的盲从,失去自主思考的能力。而在近代以来,由于西方文明的冲击,中国的读书人大都对西方的学说持迷信的心理,认为西方的就是先进的,越“新”就越“好”,于是对于西方最新的理论与思想,唯恐介绍之不力,引进之不及。1930年代,各种改造社会的方案——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的、民主的、独裁的——更呈“繁花迷眼”之势,但国人往往不假思索,不考虑西方思想的与境性(context)就大力宣传,在思想上失去自主的地位。
胡适也强调自己的理性主义的立场。他反对情绪化的冲动,尤其是民族主义的情绪,容易演化成盲目排外的力量,从而影响了对于国家社会问题的理性思考。热河事变之后,面对着华北的危机,胡适却反对“抗战”,“我自己的理智的训练不许我主张作战”,“我情愿亡国,决不愿学着这种壮语主张作战。”“理智的训练”自然是指胡适所接受的现代科学知识和处理问题的方法。在胡适看来,国内狂热的作战情绪,将会对如何解决外交问题起到负面作用。“九一八”事变之后,蒋廷黻也要求通过外交渠道,依靠国联来解决问题,他对“全国学生一致要求抗日”表示沮丧,“我当时觉得我是在对战争的狂热者从事一场艰苦的作战。”在当时举国要求“抗日”的呼声中,《独立》群体的理智主张自然成为抨击的对象,可见要坚持思想上的自由,也是一件需要付出相当勇气的事情。
思想之自由还可以成为一种道德力量,即因为掌握了真理,而敢于同任何权威和正统的压迫相抗衡,比如中国古代不合作的思想“异端”,西方中世纪晚期受到宗教迫害的科学家等等。1930年代知识分子们也普遍标榜一种“独立”的姿态,一种敢于发表己见,并且对政府进行批判的立场。胡适在《独立评论》创刊词中就指出,他们希望能保持一种“独立精神”,“我们都不期望有完全一致的主张,只期望个人都根据自己的知识,用公平的态度,来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根据自己的知识”自然是要求按照每个人的“理智训练”来思考中国的问题,而“公平的态度”是要求祛除偏狭的私见。关键在于“独立精神”的保持,“独立”自然首先是观点的“独立”,而更主要的还是不受政治势力的操纵,保持对政府的批判立场。《独立评论》一度与《大公报》被誉为北方“舆论”之所在,其中原因正在于此。然而在一些知识分子看来,《独立评论》和《大公报》却是名不副实,渐渐已经沦为政府的“传声筒”。《再生》的张君劢指出:
有人说中国舆论的中心在天津的《大公报》与北平的《独立评论》。……我们以为这两个或一个,根本就不能算是舆论。说坏点,是应声虫或留声机;说好点,是诚惶诚恐,替政府痛苦流涕而已。……若只是诚惶诚恐为政府痛哭流涕,则不但不能算是舆论,且也十分卑劣。若站在留声机的立场上而痛哭流涕,那更是卑劣中之卑劣。
这段批评可谓严厉,直指《独立》与《大公报》和政府的“合作”态度。当时,“舆论”的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就看,其是否站在政府立场、为政府说话,“独立不独立”就是指与政府“合作不合作”。1930年代的《独立评论》和《大公报》诚然有为政府说话的倾向,他们陈述政府在“国难”之际的困境,要求民众支持国民政府共赴“国难”。“为政府痛哭流涕”大概是指对于政府在“国难”时期的种种困境和失败,要求知识分子和民众给予体谅。只是这种做法,难免让思想界产生反感,认为它们一味为政府辩护,与政府同流合污,而缺乏建设性的意见与批判的精神。即使在《独立》内部成员中也因为其公开观点缺乏批评精神,而产生了分歧。1933年6月,胡适在出国之前与汪精卫会面,他表示华北的停战和上海协定一样,都证明中国政治家还有一点政治的勇气。对于这一时期胡适支持政府的公开言论,傅斯年认为太过“和平”,十分生气,甚至要求脱离《独立评论》。胡适于是与傅斯年会面,以消除误会,胡一面指出,“凡出于公心的主张,朋友应相容忍,相谅解”,一面鼓励傅多写一些批评的文章,“《独立》诚有太和平之处,你们何不多说不和平的话,使《独立》稍稍减轻其太和平的色彩”。可见,胡适也意识到《独立》论调缺乏对政府的批判。就其在思想界内的影响来说,《独立》确实被认为有时政府的“立场”太过明确了,这个“社会上一般的感觉”可以其他知识分子的言论来应证:
这些刊物中,在读者心中比较有些印象的,则有南京的《时代公论》和北平的《独立评论》。但就这两个刊物,也正如其他刊物一样,只是站在一种立场(个人的或集团的),就每一碎片每一部分,作一种批判。如说自己能先拿出一个具体方案,通盘的筹划还仅见之于《再生》。
储安平的看法,自然是认为《独立》和《时代》过于站在某个立场来发表意见,未能对于社会改造有通盘的考虑,言语之间虽然比较温和,却颇能代表思想界一批人的意见。实际上,《独立评论》的影响力很大,在当时的一些知识分子心目中,胡适在30年代支持政府的意图太过明显。而《再生》屡屡遭到国民党的为难,先不论它是否真的能保持批判政府的独立地位,但至少容易博得思想界的广泛同情。张君劢就多次标榜要“说自己的话”,在批评《独立》和《大公报》是政府的留声机的同时,也不忘把自己塑造为真正具有自由精神的典型:
国内目前的刊物真如汗牛充栋那样多了。可惜除了营业的关系以外,几乎是其中言论都有背景。他们被实际的势力在暗中决定着、支配着。貌看上去,好像是言出由衷。而深按下去,便见其字里行间透漏出一种类似无线电的味儿来。无线电虽在那里广播,却不是自己说话,乃另有个人在背后开口。我们以为必须先有内心的自由,方可再求发表的自由。言论的可贵即在其本身,不是替人家作机器。所以我们现在也只想说我们的话。心中有话,如鲠在喉,不能不吐。所以不能不吐乃是理性所示,良心所责。不必预计以后究与那一面有利或有害。因此我们不能仅在一二标语之下打回旋。我们要的是自主的自由。
批评国内刊物普遍受人操纵,失去了独立自主的地位的同时,张君劢肯定了《再生》才能代表“自主的自由”。可见,当时“自由”在知识分子的眼中意味着一种独立的姿态,并且敢于在强势压迫下依然坚持己见的道德勇气。“自由”与道德的这种密切关系,确实是中国自由主义的特点。从《再生》对《独立评论》的一再抨击,以及它标榜自己才可以代表真正的舆论这件事上,思想自由与政治的关系更可见一斑。
(四)“容忍”与“自由”。胡适把“自由”同“容忍”相联系,当然他明确提出“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看法,是在1959年发表于《自由中国》的《容忍与自由》一文中,不过他的基本想法早已形成。他对国民党“党治”的不满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在于,国民党的一系列政策体现了“不容忍”态度,“苏俄输入的铁纪律含有绝大‘不容忍’(Intoleration)的态度,不容许异己的思想,这种态度是和我们在五四前后提倡的自由主义很相反的。”他说1927年的“清党”可以说是对于这种“不容异己”专制制度的反抗,但是长期形成的“不容忍”的习惯仍然起作用,因此法西斯蒂的不容异己的行为又得以蔚然成风。胡适多次强调要把新文化运动和国民党的国民革命运动的意义相区别,其关键也正在这里:新文化运动代表了中国自由主义的开拓时代,而国民党代表的是“不容异己”的党纪律。在胡适的观念中,“自由”在一定程度上就意味着对于各种不同思想和政见的宽容态度。胡适一生呼吁宽容的自由理想,他在学术与生活中也是这样做的。胡适虽然长期在学术界地位显赫,但是他往往能够注意宽容对待与其学术观点迥然对立的“异己”。
张东荪也认为一个正常的社会必然是可以容纳各种不同思想的社会,只允许一种思想的独尊,这个社会就失去了进步的动力。他是以社会的“异质性”来阐释思想自由的意义的:
我们必须承认社会是一个“异质的结合”(Heterogeneouswhole)。在此种结合中,各分子有共同的地方,复各有异的地方。即有共同的利害亦有个别的利害,既然在一个社会中利害不能完全一致,则其中的思想自然亦不一致。因为思想无论如何公正,总不能免去为利害所牵制的影响。因此我们必须承认任何思想都包含有偏见,而偏见则根据于利害而起。我们在这个前提之下断不能主张只许一种思想来彻底实现。因为一种思想而绝对不稍加以折扣,使之实现,便无疑于完全打倒其相反的其他思想。须知仅是思想尚不要紧,而思想是代表利害的,则一种利害完全贯彻了,势必把相反的或相异的其他利害完全埋没了。这样便把社会使其不复成为异质的结合,乃变为“同质的结合”(Homogeneouswhole)。
“异质的结合”才是社会的本质,若是强把一个社会变为“同质的结合”,那么就违反了人类的本性,这样的社会必定是不健全的。在张东荪看来,每一种思想背后都代表了一定的利益,如果使某一种思想独尊,那么就必然会排除其他思想表达的机会。张东荪深受康德“道德自律”思想的影响,同时他对社会“异质性”和思想多元化的主张也主要来自密尔的理论。因此他主张社会不能由一种思想垄断:一种“异端”思想无论如何有害,只要它局限于表达的领域,那么就对社会有益;而一种思想无论如何有益,一旦它处于垄断地位,那么必然会压抑社会的“异质性”本质,而对人类造成严重的危害。张东荪在讨论“宪政”成立的前提时,专门指出了容忍与调和各种思想的重要性:
须知宪政的真诺就在于调剂各种不同的思想……所以宪政不在于法律条文,而在于干政治的人们的态度。这个人若是抱了我是替天行道的意见,则决不会承认他的“道”以外,还有别的“道”存在,于是唯我独尊起来,便不能不与宪政相抵触。因此我以为国民党内有了宪政运动,虽不能不算一种觉悟,然而我们却又不能不希望其更进一步,而彻底了解宪政的真义不在宪法而在是否能容忍与能调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