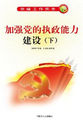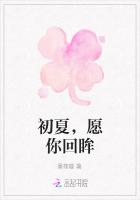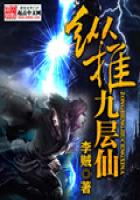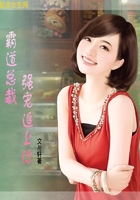容忍各种思想的存在为宪政的真谛,而国民党的“党治”以替天行道的心理,而排斥其他思想的存在,是一种“不容忍”了。这里与胡适将自由与容忍相联系的做法,实是异曲同工。可见,讨论“容忍”与“自由”的时代含义,也就是要求国民党政府能“容忍”,无非是向国民党要求言论自由与开放党禁,要求给知识分子和民众更多的表达政见和思想的机会。以西方思想和学说包装的“自由主义”宣传的背后,其实是中国式的问题意识和表达方式,如同臣子们向皇帝进谏,痛言严法苛政的弊端。此种由寻求“自由”到提倡“容忍”的进路,与西方自由主义的发展,体现出截然不同之处。
由以上思想界关于“自由”问题的讨论可以看出,实际上不论是《独立》的胡适,还是《再生》的张君劢、张东荪,都倾向于把自由理解为一种“精神”,从而强调思想的自由(或“内在自由”),进而在实践中形成一种自主的、独立的“个人主义”的人格理想。这是中国式“自由主义”的特点。正如张佛泉指出的,中国人更多把“自由”与个人主义相联系,对于西方“自由主义”理论中如何共营社会的方面则阐发较少。
四、关于“宪政”的思想论争
1“宪政能救中国?”
“国难”会议前后,国民党许诺召开“国民代表大会”。这使得要求实现“宪政”的呼声很快成为了思想界的主流力量。这个曾经在孙中山的《建国大纲》中被赋予国家最高权力的机构,也承载着知识分子对于国家命运和前途的期盼。借此国民党寻求国家团结以“共赴国难”的机会,知识分子普遍希望能够早日实现“宪政”,以便中国政治能走上正轨。“宪政救国”的口号,一时间流行开来。其中,胡适和王造时都持非常明确的“宪政救国论”,这遭到了梁漱溟和《国闻周报》马季廉的质疑。马季廉就撰文《宪政能救中国?》,提出批评。而《时代公论》群体则更持一种“法律历史主义”的主张,否认中国现在可以实现“宪政”。
王造时主张“宪政”的论据最为明确。他首先指出国民党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目前已经到了政治改变的关键时期,而改革政治的途径无非是“革命”或者“改良”。而国民党的“寡头政体”的维持全凭武力,因此其崩溃最容易走上以“武力”为基础的“革命”之途。然而中国之残破的现状已无法承受革命的破坏力,“政治上,若有别的的办法改善,我是不赞成武力革命的。在日本蹂躏之下,我们再来演斗蟋蟀的故事,我认为只是野蛮!这是无耻!”因此,他要求国民党以国家命运为重,而宣誓“改良”,也就是实行“宪政”奠定现代政治的正轨:
政治好比秋戏,宪法好比规则,宪政好比有规则的秋戏。若比赛足球而没有规则,或有规则而不遵守,那么结果只有踢得头破血流。政治势力的争斗,若没有根本大法,或有宪法而大家不行,结果也只有打得落花流水。
所以,王造时认为,“宪政不但可以避免革命与内乱,并是(且)我们要知道,还是立国的根本大计。”胡适也是力主实现“宪政”的,他同意“宪政”是造成政治正轨的唯一途径。当时,一些知识分子对于“宪政”能否在中国实现,颇存有一些疑问。比如《时代公论》的何浩若就觉得“宪政”应该是资产阶级的专利,不一定适应于中国,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资本主义;《国闻周报》的马季廉认为中国当前的急务是如何解决“民生”问题,“宪政”可谓药不对症,并质疑“宪政可以救中国”的论调。胡适针对所有这些对于宪政的质疑,给予了一个总的回答:
第一,我们要明白宪政和议会政治都只是政治制度的一种方式,不是资本主义所能专有……
第二,议会政治与宪政不是反对“民生”的东西……
第三,我们不信“宪政能救中国”,但我们深信宪政是引中国政治上轨道的一个较好的办法。
以“宪政是引中国政治上轨道的一个较好的办法”,与王造时宪政是“立国的大计”的看法正可以互相映照。以胡适的看法,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与宪政并不矛盾,则宪政显然成为了其他一切政体和政策(包括民主的或是独裁的)得以实现的基本条件,是现代政治的基本“游戏规则”了。但是与王造时坚持民主的立场所不同的是,胡适并不排除在遵循基本的“规则”的前提下,采取“独裁”政体或是“社会主义”的政策。王造时说:
根据宪法而行的政治,便叫做宪政……那么实行宪政,必须先有宪法;有了宪法,还需实际施行。没有宪法固不成其为宪政。只有宪法而不实行,也不成其为宪政。
可见,“宪政”就是由“宪法”来统治国家的政治,这便是“法治”而非“人治”。然而进一步看,宪政即按照“宪法”治理国家,这自然还是Rulebylaw,而非Ruleoflaw。胡适急切地呼吁要求赶快制定一部宪法,然后才可以使得人民提高自己的参政能力。他反对由国民党来“训政”,他指出“宪政是宪政最好的训练”,要想使得民众掌握四权,就必须让他们自己来实践,其中的道理带有很浓厚的实验主义的味道。胡适还更进一步明确了他的意图,他认为制定宪法和建立国会制度,足以团结全国的民心。在长沙的一次演讲中,他认为应该“努力建设一些可以维系全国人心的制度:如国会制度,如考试制度”,而在讨论如何实现中国的“政治统一”的时候,他也指出要“用政治制度来逐渐养成全国的向心力”,而“国会制度”即是这种可以造成“向心力”的政治制度。
近代以来西方的思想以席卷之势,将中国的旧学冲击得七零八落,因而国人容易把西方的制度、文化、思想加以美化,给予其“名”的美誉,而缺乏对其“实”的考究,认为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因此中国也必然可以效仿。“宪政”就是这种好的政治名号,故而可以造成“全国之向心力”。
胡适和王造时对于宪政的看法,都不程度地陷入了“立法主义”的怪圈。胡适的意图更明确,而王造时把“宪政”最终归结为依照“宪法”的统治,可是宪法如何切实执行,却未有深论。王造时自信地认为“宪政”可以避免武力政治,然而中国民初的种种现实却是武力的存在一再破坏宪法,因此驱除武力恐怕是宪政成立的条件,而不是宪政的结果。张东荪的看法是,“宪政”的障碍恰恰在于“国内有特殊势力,这个势力是不愿把自己置在法律轨道内的”,他所指的“特殊势力”,即“军阀与官吏”。执掌政权的是一些凭借武力获得政治资本的军人,则又如何能够指望他们放弃既得利益,而自觉地在法律范围内行“宪政”之实,而不是名义上宣布“宪政”,实际却依旧以“专制”行事呢?
孙中山的政治设计中也屡屡提到宪政实现的条件,比如统一全国行政、军队,地方实现自治,国家有完备的文官制度等等,这些自然是宪政的必要条件,却不是充要条件。制度上的建立,是可以通过胡适所说的“实验”、“试错”的方式解决的,然而每一种制度背后都有其成立的与境性(context),若是剔除了对于“与境性”的考察,那么只能是在概念(“名”)和价值的领域打转,而无法深入到其历史的情景中。任何一种西方的因素(无论制度的、思想的),都有这个问题在内。“宪政”自然也不能例外,正如英美法学家经常引用的一句名言,“宪法是历史地长成的”,也就是宪法为一种历史传统的产物。民国时人,包括胡适和王造时,都有把宪法仅仅理解为表现为条文的“实在法”的倾向,而对宪法来自于传统、来自于习惯法的认识却大为不足。在这方面,张东荪和梁漱溟的见解,显然更接近历史主义法学家。张东荪说,“民主就是一种生活”,则这种生活的方式自然与其文化传统和习惯密不可分。显然“宪政”背后还有其特殊的“与境性”,故而“宪政”也不是按照宪法统治就可以实现的,而它的正常实现还必须具备人们认可这套“游戏规则”的文化传统和社会习惯。因此,张东荪说“宪政”不是制定一部宪法,并要求大家按照宪法行事,就可以达成的,原因亦在于此。
梁漱溟对于胡适的“宪政论”进行了批评,他以自己在中西文化比较中所得的种种启示,看到了宪政背后的文化因素,认为“中国此刻尚不到有宪法成功的时候”。梁漱溟认为此刻中国的“宪政要求”乃是“从外面潮流所开出来的,而非从固有历史演出”。在他看来一种政治结构只是其社会结构的一个层面,因此必须决定于其社会结构的基本状况。那么西方的“宪政”自有其社会结构作为它维系的基础,而中国的社会结构毕竟与西方不同,“他(中国)政治的构造松散无力,人民仿佛只有社会生活,而没有国家生活。社会秩序存于礼俗,自尔维持,若无假乎上面的法律”,因为根本没有法律的观念,宪法缺乏其存在的社会条件。梁还指出,中国的改造未来必须有一种“新礼俗”,礼俗决定法律,而不是法律决定礼俗,所以他虽然不排除中国未来可以有一部宪法,但现在却不能成功,只因为社会结构未改变,“新礼俗”未造成。这容易让人们联想到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梁对中西文明的基本判断,中国既然是个伦理的社会,而西方是个法律的社会,那么对于中国社会的改造,恐怕总归要从“礼俗”入手了,一味地照搬西方的良法善政,不是根本解决问题之道。梁看到中国社会的基层组织是乡村,故而主张改造从中国社会的细胞入手的“村治论”,其原因也正是为了造成中国的“新礼俗”。
张佛泉认为梁漱溟的看法很有见地,认为法律必须“从固有历史演出”,也是颇得西方“法治”之真谛。他称赞梁的想法“和政治哲学上称为历史学派的(HistoricalSchool)几乎完全是一样”。不过他也指出梁的看法有些“历史宿命论”的嫌疑,因为在中国具备宪政所需要的“新礼俗”之前,所能作的只有等待,而人们主观的改革努力则丝毫对于社会进步没有作用了。实际上,梁漱溟要求努力的方向自然不是“宪政”,而是他倾注心血的“乡村建设运动”。张佛泉对于梁和胡的观点似乎有些调和,但这种修正(主观努力与客观条件的结合)却更近社会改造之真实。
当时《时代公论》群体对于西方“法治”和“宪政”理论的了解更加清楚。他们主张“法律来自于历史”,对于英美“宪政”来源于历史传统有较多的论述。阮毅成指出,“法源由社会生活中的事实规则”,反对将法理解为“主权者的命令”,也不赞同“法是从个人自然法而来”(因为“自然法”完全是超出经验之外的玄想)。法先于国家而存在,因此国家亦受法的制约。而法律来源于社会生活的事实,也就是说来源于历史的进程。萨孟武也认为,“法律是事实的表现,不是理想的结晶。法律不能引导社会进步,只能随着社会进步而进步”,“因此,立法家不但要精通法律原理,还要明瞘社会的实际情形。如果不然,则所制定的法律只是一纸空文,没有实行的可能。”
由以上言论可以看出,《时代》核心成员体现了一种“法律历史主义”的倾向。阮毅成反对法来自自然法,以及法是主权者的命令,也就是不同意法律建构主义和实证主义的观点;而萨孟武要求立法者,不仅要精通法律还要了解社会的变迁,正是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梅思平认为,“宪法是生长出来的”,这本来是英国经验主义对法律的基本看法。然而这一看法却遭到胡适和蒋廷黻的批评,在这一点上,胡适倒更多地倾向于建构主义的理论。田炯锦对宪政和法律的评述也完全持一种历史主义的观点,“凡一个宪法或政体的好坏,我们只能在政治上了轨道,法律完全有效的时候,看其运用上有无扦格,若大家视法律如无物,任意违犯,则任凭什么联邦制分治集权合作,都谈不到。因为这些政体,全靠法律维持其运作。法律苟失效用,则制定政体之宪法,不过反白纸黑字而已。”“政治不上轨道”的历史现实,制约了我们实现宪政,因此不是好的宪法和政体可以决定政治现实,而是现实的社会关系决定了实现什么样的社会制度。
法律决定历史,还是历史决定法律,是当时宪政论争中的一个主要分歧。在论争中,胡适等人确实有将西方宪政“乌托邦化”的倾向,制度的确立可以通过人的主观努力而实现;而《时代》群体更多关注的是在认识现状之后进行政治改造的途径。
2宪政实现的途径
1932年4月“国难”会议召开的前后,也正是“宪政”呼声最高的时候。“国难”会议主要解决两个问题,其一,是确立对外的外交方针;其二,对内则是响应民意,国民党许诺马上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并就国民代表大会的组织、权限、选举办法进行了讨论。这在知识分子中间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比如胡适等人乐观地希望借此机会,把国民代表大会改造成类似于国会的机关。因此国民代表大会究竟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机构,是拥有真正实权的立法机关呢?还是一个咨询性的机构?思想界对此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显然,“国民代表会”的意义更多在引起知识界政治“参与”的热情。正如《时代》的杭立武指出的,“代表会之意义不在代表会之本身,而在其所表示。一在国民方面,其要求召开代表会,乃对政府不满之表示也”,“一在政府方面,其允诺召开代表会,乃对国民不满之情,表示一部分之容纳也”。因此杭立武并不觉得一个国民代表会的召开就真的有助于“宪政”的实现,实际上他认为民意机关的设立不过是知识分子的要求,中国的民众却对此没有多大兴趣。“夫要求召开国民代表大会之国民,其呼声不过代表一部分之智识分子;至于不明政治不愿过问政治之大多数民众,其所责于政府者;固不在召开国民大会。”但是,借此国民党“礼贤下士”的表示,思想界对于如何实现宪政的思考则渐渐热烈了。
(一)《时代》:由“党治”到“民治”的制度安排。虽然胡适等人对于宪政呼吁最力,但实现宪政的具体办法,即如何从制度安排上处理好由“党治”到“民治”的过渡,却少有论及。在这方面,《时代公论》群体的意见很值得探讨,不仅因为他们在“宪政”问题上所持的“唯实主义”的立场,更因为他们实现“宪政”的意见,在“国难”会议“杨端六提案”中有切实的反映。
前文已经提到,以杨公达的意思,中国根本未能实行过“党治”,但是“党治”的名声已坏,因此他觉得当时(“国难”会议召开之时)的急务是调和“党治”和“民治”,为通向民主政治创造条件。对国民代表大会性质的讨论中,《时代》的几个核心人物的意见比较一致,都是认为应该将国民代表大会改造成“党治”与“民治”的调和力量,渐渐地减退“党治”的色彩,使其成为一个真正的议会组织,而不是马上就实现“宪政”。梅思平原来是签署了“杨端六提案”的,他的意思基本上对此提案表示赞同;此外经过“国难”会议的几番争论,最终就“杨端六提案”的可行性,国民党党内与由一些宪法、政治学专家组成的审查委员会基本达成了一致,因此最终决定国民代表大会的组织办法和职权范围,按照“杨端六提案”的办法执行。这样,这个试图调和“党治”和“民治”的议案最终得以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