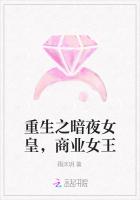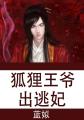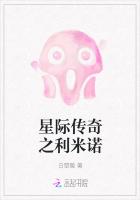——1930年代的世界政制趋势与中国背景
以往史学界对1930年代“民主”与“独裁”政制的论争,研究是比较多的。①然而,相关论著大都着眼于论争本身,关注于论战中各方的立场,未能深入其历史背景,且多有“后见之明”,缺乏“同情之了解”。关于中国应该实现什么样的政制的论争几乎持续了整个30年代,这次民主与独裁的争论决不是孤立的。为了更好地理解这场论争,必须考察30年代思想界对于中国政治制度的全面思考。②即使是就独裁与民主问题本身的讨论,史学界目前的研究也颇有盲点。③
本文关注的是论争产生的时代环境和思想背景。本文分五个部分展开:“独裁”与“民主”之争是在30年代特殊的世界背景下展开的,当时“资本制度”遭遇了空前的危机,本文先从“资本制度”的危机谈起;这一危机造成了世界范围内“统制主义”政制思潮的盛行,也深深影响着中国“思想界”④的动向,这是本文第二部分关心的问题。文章第三部分,将讨论民主制度所遭遇的困境,这对于思想界理解西方的民主制度提供了新的契机。第四部分,将关注思想界对于中国政治出路问题的思考,这是促成民主独裁论争背后的问题意识所在。最后,我将回到民主与独裁论争事件,检讨学界以往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一、资本制度的危机
1929年爆发的经济危机波及到了世界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场空前的灾难。大量的人口失业,资本主义盲目地生产,而同时劳动者的购买力却直线下降,生产的东西买不出去,只好销毁以平衡供需关系,从而造成了极大的社会物产的浪费。马克思对于剩余价值和经济危机的论述,似乎一夜之间得到了验证: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不是绝对过剩,而是相对过剩,只是相对于消费者的购买能力是“过剩”了。这使得人们对于“价格体系”失去了信心,当时在美国非常流行的“技术统治”(Technocracy)的倡导者就要求废除“价格体系”,以“能力”(Energy,即若干年内单位机器效能提高比率)计算的复杂手段替代通过价格制度来获取消费品的市场体系。⑤这自然是针对资本制度的社会危机。机器生产的效率越高,劳动者失业率就越来越高,机器生产的进步带来的却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当时资本制度的弊端,一个显而易见的方面就是它只关注于生产,而不顾消费的利益,这使得人们距离资本主义曾经许诺的幸福美好生活越来越遥远了。⑥
资本主义认为供需的关系应该由市场行为来进行调节。19世纪“自由放任”的资本制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也使得市场可以自由调节生产,政府行为不应干涉经济活动成为了人们的信条。亚当·斯密、斯宾塞等自由主义的理论大师们不止一次地提醒过“自由市场”的原理。然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随着世界范围内经济危机的蔓延,“自由放任”的资本制度已经在人们的心目中彻底破产了。甚至,人们认为“自由放任”、缺乏计划就是“资本制度”的本质。博兰尼曾经指出,19世纪的资本主义建立在四个制度性支柱的基础之上:霸权均衡制度、国际金本位制度、自律性市场制度和自由主义的国家制度。⑦其中自由市场制度是整个资本主义的基础之基础。自由市场制度的破产也意味着19世纪以来资本制度的基础已经根本动摇:30年代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英美陷入危机,自顾不暇,而德意等国则转向法西斯主义,尤其是德国对于一战所形成的帝国主义格局冲击最力,世界逐渐分裂为两个阵营⑧,霸权均衡制度被打破;各国为了摆脱危机纷纷宣布放弃“金本位”制度,尤其是美国的政策转向对于世界范围内经济结构的变动影响最大,国际金本位制度遭破坏;最后由于将政府力量不断介入经济领域,各国在政治体制上也不得不趋于放弃民主制度的一些基本原则,而纷纷寻求政府力量的强化,自由主义的国家制度渐被遗弃。
在资本主义世界为经济危机困扰的时候,苏俄的经济建设却已经初具规模。“一五”计划的提前完成,让世人为之一惊。资本主义世界失业人数一国动辄达数百万,而苏俄却被誉为“世界经济恐慌中一个没有失业的国家。”⑨因此苏俄的经济政策成为医治世界经济恐慌的一剂良药。张君劢指出苏俄的最大贡献就是引起各国对计划经济的重视。至此,自由主义国家也开始寻求经济上的“统制”了。总之,自由资本制度在30年代已经积重难返,而“统制经济”和集团主义的呼声遂成为了世界的新潮流。
二、“统制主义”与中国“思想界”
所谓“统制主义”可以分三个层面来说明。首先,它是指“统制经济”,即计划经济的另一种名称。⑩此为狭义的“统制主义”。自由资本制度的破产,使得人们开始寻求新的社会改造的道路,这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产生了一种对于秩序和有计划的社会制度的向往。而苏俄凭借着经济上的初步成果,引起了思想界的普遍关注。当时的“统制经济”的代表就是苏俄的经济制度。
不过苏俄的制度是否可以普遍适用,思想界是有分歧的。蒋廷黻对统制经济是极力倡导的,显然这与他对苏俄的关注和了解有关。在蒋廷黻的“独裁”主张中,推行计划经济也是一个重要的考虑。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础,就意味着经济上的统一规划和管理。因此,苏俄制度的成果似乎提供了一种信号,即经济上的统制必须通过政治上的集权来完成。钱端升说:
现代民族主义的表现有二,一为国家经济力量的增进,一为军备的注意。……工业化本是近代社会自然的倾向,再加上民族生存的需要,在最近的将来,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势必求于最短期内发展工业,而较发达的则势必求维持他们向有的比较优越的地位。在这种尖锐化的竞争过程之中,凡比较敏捷不浪费的制度将为大家所采纳,而比较迟钝浪费的制度,将为大家所废弃,不论在那一个国家,统制经济迟早将为必由之路,因为不采取统制经济者,其生产必将落后。
可见,因实行统制经济,而必须在政治上“独裁”,这乃是现代民族国家发展的趋势。对于渴望建立现代国家基础的思想界来说,“经济民族主义”的诉求容易让他们认同苏俄体制中“统制经济”的成分,进而认同苏俄的集权体制。
然而,苏俄废除了“私产制度”、推行了“公产制度”,它的“统制经济”的基础是以革命方式改造社会的结果,这为思想界其他人无法接受。虽然自由市场体系的破产已经为思想界的“共识”,但是“私产制度”是否也要一并废除呢?马季廉指出,若不想放弃“私产”,象苏俄那样把资本归于国有,则一切经济统制的手段都难收效果。在他看来“统制经济”就必须建立在“公产制度”之上。而张君劢等人却一再强调,自由资本制度与私产制度是两回事,自由资本制度的失败,并不意味着要废除私产制度。张为首的《再生》群体,要求一种社会的改良,他们以柯尔的“费边社会主义”为蓝本,要求保留私产制度的基础上,对经济和社会实行有计划的管理,并使得产业的利益能为大多数人所共享。正如张君劢指出的,他们希望“加入集合的计划于现制度之中”,而不是根本改变现有的社会制度。
罗斯福新政的初步成功,使思想界看到了社会改造的曙光。美国的改良政策即保留了私产制度,又实现了“统制经济”的基本要求。何廉指出,美国代表了另一种“计划经济”,“苏俄的五年计划只可以说是‘共产主义的计划经济’。此外美国近来亦大倡其计划经济。但美国还不能抛弃资本制度,所以美国的计划经济可以说是‘资本主义的计划经济’。”对于向往英美制度的知识分子来说,“统制经济”因此更具魅力了。
至此,“统制经济”为现实之需要已经基本成为思想界的“共识”。这一世界的“光明出路”也在中国得到了反响。1933年宋子文从欧美归来,即主张统制经济。到庐山会谈的时候,宋氏报告了游历欧美之总结,“党国领袖乃感觉中国本身拿出办法以求自救自存之必要,而实行统制经济,扩充全国经济委员会范围,管理全国经济财政事宜,并统制一切国营事业之议遂以决定。”全国经济委员会于1933年10月就匆匆成立。思想界认为它应该是“统制经济”的核心机构。
“统制主义”的第二层涵义是它代表了一种政制模式。“统制”即以国家政权的力量来干涉经济和社会事务,只是组织政府的方式和干涉的强度各国有所不同。当时意大利、俄国、美国的政制,都属于这一意义下的“统制主义”。以“统制”的方式来应对30年代的危机,成为了世界政制的趋势:
我们承认这个世界上的各国,因为经济情形愈趋愈失其自然,所以几乎都有紧急状态陈于他们自己的面前。他们为了解决自身的困难起见,不得不要求有个强有力的政府。俄国之所以有共产党专政,在我们看来,是和英国之所以有混合内阁一样。意大利之所以有棒喝团专政,亦是正和俄国之所以有共产党专政一样。
世界范围内的“统制主义”对中国的影响,可以从三个方面考察:
首先,如何造就“服从”的民族精神和国家意志的集中。当时,意大利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最早施行了“独裁”,在整个世界都在经历着“资本制度的危机”之时,墨索里尼的上台使得法西斯主义成为领导欧洲革命的先锋。“独裁制”最早是指古罗马在国家遇到危机时所施行的应急制度。墨索里尼所领导的法西斯运动,在思想界看来也是为恢复古罗马政制的这种“崇高的权力和武装的威严”,从而其应付危机的正面意义得到了一致的肯定。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政治陷入奄奄一息的时刻,墨氏所唤起的意大利国民对政治的热情和“服从”的民族精神,无疑是赢得远在中国的有识之士崇拜的重要因素。
在蒋介石精心推动的“新生活运动”中,其效仿的主要对象就是意大利的法西斯运动。推广“新生活运动”的“蓝衣社”是一个试图向法西斯主义学习的组织。他们确实企图掀起一股崇拜领袖的风气,且举动不断趋于激化。在青年国民党员中,法西斯主义的影响是深远的。蒋介石确实曾试图加强对青年的控制以求对国民党的改造,就如同法西斯政党的旗下,其青年组织对党的辅翼那样。国民党在30年代所设立的各种特务和警察机构,也多是从法西斯主义处借鉴的经验。意大利议会实行“职业代表制度”(全国选举以各职业法团为基础,因为他们认为只有职业团体才能真正代表大众,而议会政治的普选代表则空有其名),即所谓的“法团主义”也被思想界认为可以真正调动国民的积极性,以保障国家意志的有效集中。在造就“服从”的民族精神和国家意志的集中上,意大利的“独裁制”确实提供了一些现实的经验。
但是,思想界对法西斯主义是否适应中国并不乐观。正如张佛泉所指出的,“独裁”所需要的基本条件是,具有领导魅力的领袖以及民众狂热的宗教精神,而这些要素中国并不具备。王芸生说,“现在中国也在喊着‘法西斯蒂’了,‘橘逾淮而为枳’,将来还不知变成个什么东西呢!”这正是思想界的主要意见,“独裁”在中国是缺乏主观条件的。而张君劢认为中国的当务之急与德意等国不同,也就是说“独裁”缺乏其客观的需要,“吾国今日之问题,非取消议会而代之以独裁之谓,乃如何削平群雄而划一号令之谓也。故吾国今日之病痛,可谓与欧洲之独裁政局全不相涉。”国民党宣传“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希望民众的拥护和服从,却都不能收效,其原因恐怕也正在于此。
其次,国民党如何强力化,从而以党的力量带动中国政治秩序的稳定。在这方面,思想界大多认为法西斯党政合一的体制,可以作为借鉴的对象。《国闻周报》的邱昌渭,指出意大利形成了一套高度集权的国家组织,它的特点是国家的法律都要首先通过该党最高委员会的通过,因此政党与政府实际上是合为一体的。另外一些人则认为苏俄的体制可以作为改造国民党的参照对象,《时代公论》的杨公达说,“在苏俄,党政在精神上是二位一体,政权是受党权的管辖,一切政策,一经党部决议,便可雷厉风行,好像党权是决议权,政权是执行权,如果政权不奉命而行,则党权又有监督权制裁权。但是党部并不因此滥用其权力,去干涉司法”。总之,俄意的政制模式都是以党权决定政权,当时的思想界认为这是改造中国政治的一条出路。
孙中山也曾强调要求“党在国上”,不过随着国民党的“分共”,从而与苏联分道扬镳,国民党一度失去了“党治”最有力的工具和指导,这使得国民党在30年代初迅速走向了衰退。为了改造国民党,30年代国民党的领袖和思想界一些人,力图恢复国民党在1924年改组时的政党精神,希望重新效仿苏俄政党的模式。蒋介石在公开场合多次表示,希望唤醒“十三年的革命精神”:
中正今日唯一之志愿,乃在复兴中国国民党十三年之革命精神,与其独一无二国民革命之组织和方式,而以实现三民主义自任也。
《时代》的杨公达认为,国民党的“自救”应该从三个方面下手,即力求“党政思想化;党员职业化;党部简单化”。他希望能够恢复“十三年的革命精神”的同时,更在组织上要求国民党党内恢复总理制。这一切都是试图以党内权力和精神的高度集中,而造成强有力的国民党组织。
不过,试图重塑苏俄政党组织模式,以维持“党治”局面,受到了思想界的普遍抨击。在“九一八”之后,思想界的风气是希望通过开放政权来增强国力,共御强敌。在国民党内,孙科俨然以“民主派”自居了,“国难”会议召开期间,他发表了《抗日救国纲领》,系统地阐发了他希望开放政权、结束“党治”的主张,并受到思想界的欢迎。而像《时代》群体那样公开主张强化“党治”的知识分子则显得处境尴尬。迫于民主化的压力,“国难”会议期间,《时代》的态度也不得不倾向于在“党治”和“民治”之间的调和,而不是以党权来决定国家的一切。
其三,罗斯福“新政”的初步成功使得思想界对于“统制主义”有了新的认识。当“统制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之际,大多知识分子是困惑的。他们既承认“统制”的效力,又不愿意提倡苏俄意大利的“独裁”政治。而美国罗斯福的上台为知识分子提供了新的路向。
罗斯福的最大贡献是恢复经济秩序和重视国家利益。人们开始把罗斯福与曾博得中国思想界高度好感的威尔逊相比较。30年代,威尔逊时代所倡导的世界和平、裁减军备和大国均衡体制都已经渐渐被破坏,国际主义和理想主义已经不合时宜。即使当初追随威尔逊的脚步而倡导“世界主义”的胡适,也在30年代不得不承认“国家意识”的抬头将会是世界的趋势。而代表了国家利益和现实主义的罗斯福,也取代了威尔逊成为了思想界纷纷追随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