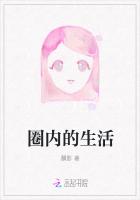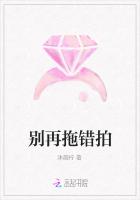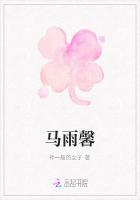以“科学”解决一切问题,表现在政治领域,就形成了提高行政效率必须依靠科学态度、科学家的基本看法。因为科学家具备了一般的科学精神,因此国家的各项事务都最好交与科学家来负责。科学家不但应该作好本职的科学研究,更应该出来参与政治,把治理国家的任务交给科学家,就是主张一种所谓的“技术统治”(Technocracy)。
此思潮进一步发展而为一种“专家政治”的诉求。现代政治就是“知识”的统治。政府各部门只有吸收各个方面的学者、专家,才能保证政府的效率,从而要求把“治权”交给专家。在此背景下,30年代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开始纷纷进入政府,实现“专家政治”的治国理想。这些参与政治的专家,既有像丁文江、翁文灏等自然科学出身的学者,也有胡适、何廉、傅斯年等社会科学出身的学者,《独立评论》周围集合的群体,大多都可以算得上是“专家政治”的实践者了。因此,1930年代知识分子普遍参政的现象,似乎不仅仅是知识分子试图承继传统士大夫“治国平天下”的道德志业,也是现代政治的必然产物,即专家政治所要求的知识与政治的结合、学术社会与政治制度的有效沟通。
提高政治效率固然需要学术专家,此为“人”的因素,但是行政效率的提高,更需要建立一套韦伯所说现代的理性制度——“科层制”,这是“制度”的因素。现代行政之所以有效率,就是以制度来应用人,这在政府组织上体现为“文官制度”,为了能够选择最合适的政务人员,又需要“考铨制度”。许多“独裁”论者,都强调德意等“独裁”国家的基础,建立在现代文官制度之上,因此可以保证领袖意志的畅行无阻。因此,透过当时西方国家在政治形式上民主与独裁的区别,可以发现它们的共同之处是,都具有保证行政效率的文官制度,而这恰恰是中国最为缺乏的。
行政效率的改进包括了两个环节,即政治审核和计算。所谓政治审核,即检查政治成绩;至于政治“计算”,则为了仿效计划经济的模式,对于国家长远发展作出规划。政治的审核基本相当于国家“文官制度”的确立,与官吏考察和选拔有关,而所谓政治计算,则受到当时实行“统制经济”的影响,可以说是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对政治领域提出的新要求。
在中国,行政效率尚未能步入正轨之时,因统制经济需要而增加之种种政府职能(即政治“计算”)又给行政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张佛泉认为中国的政治尚处于未能“得人”的阶段,还不到以制度应用人的时候。故而,目前应以“澄清吏治”为解决行政效率问题之先导,在建立起有效的“文官制度”之前,似不应忙于讲求行政效率。况且西方国家的“文官制度”在30年代也遇到了空前的危机,可见行政效率的改革固然意义重大,但其难度自然也更大。此为时代之一大难题,更为中国政治的一大难题。
为了提高行政效率,国民政府在30年代实行了一些面向现代化的“制度”创新。以地方制度改革为例,则有省府合署办公、县政府中费局设科的种种举措,并设立试验县为县政改革的模范,而中央通过一系列的地方制度改革也加强了对地方政府的控制。萧公权强调了县政建设中的这一趋势:
省府则合署办公,行政有专员督察,县府裁局,设科治事。区设署长,民编保甲。凡此诸端,自成系统。吾人若以政治学中之名词,说明此项制度之改革,则由自治而变为吏治,实不啻离分权而趋于集权。
国家行政效率问题,一开始就与“集中”和“集权”问题紧密联系。
3“能力”与“决断”:现代政治的要求
“民主”与“独裁”的论争中,有一共同的趋势,即认为一种好的政权必定是有能力的。独裁论者大都主张,“独裁”的结果可以造就一国强大的政治能力。而民主论者也纷纷强调民主政府也是有能力的,对于“民主必然造就一个弱的政府”的论调,他们加以极力的反驳。思想界认为政治能力是衡量现代政治的一个重要因素。
张佛泉指出任何一种成功的政制,都需要强大的政治力量,民主政治也不例外。因此,民主政治绝对不是没有力量的,任何一个软弱的政府,一定是这种政制的原则受到了侵害,就好比一个人生了病,无论是专制还是民主政府都可能生病,因此一个国家是否强有力与其是民主制还是独裁制并无必然关系。由此,张佛泉更强调中国政治所需要的是政治力量,而不是在“民主”和“独裁”之间的简单选择。他考察了民初以来中国在政制上存在的根本问题,“一直到现在,我们可以说我们所犯的最大的病,便在怕‘专权’,而结果闹成没有一时一刻不有人在‘滥’权。”结果民元以来,只出现一个又一个弱的政府。他还赞许当时独裁论者敢于要求“权力”,这是他们对现代政治认识的深化。
在对中国传统政治的诊断中,《时代》群体要求只有造成能决断政治的意志,方是医治中国政治的良药。杨公达认为中国的政治就是“灰色政治”、“姑息政治”,无主张、无对策是中国政治的悲惨现状。然而“国难”的现实却需要有人来做决定、有人来负责任。《时代》的创刊正值“国联”调查团到了中国,对于中日关系究竟该如何应对,萨孟武以“战”还是“和”的决断作为《时代》的开场白。他鼓励政治家应该有决断的勇气,对中国政治要有责任心,“政治家对于政治问题,必须完全负责,不但对政治上有名誉的事件,宜负其责,即对于政治上不名誉的事件,亦宜负其责。”养成决断的勇气和负责的态度,就必须将国家的重心置于一个意志力之上。杨公达的意见是要“独赴国难”,“要树立赴国难的中心,找出一个真能负解救国难的首脑,把民族生命存亡的责任放在他的身上。”这个决断的意志权威无疑就是国民党。“独赴国难”最终就是“独裁”以赴“国难”。
是否能塑造强大的政治能力和决断政治的意志,是思想界衡量政治模式的新标准。“独裁”可以造就强大的政权,民主政府是弱的政府,这些论点固然经不起学理的推敲。但是,我们必须考虑到当时思想界对于现代政治的追求,才能给予“同情之了解”。
五、民主与独裁的论战的透视
对于30年代国内外政制的这些动向的展示,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民主与独裁的论争。我无意重复论战中各方的意见,以往的研究已经对此作了细致的考察,只是针对有关研究者的论点提出商榷意见。
许多论者在对此次论争的评价中,认为中国自由主义者缺乏其基本的价值理念,往往容易导向“独裁”政治,并以《独立》群体的蒋廷黻、丁文江等人为例。其他论者由此指出中国缺乏“自由主义”生存的“土壤”。另一些论者把当时的“独裁”主张简单地等同于“保守主义”政治。然而通过前文论述,我们知道30年代的现实是“统制主义”具有积极的正面意义,民主政治则面临着空前的危机,在此条件下人们的选择是不能简单地以能否坚持自由主义的理念为标准的。
当时人们往往把民主作为19世纪西方的制度,而“统制主义”是20世纪的西方政制。无论论者反对还是赞同民主,对于世界的这一趋势都是普遍承认的。对于以学习西方为己任的思想界来说,究竟是从19世纪的西方学起,还是直接以20世纪的西方为摹本呢?从这一点来说,“独裁”不仅不是“保守政治”,恰恰是对民主政治的一种激进的改造。即使拥护民主的张东荪,也认为“独裁”并非“专制”,而是一种新型政治模式。当时人们力图区分“独裁”与“专制”,正是鉴于“独裁”政治的激进和破坏,而非如“专制”之因循与保守。
从胡适“民主幼稚论”中,我们可以看出“独裁”政治对于思想界的意义。无疑胡适的立场是主张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的,“我观察近几十年的世界政治,感觉到民主宪政只是一种幼稚的政治制度,最适宜于训练一个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民主政治的好处在于不甚需要出类拔萃的人才,在于可以逐渐推广政权,有伸缩的余地”。可见,中国必须实行民主制度,并不是因为民主制度有多么难以企及,而是因为民主制度最容易达到。在胡适对于政治形式的理解中,存在着以下三个由低向高逐渐进化的阶段:
中国目前的政治西方19世纪的“自由民主”政治西方20世纪尤其是30年代以来的“独裁”政治。
胡适认为一定时期的人们只能采取与之相应的社会制度,而不能妄想可以一下子跨越时代的鸿沟,必须通过点滴的改良,以取得逐渐的进步。胡适很看中依照中国的现实,而采取相应的策略。他说,中国距离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还很远,则19世纪的自由民主制度仍然应该是中国努力的方向,那么在达到民主制度以前,就试图越过19世纪的西方,而直接采取20世纪西方的“独裁”政治,显然是没学会走路,就试图跑步了。对于“独裁”是时代的趋势,是比“民主”更高级的政治,胡适是承认的。“民主”之所以幼稚,是因为它需要的知识和训练较少,而“独裁”政治需要投入更多的政治知识,对于民众和领袖的要求更高。在中国当前所需要的是通过民主而走上建立国家的正轨,还不到运用国家机器来推行积极的经济、社会政策的阶段。在政治幼稚、政府无能的境遇下,“独裁”和“专制”都成为不合时宜的政治幻想了。胡适的主张“民主”,却实际上把“独裁”的地位抬得更高,毋宁说“独裁”在胡适的政治序列中代表了“未来”,而“民主”是中国努力的方向。
“独裁”政治是一种强力、高效,需要更多知识和智力的政制模式,是思想界的基本看法。实际上,人们普遍把效率、能力与现代政治相联系,从而以能否实行统制经济、能否统一等标准来衡量中国政治。如果我们避免以“思想”代替“历史”、以价值判断代替事实考察的话,正可以洞见那个时代思想界的问题意识所在。
当时思想界的主题是对于“现代政治”的追求,表现了思想界政治知识的“自觉”。这可以从两个方面说明:
其一,就其关心的问题来看,集中在中国政治步入现代轨道的途径是什么。这又分为两个问题,一是现代政治包括哪些要素,二是在中国如何实现现代政治。思想界的看法是,现代政治至少应该是有效率的、有能力的,有一个可以决断政治的意志来保证权力的应用,并且要求行政权在相当范围内驾驭立法权,实行统制经济,而中国的特殊处境更首先要求“统一”。独裁论者主张中国实行“独裁”的理由不外出于以上几个方面。蒋廷黻要求“独裁”的目的在于“武力统一”和实行计划经济。钱端升则认为实行统制经济,必须通过政治上的“独裁”。丁文江则是受到苏俄模式的影响,希望塑造举国一致的信仰,出于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仍然是倾慕苏俄决断的政治能力和强大的国家效率。而吴景超、何廉也认为统制经济和国家秩序的稳定将是中国政治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虽然何廉并不像吴景超那样明确主张“独裁”政治。即使是民主论者,如前文所述,也都倾向于把民主的原则束之高阁,而保障行政权力的有效集中。到了民主与独裁论争的后期,思想界已经开始摆脱“主义”之争,而开始讨论中国政治出路的具体“问题”了,即如何使得中国政治有效率、有能力,如何实行统制经济等。
其二,就其论争的方式来看,当时思想界的论争是一种“事实”之争,而非“价值”之争。这表明思想界政治知识的“自觉”。从清末以来,中国的读书人就不断地把国外的政治理论介绍到中国来。但是应该说,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曾经轰轰烈烈的倡导“德先生”为止,思想界之引入西方学说和理论,都不过是“雾里看花”,尚未能“登堂入室”。时人率以西方学说为救世的良药,而不能深入到它背后的问题意识中去。于是,民主、宪政、自由、人权、开明专制、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曾几何时,都不过成为激励一批又一批志士仁人奋斗的口号,而未能使得国人在理智上和知识上了解种种政治概念背后的事实依据。因此,思想界对西方政治学说大多持“理想主义”的态度,这些“乌托邦”色彩的政治形式又多不能关切到中国的现实问题。于是争论大多成为了“价值”的论争(Disputeofvalue),而非“事实”的论争(Disputeoffact)。
到了1930年代“民主”与“独裁”论争的时候,这种“事实”之争才成为了主题。从思想界论争的方式和争议的具体问题来看,这种“事实”论争的倾向十分明显。比如,大家争论的焦点,已经不在于“民主”还是“独裁”更合乎人类的价值理想,而是“民主”与“独裁”的实现都需要什么样的条件,进而这些条件在中国是否或者可能具备。张佛泉认为“独裁”需要领袖的道德号召力,同时民众要有宗教热情,而这些要素在中国并不具备。他一再申明他并非绝对地反对“独裁”,而是目前中国并不具备“独裁”的条件。胡适也认为中国缺乏“独裁”的基本条件。这些论证的具体问题,在论战中随处可见,都是在追问中国能不能行某种政制,而不是应不应该行某种政制。此乃“实然”的问题,而非“应然”的问题。而在论证过程中,论者大多也习惯于引经据典,以中国和西方的历史为其证据,显然历史已经成为事实,更具有实际的说服力。蒋廷黻和吴景超以西方和中国的历史为其证据,而张熙若对他们的反驳也以事实之困难为准。他说“独裁”所以难达到统一的目的,“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有自由、平等、个人解放,唯理主义,以及其他许多新时代的思想在那里作梗。”以两种政治思想的斗争为阻碍“独裁”制度实现的理由,正是在为民主的合理性寻求“事实上”的依据。
此时的西方也渐渐由一个整体而分裂为多个对象,19世纪的西方、20世纪的西方,意大利、德国、英国、美国、苏俄,每一时代、每一国都有不同的政制模式。思想界开始选择他们自己理想的学习对象,比如在经济上学苏俄的计划经济、学习美国的“新经济政策”,在政党组织上则学习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在行政制度上仿效英国内阁制等等。这显然在根据中国的“事实”,借鉴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经验。
30年代的世界和中国,都在寻求着政治上的出路。这是一个解决“问题”的需要远远大过“主义”的信仰和追求的年代,这是一个危机四伏,而催生出“现实主义”盛行,排斥“理想主义”的时代。在“民主”与“独裁”的论争中,主张“民主”的论者大多喜欢称呼“独裁”论者为“实际主义”者。然而时代的方向也迫使那些曾经对“民主”持有幻想的人们,从“德先生”的理想美梦中觉醒过来,去审视国内外政治的现实与趋向。从一定程度上,思想界讨论问题的标准都被从“天上”引入到了“人间”。这标志着思想界政治知识的自觉。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