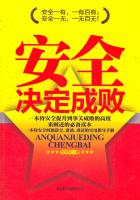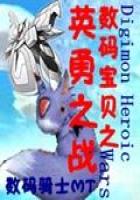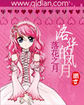——社会改造的两个路向
本章将讨论思想界对于社会改造的基本态度。1920年代末以来的社会史论战,首先就关注于中国社会现状的讨论,从而为社会的改造奠定了理论上的基础。搞清楚中国的现实,才能够决定如何下手。因此1930年代思想界对于社会改造的思考,就成为思想发展逻辑上的必然结果。同时,随着一个新兴政权逐渐开始走上正轨,各种现代化导向的事业发展起来,而社会自主领域的发展与强大也成为必然,于是如何处理政府在社会领域中的地位,如何保障社会的健康发展,这些重要的问题摆在了思想界面前。胡适确实曾经为政府在社会改造中所应该承担的角色而忧虑,在他看来,政府似乎应该为社会的正常规范提供基本的前提——比如统一与安定的政治环境,但是他排斥政府在社会领域的广泛介入。①国民政府30年代为社会改造付出了一些努力,它认识到了农村问题的严重性。在主要的大城市,国民党致力于以政府的机构来控制和主导私人企业,蒋介石、宋子文和孔祥熙都通过自己控制的国家部门来发展实业,这类似于一种“国家资本主义”的政策。思想界显然十分关心都市与乡村的协调发展。
社会改造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解决社会财富在各阶层中的合理分配。对于“平等”的关注是中国一个传统的话题,中国文化中一直都有试图避免社会两极分化的思想因素。而在1930年代随着世界范围经济危机的影响,资本主义所造成的对社会平等的戕害,最容易引起中国知识分子的警觉。当时,世界各国无不采取种种社会救济的政策,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和英国工党上台所采取的社会政策,被中国思想界视为采取“社会主义”的积极姿态。而苏俄凭借“一五”计划的极大成功,也提供了社会改造的另一个有效途径。因此,摆在知识界面前的两条道路,即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就引发了社会改造的一系列论争。
中国各派知识分子都有强烈的“社会主义”倾向。即使是以胡适为首的自由分子群体,也对于社会公道的关注和各种“福利”国家的政策,有着浓厚的兴趣,美国在1930年代的政策转向使得胡适等人看到了实现社会主义的曙光。张君劢的《再生》群体,却一直追随英国“工党”的理论后盾——费边社会主义的步伐,在国家社会党的理论中充斥了来自柯尔、拉斯基等人的思想因素。同时,苏俄作为一个强大的国际势力在1930年代的世界事务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苏俄的社会改造工程也影响着思想界的选择。思想界在社会改造的问题上,可以从西方的各国中吸取不同的营养。1930年代西方已经逐渐分离为众多的路向,那种把西方当作一个整体的思潮已经不复存在②,甚至对于某一国知识分子也开始将其具体分割为不同领域(比如将苏俄分为政治的、经济的),在此基础上思考中国政策的走向。本章就将讨论“思想界”面对西方国家所提供的不同的社会改造道路所持有的态度。
一、20世纪以来的“社会主义”思潮
中国文化中历来就有着对一个理想的“公有”世界的追求。《礼记·礼运》篇里所渲染的“天下为公”的社会景象是历代许多改革家的政治理想。19世纪末,在康有为和谭嗣同等维新人物的笔下,“大同”世界仍然是人类最理想的生存状态。孟子“民本”的思想,也成为中国知识分子警惕社会分化的重要来源。晚清章太炎等人就盛赞民众的道德性,孙中山也把节制社会财富的过度集中作为其“民生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但是,“社会主义”作为一股思潮能够全面影响中国,则主要在西方理论的传入。在西方基督教传教士兴办的报刊中,出现了最早的有关“社会主义”的介绍,而甲午战败后大量留学日本的青年学生,在日本接受了来自西方的各种社会主义的学说,日本成为了中国知识界输入“社会主义”理论的中介,一批日文的宣传社会主义的书籍被译成中文,而在《新民丛报》和《民报》的论战中,也频频引用到这些学说。同时,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动向,也深深影响着中国思想界对社会主义的早期理解,1906年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发生分裂,而以幸德秋水为代表的左翼则宣扬“无政府主义”,他们主张同盟罢工和暗杀来推翻政府,当时革命派的领袖章太炎和刘师培等人深受其影响,这也决定了20世纪初社会主义思潮带有明显的无政府主义的倾向。③
1907年至“五四”运动前,是社会主义思潮发展的另一个重要阶段。无政府主义仍是这一时期的主要力量,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以及巴枯宁、普鲁东等人的著作为其思想来源。早在1905年,李煜瀛在巴黎刊行《新世纪》,以互助论为根据宣传社会革命。1911年,师复等人在广州组织晦明学舍,宣传无政府主义,后组心社为立党之基础,黄涓生、华林、袁振英、欧声白、黄凌霜为社中中心人物,并定无政府主义十二条,刊行《民声报》、《无政府主义同盟罢工伏虎集》。1915年师复死,社员四散,1917年上海、山西、南京、北京各组分社,1920年各社复合组进化社,1920年以后,组织无政府主义同盟。此派主张废除政府与法律,而以人类道德和友爱之本性维系人类的和平。此外江亢虎主张所谓新社会民主主义,组织社会主义宣传会,辛亥上海光复即改组为社会党,并在上海组织成立大会议决党纲、政策,其党30个成员一度成为了国会议员。1922年,江氏发表《新社会主义与新民主主义》,承认军阀官僚势力,同时复兴工商阶级。1924年正式改组为中国新社会民主党,其影响已渐微。④
五四前后,社会主义思潮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其时分为两个流派,一派为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宣传的马克思主义,另一派则是以张东荪、张君劢为首主张的基尔特社会主义。陈、李二人后来主导了《新青年》的转向,使得后期的《新青年》与《向导》一起成为了共产党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但是陈、李二人最初也是民治主义的推崇者,陈独秀曾将法国式的革命视为社会革命的榜样,而李大钊早期也宣传过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正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向中国的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的信仰者指明了另一条改造中国社会的道路。因此,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革命的榜样在五四以后已经逐渐由法国变为了新兴的苏俄。张君劢在一战后,与梁启超到战后欧洲游历,亲历资本主义世界的空前失败,进而对资本主义的前景失望,归国后与张东荪创办《解放与改造》(后更名为《改造》),发表了一系列宣传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文章。张东荪还组织了今人学会,并且一度参与了上海共产党的活动。当时英人罗素来华,发表了对于中国问题的一系列看法,一面反思资本主义的失败,一面反对在中国行马克思主义,为鼓吹基尔特社会主义大壮声威。张东荪先是在《时事新报》撰文,后又在《改造》第四期发表了《现在与将来》一文,阐发了罗素对于中国问题的系统判断,认为中国当务之急是开发实业、发展资本主义,而不是马上进行社会主义的运动。这立即遭到了陈独秀等人的反驳,陈在《新青年》第四号上发起有关社会主义的讨论,而《改造》第三卷六号上随之开辟“社会主义研究”专栏,梁启超、蓝公武、蒋百里等人都发表文章,申发对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具体主张,从而掀起了一场马克思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大论争。⑤
这场论争中所讨论的问题,基本上奠定了后来思想界对于共产主义的主要态度。首先,张东荪等人批判唯物史观,并且对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暴力革命夺取政权持否定意见,他们认为社会应该渐进地改良,故而把如何发展中国实业作为当务之急,他们认为社会改造以“行会”(基尔特)为基础才能使中国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张东荪说,“简言之,资本主义必倒,而社会主义必兴——特此所谓社会主义内容或经多少变化亦未可知,要总不是现在有缺点的社会主义。”他认为,相比较而言,基尔特社会主义是最完美的社会主义,其具有普遍的适用性。⑥而马克思主义者则坚持唯物史观不仅是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是为得着全部的真实”,而且是民众争取解放的思想武器,“这不是一种供权势阶级愚民的器具”。⑦有意思的是,虽然张东荪宣布了资本主义的死亡,马克思主义者指责他不过带着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假面具”,实际上却主张的是资本主义。⑧这些是双方在社会改造的指导思想、道路以及改造手段上的根本区别。其次,双方还从西方不同的国家摄取社会主义的思想,这也决定了他们之间的分歧所在。张东荪张君劢等人主要追随英国基尔特社会主义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即第二国际)的学说和理论,而陈独秀李大钊则主要信仰马克思主义,当时新兴的苏俄是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样板。张君劢在后来的回忆中指出,“其时,国人言社会主义,激烈者师法苏俄,温和者步趋英费边主义,德社会民主主义。五四前后,(张)东荪与陈独秀之对立,俨如清末孙(中山)康(有为)之相冰炭其最著者也。”⑨德英之与苏俄的西学背景的区别,宛如当时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的对立,则是广义上的社会主义思潮的不同走向。
以往的研究中,大多都把《新青年》胡适和陈独秀的分离作为当时思想界分裂的重要信号,而“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主义论战,往往作为马克思主义逐渐取得胜利,以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形成自觉意识的标志。⑩《新青年》的分裂固然由于五四一代在理念上的两歧性,正如张灏指出的,“五四”思想充满着一些对立的因素,如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怀疑精神与“新宗教”、个人主义和群体意识、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等等,这自然为其成员的分裂埋下了思想上的因子。然而在20年代的思想界,似乎还没有这么明确的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分野,胡适为首的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仍然将陈独秀等人引为同道,而有意把梁启超、张东荪等人视为“他者”,胡适指出要实现陈独秀等人的主义必须先实现胡适等人的主张,则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相通之处,正远多于其相异之点。1920年代胡适一直把社会主义作为他实现自由理想的必要条件,杜威对于社会改造的关怀,无疑影响了胡适向新自由主义方向的发展。
1920年代随着西方世界的分裂,中国可以效仿的对象,也不再是一个笼统的西方文明,而是具体地可以分为英美、法日、苏俄等不同的道路。在“思想界”中间,英美和苏俄逐渐成为了两个重要的取向。罗素、拉斯基等人的社会主义理论,在20年代曾对思想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即使胡适等人把张东荪归为“他们”之列,而把陈独秀等马克思主义者引为“同道”,他们和张东荪等人在社会主义的方向上,却有着更多的共同之处。《新月》时期胡适等人深受费边社会主义的影响,罗隆基把费边社对于社会问题的研究方法引入进来,他们还大量介绍了拉斯基的学说,而同时在上海的张君劢则翻译了拉斯基的力作《政治典范》。罗隆基因为“人权论集”遭到国民党压制后,北上任《益世报》的主笔,也曾参与到国家社会党的活动中。同时30年代的苏俄则凭借着“一五计划”的成功,也逐渐赢得思想界更多的关注。
二、社会主义的倡导
正如忽视1920年代自由主义者与社会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是不恰当的,同样在1930年代,我们也应该正视张君劢为首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与胡适等自由主义者在面对苏俄共产主义体制时,所持有的一些共同的态度和观点。当时思想界的趋势是,对于社会主义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向往和认同,而同时又都排斥苏俄共产主义的基本模式。只是随着30年代西方世界的新变化,《再生》群体更推崇英国工党所代表的社会主义,而胡适则明显把罗斯福新政当作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实现。同时他们又在不断分割着苏俄的社会制度,而吸取其中他们认为最适合中国的那些部分。
(一)社会公道的基本原则。正如在社会主义论争中张东荪等人所强调的,社会主义根本上是一种人道主义,这种人道主义的根本在于根据最合乎人性的标准来取决社会改造的方式。自然对于什么是“人性”的基本内涵的理解,主要来自于西方关于人性的各种理论,同时也反映了中国传统中的“民本”思想。毫无疑问,西方启蒙以来的政治理论基本都建立在对“普遍人性”的讨论之上,受到西方自由主义极大影响的中国思想界,也自然愿意从这一基点出发来拥护或者反对中国文化,同时向社会主义的皈依和对共产主义的批判,也必须从这里才能得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