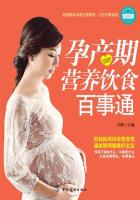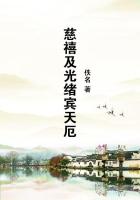与现代知识分子主要影响力在都市不同,梁漱溟的著作和他平易感人的演讲,却打动了无数乡村的民众。都市知识分子最切近地感受着西方文明的冲击,他们成为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代言人,而在面临着西方文明强烈冲击的境况下,梁漱溟却代表了中国文化的困扰和抗争。现代化本身就同时孕育了“反现代化”的力量。当梁试图从乡村改造中国的时候,他努力在超越“现代化=西化”的论断,他将西方现代科学技术置于一种道德力量的支配之下,而这种力量只有在中国文化的传统中才能找到。梁的相对主义倾向,让他坚信中国的根本是一种“乡村文化”,这必然使得中国的道路由乡村的发展为主导,以农村发展才能繁荣城市。在当时的思想界这自然遭到来自都市知识分子的猛烈批判。张君劢对于中国文化也颇持有几分同情,但是他对于“村治论”的批评却是严厉的。张君劢大概并不认为中国文化的复兴,需要依靠农村的力量,他主张在农村普及现代化的机器生产,根本需要利用现代技术和管理模式来改造农村,他相信采取苏俄集合农场是可行的,并且由国家掌控、管理和支配土地的所有权。在农业改革上,《再生》的主张已经超过了资本主义的模式,而要求一种高度集中和现代化的集产政策了。对梁漱溟批评最力的当属陈序经,他首先批判梁的化约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倾向,他根本反对把中国文明等同于“乡村文化”,而把西洋文明等同于“都市文化”,并把两者绝对地对立起来。在陈看来,如果想使中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舍“西化”外别无他途,试图走中国乡村改造的道路是行不通的。都市力量的崛起代表了现代化的方向,只有发展都市来解救农村的种种困境,而不是像梁那样寄望于农村来改造都市。陈的批评至少在乡村建设是否能实现“现代化”的导向上,对梁是一个重要的打击。梁不得不承认,他的一系列兴办合作社、使用新技术的举措收效甚微。陈序经指责梁的想法不过是另一种“中体西用”罢了。吴景超也认为把中国一切问题归结为农村问题是不合适的,当都市得到充分发展以后,农村自然会被带动起来,他认为应该以都市为中心来发展农村。虽然相比较而言,中国的广大地区都是农村,但是正因为如此,才必须大力拓展都市的影响力,并最终使得中国实现由“农业立国”向“工业立国”的转变。
陈序经等人的“西化派”非常重视现代化过程中的城乡关系的失调。不过,他们认为都市对于乡村的优势是必然的,在“都市化”的过程中,农村面临的困难也是必须付出的代价。当乡村感受到来自都市的威胁时,正说明都市蕴藏着巨大的力量。梁漱溟则非常担心都市对农村的破坏力,这不仅表现为都市在经济上的支配力,进而实际上体现了帝国主义势力对中国的操纵,而且都市还在破坏着农村中所保存的道德精神。梁常常谴责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了中国经济的贫困,他警惕都市吞噬乡村的现实,即使在建国后他与毛泽东的争执也是自觉地站在乡村的立场,而反对“工业化”对农村的剥夺。
人们一般都会强调胡适与梁漱溟的区别,但是在农村问题上他们却有一些相近的想法。胡适在谈到救济农村问题的时候,非常反对政府的力量渗透到乡村中去,不过他的理由是中国目前还没有形成强有力的政府。胡适提倡实行一种“无为”的政治,在政府既没钱又没人才的境况下,无法实现积极有为的农村救济,只可以采取“消极无为”的救济,也就是裁官、停止建设、裁兵、减除捐税等。他甚至主张将政府的权力只缩小到警察权,“我们只是贫儿,岂可以妄想模仿富豪的大排场?我们只是婴孩,岂可以妄想做精壮力士的事业?”在胡适的政治哲学里,人们所处的进化的某个阶段,决定了人们只能实行和这个阶段相应的制度,试图僭越进化的环节是徒劳无益的。在中国尚未有强大的政权之际,就采取一种积极建设的政策,无异于“拔苗助长”。在胡适看来,现代政治需要的是知识和人才,在缺乏这些要素的时候,就不能盲目勉强地利用政权来搞建设。蒋廷黻在《大公报》上撰文,担心“建设的前途堵塞”了,实际上针对的是胡适的“无为政治”。胡适当然不是反对“建设”而是要求“合理”的建设。他的目的在批评国民党政权在农村的盲目建设,在他看来“建设”的结果是各种摊派盛行,这不断增加着农民的负担。以“建设”为名实际上却造成了“扰民”的后果,这使得人们得出一个怪论,即“建设越多,土匪越多”,越是“建设”,农村的处境越艰难。梁漱溟早从20年代开始,就反对那种以政权力量来进行的乡村建设,他担心乡村在不断地被官僚的力量所控制,他批评山西的“村治”运动受到太多的行政的干预,而必然会走向失败。胡适和梁漱溟似乎都认为,在乡村存在一种自发的社会秩序,政权的力量必须避免干预这种秩序。当然,他们的理由大相径庭,胡适出于经验主义的和进化论的社会秩序观念,而梁漱溟则出于他对于中国文明建设基于乡村之上的强烈信念;胡适判断中国的政权尚处于“前现代”的状态,必须向现代化的方向努力,梁漱溟则根本排斥西方化的趋势,希望在中国乡村中寻求未来秩序的重建。
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国家的“政权建设”。国民党政府在十年建设时期,确实曾经致力于将国家政权的力量深入到农村去。蒋介石出于“剿匪”的需要,修筑了大量的公路,交通的便利有利于国家政权更好地控制乡村。同时,国民党在农村推行保甲制度,地方上的保长承担着教化、治安以及税收的职能,他们成为乡村和国家政权的中介。“县财政”的增加也说明农村对于基层政权的依附加强了。1930年代,国民党政权也开始推行“乡村建设运动”,他们在一些省份设立了模范县。在CC系的主持下1933年浙江的兰溪和江苏的江宁设立了两个模范县,试图改变乡村的面貌,《时代公论》的梅思平(当时他是中央政治学院的教授)成为了江宁试验县的县长。国民党还压制那些民间的乡村运动,他们认为必须把乡村建设控制在国家政权的范围之内开展。对于乡村建设的积极组织者来说,来自都市的、帝国主义势力的、以及国家政权的种种压力,都迫使他们无法真正从农村利益出发来寻求改造中国的道路。
总的来看,1930年代思想界仍然保持着对社会改造的极大关注。从20年代以来,他们就一直希望了解中国问题的社会根源,当然在他们寻求改造中国的道路时,共产主义运动(国内的、国际的)给予了他们极大的刺激。他们必须试图回应苏俄所解决的问题和指示的道路,他们又必须面对共产党在农村日益广泛的影响。在西方国家纷纷转向重视社会政策之时,他们无不在思考着如何保障“社会公道”的真正实现。因此,“社会主义”的倾向在1930年代的思想界是普遍的。
注释:
①参见(美)格里德著、鲁奇译:《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50)》,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
②关于西方文明在中国思想界的分裂开始于五四前后,以及这一分裂的过程对于思想界的意义,参见罗志田:《西方的分裂:国际风云与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③伯纳尔将1907年视为“无政府主义”获得胜利的标志性的时间。参见(美)伯纳尔著:《一九○七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④参见葛懋春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曹世铉著:《清末民初无政府派的思想》,社会科学文献,2003年。以及杨幼炯著:《中国政治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98年,362—363页。
⑤参见陈汉楚编著:《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实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135—144页。以及杨幼炯著:《中国政治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98年,365—370页。
⑥张东荪:《一个申说》,“社会主义研究专栏”,《改造》第三卷第六号,1921年2月15日。
⑦李大钊:《唯物史观在现在史学上的价值》,《新青年》8卷4期,1915年10月10日。
⑧《先驱》第1期。
⑨转引自陈汉楚编著:《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实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143—144页。
⑩陈汉楚书中尤其强调了马克思主义者正是通过这两次论战,扩大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传播。胡适为首的自由主义群体以及二张为首的民主社会主义群体的理论,被塑造成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全面胜利的反面陪衬。参见氏编著:《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实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125—144页。
张灏:《重访五四:论五四思想的两歧性》,收于《张灏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
胡适:《致陈独秀》,《胡适往来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119—120页。
参见罗志田:《西方的分裂:国际风云与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再生》群体中一些人坚持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民主制度在基本精神上是相通的,都反映了人性的一些基本要求。朱亦松强调儒家思想本来就是一种“民治主义”,而诸青来认为自由平等的思想与忠恕之道是相合的。参见朱亦松:《新时代的民治主义》,《再生》1卷9期,1933年1月20日,以及诸青来:《社会改造问题——答俞寰澄先生》,《再生》1卷2期,1932年6月20日。
在胡适一生的文章中,他使用“个体主义”、“个人主义”的表述远远多于“自由主义”,这是他特殊的阐明自由主义理念的方式。当然,西方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和逻辑前提,可以说是个体主义的。不过胡适理解的个人主义,则具体化为易卜生等偶像的榜样。
罗素把战争归结到人性中欲望的毫无节制的发展。在他看来,人类采取行动的动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无意识的冲动,“冲动比有意识的目标在形成人的生活方面有更大的影响”,但是欲望和冲动具有双重的效应,“冲动一方面是战争的原因一方面也是科学艺术恋爱的原因。”因此冲动可以分为两类,占有性的和创造性,他希望能够提供一种比较好的社会秩序的模式,以体现更多人类的创造性和避免占有性的无节制的发展。参见罗素:《社会改造原理》原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另见《罗素的社会哲学》,《新青年》第七卷第五号。
参见罗素:《社会改造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82页。
张君劢:《国宪议》第十篇之“社会主义之规定”,上海时事所报馆,1922年。
《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胡适文存三集》,亚东图书馆,1931年。
他在1926年9月23日的日记中,提到他准备写一本关于“西洋文明”的书,在列出的提纲中他把科学、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归结为西洋文明的基本要素。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4册,1926年9月23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20世纪的自由主义理论,已经表现出不同于19世纪的一些基本特色。当然这与西方世界在19世纪以来,所经历的种种社会巨变有着密切关系。新自由主义倾向于关注和处理社会平等的问题,这似乎也受到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日益扩张的影响。西方国家的社会福利政策,便是自由主义对平等问题的处理办法。罗尔斯在他的经典名著《正义论》中,成功地从政治哲学的高度,为自由与平等的关系做了说明,目的即在建立一种“公平的正义”(justiceasfairness)原则,参见罗尔斯著、何怀宏译:《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关于自由主义对于平等问题的关注,参见钱永祥:《自由主义为什么关切平等:当代的一个看法》,收于张斌峰、张晓光编:《殷海光学术思想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2001年,138—150页。
参见朱亦松:《新时代的民治主义》,《再生》1卷9期,1933年1月20日。
同上。
张东荪主张基尔特社会主义,自然是认为它可以解决经济民主的问题。到了40年代,张氏坚信苏俄的共产主义体制根本解决了经济民主的问题,故而,也从信仰社会主义转向了共产主义。
诸青来:《资本主义之过去与将来》,《再生》1卷5期,1932年9月20日。
记者(张君劢):《我们与他们》,《再生》1卷10期,1933年2月20日。
东荪:《生产计划与生产动员》,《再生》1卷2期,1932年6月20日。
记者(张君劢、胡石青):《我们所要说的话》,《再生》创刊号。
张君劢:《胡石青先生之言行》,《再生》(重庆版)第87期(纪念胡石青先生特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