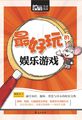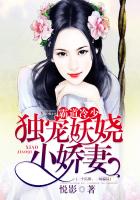1932年胡适在长沙的一次演讲中,提出了他对于中国政治出路的看法,他希望人们认清政治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统一的、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国家”,而阻碍这一目标最大的敌人是所谓的“五鬼”,“贫、病、愚、贪、乱”。这里仍然是在强调一切政治问题的根源,都在它的社会背景中。因此,政治现代化的根本任务就是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再生》群体在国家社会党的宣言中也把“贫穷”作为首要解决的问题,“照他(柯尔)的意思,是以为贫穷由不平等而生,不是因为贫穷而方有不平等。但我们在此处则认为各国的情形或有不同。以中国目前的情形而论,恰与之相反,实在是患寡而甚于患不均……所以中国的唯一无二的问题是如何增加国家民族的富力。”可见,思想界首先都把改造社会的注意力投向了如何增加国民财富,即如何解决贫穷的问题。
贫穷问题最严重当属中国的农村。在一个被迫进入现代化的国家,农业的发展本来就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再加上中国大量的农业人口和国民经济基本上处于“以农立国”的阶段,使得如何解决农村在现代化中的地位和命运,成为困扰国民党政府的难题。南京政府在最有希望的十年里,于农村问题无所建树,可以说是整个政权走向失败的重要原因。当1930年代国民党忙于“剿共”的时候,实际上也在农村问题的另一条战线上和中共进行着激烈的争夺。知识分子虽然赞同“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但是他们希望通过有效的社会改革来限制共产主义在农村的广泛影响,而仅仅靠“军事”上的镇压是远远不够的。
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的农业经济继续衰落。军阀战争、土匪横行的影响不仅没有缓解,而且30年代还遇到了更大的危机。就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扬子江流域发生了大面积的水灾,大量人口流离失所。1932年,中国农业首先失去了东北市场,继而世界经济危机开始影响农村。1931年下半年开始,英、德、日纷纷宣布放弃“金本位”制,1933年美国也加入进来,1934年6月美国通过白银法案,开始大量收购白银,这造成中国银价上涨、大量白银外流,同时物价暴跌。经济萧条首先就影响到中国的农业,农产品的价格大跌,据估计,“农产品价值在全国总产品价值中所占的比例,按当时价格计算,从1931年—1934年下跌了47%。”农民的收入随之受到严重影响,进一步激化了农村贫困的现状。当时思想界的许多人,都预感到农村危机必将引发新的社会革命。
正是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开展了他们的土地革命,试图解决农村最迫切的问题,满足农民分有土地的愿望。晚清废除科举以来,作为地方精英的乡绅集团便不复存在了。乡村逐渐被那些所谓的“土豪劣绅”所把持,他们自私自利缺乏传统乡绅的公众意识,只为个人的敛财。他们吞并了大量的土地,然后又投资于城市的产业或者是购买国家的“公债”。另一方面,土地兼并严重,自耕农的数量减少了,农民不断地失去土地。由于田赋成为了地方税,地方军阀为了维持武备而大肆征敛,这迫使更多的自耕农沦为了佃农。同时,地主又把地方军阀的各种重税转嫁到农民身上,因此农民的负担越来越重。每亩田赋及其他附加可达农民收益的百分之二十左右,而高者可达百分之四十。高利贷者乘机而动,从农民身上榨取暴利。这样农村中憎恨地主和高利贷者的情绪不断高涨,同时要求土地的呼声也越来越激烈。这一切为共产党顺利的开展农村的革命运动制造了条件。1931年,苏维埃政权在江西瑞金成立,并且很快就在苏区开展了土地革命。毛泽东将农民进行了区分,并且对于不同的阶层采取不同的策略,这样那些贫农和雇工构成了群众组织的先锋,开始了雷厉风行的“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运动。蒋廷黻敏锐地观察到,“是则明明白白的中国红军的战斗力不是来自共产化的工商业。据共党自己的报告及剿共国军的观察,红军在江西极盛时期的力量实来自农民的合作。共党为农民做了什么好事呢?只做了一件事:干脆的、彻底的消灭了地主阶级,实行了耕者有其田。”“租佃的免除”抓住了农村问题的关键,也凸现了国民党在农村问题上的失败。
蒋廷黻的批评是中肯的,他指出国民党已经失去了对于“民生”问题的关注,而这曾经是国民党获得民众支持的重要支柱。国共合作中,孙中山倾向于把他的“民生主义”解释为社会主义,从而奠定了两党合作的理论基础,也使得他顺理成章地获取了苏俄的支持。在地方,国民党的左派分子和共产党合作,动员农村的群众运动。然而,在国民党“清党”之后,国民党的理论家们也开始致力从学理上,划清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限。胡汉民和戴季陶确实花了很大的功夫来澄清孙中山学说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区别,戴季陶有意构筑了一套“民生”的哲学,并且与儒家的传统道德相接续。在土地政策上,国民党也开始表现出一种承认地主利益的保守倾向,他们维护现存的农村秩序,而各种农村势力也通过各种方式进入到国民党的地方政府中,或充当国家向农民征收赋税的“经纪人”,以维持他们在地方的显赫地位。于是,知识分子普遍批评国民党“三民主义”,只剩下了民族主义的一民,而国民党内部的反对派也可以借着总理“民生主义”的遗教打起反对的旗号,就如同福建事变中所做的那样。当红军在瑞金拥有了“红色基地”,国民党的“剿匪”却屡遭失败以后,蒋介石也逐渐认识到问题的严重,公开宣称剿匪要依靠“七分政治,三分军事”,决心解决农村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和土地问题。
思想界希望通过“和平赎买”的方式,由国家出资从地主手中购买土地分配给无地的农民,而不是像共产主义那样通过“暴力”没收地主的土地。1935年阎锡山发表了一个《土地公有案》,他的办法是由村公所发行公债收买全村的土地为公有,然后分给有劳动能力的人,课以较轻的税。这个方案得到了丁文江等人的赞同。丁指出虽然田赋很重,可是农民承担的田租更重。丁认为目前农村的关键问题是农民没有土地,应该把土地转移到自耕农手中,尽快实现真正的“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他希望政府筹措大量的款项,而这笔财政的来源则主要依靠清理田赋、举办土地测量,他相信中国还有大量可耕地未能纳入国家的税收。吴景超也要求通过“赎买”的方式,将土地和平地转移给佃农,但是他的方法是向地主发行土地债券,其本息在“不加重佃户负担”的前提下,由佃户于若干年内还清。丁担心吴的方法仍然在若干年内,使得农民的生产未有增加。当时农民的问题是复杂的。一方面他们不满沉重的地租,渴望拥有土地,另一方面由于“田赋”在国民政府时期属于地方税,被地方军阀势力所把持,因此各种地方的“摊派”往往使得有地的农民不断赤贫化,而不得不出卖土地变为雇农。何廉了解农民的赋税负担,在他看来在实现“耕者有其田”之前,先得保证农民的负担不要太重。农民的负担长期有增无减,不仅田赋和各种附于田赋的税捐,都直接或间接征之于耕者,而且关税、盐税、统税、印花税、烟酒、屠宰以及营业等税属于消费者,也直接间接征于耕者,田赋苛重、地主逃税,而造成“耕者有其赋”的局面。何廉认为“减赋”似乎比“有地”更为迫切。在“平均地权”还是发展农业经济之间,很难说那一个更为重要。但是,显然贫困、沉重的负担、教育的匮乏,和天灾人祸纠缠在一起,使得农村需要解决的问题非常复杂。
国民党试图改变他们在农村的无所作为。随着“剿匪”取得的一定胜利,蒋介石在豫、鄂、皖、赣等共产主义活动过的省份,开始推动所谓的农村复兴运动。行政院下设专门的农村复兴委员会,来研究如何振兴农村的经济。在收复的省份农村复兴委员会还在县、区、乡各级建立了组织,一面恢复农村秩序,处理“分田”引起的所有权的纠纷;一面振兴农村经济。这些复兴农村的政策范围是广泛的,试图全面解决上述提到的农村问题。豫、鄂、皖、赣四省的农业银行,向农民提供发展生产所需要的贷款。人们认为农贷不仅可以把农民从债务的灾难中解救出来,而且农民可以购买新的生产工具。在江西,一种将保甲制度和基础教育相结合的“保学制”开始推行,普及义务教育和国民教育的活动得到顺利开展,这对江西农村社会的变迁产生了重要影响。当然,国民党也推行了有利于农民的土地政策,在收复省份他们鼓励农民耕种无主的田地,并确定他们的所有权。1937年通过的《土地法》修正案还明确了以下原则:倾向于扶植自耕农,限定地租最高额为地价百分之八,荒地承垦者待垦熟后无偿获得所有权,设立土地银行发行土地债券,国家征收土地得用土地债券以为补偿。这些修正原则,明显弥补了原《土地法》中对于农民保护不足的缺陷。
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乡村的改造,早从20年代中后期就开始了。尤其在1927年,也许是共产党在农村的社会动员,使得知识分子看到了中国农村中所蕴藏的巨大动力,这一年掀起了乡村运动的一个高潮。在冯玉祥支持下,陶行知建立了晓庄师范,晏阳初的平民教育促进会开始转向农村,黄炎培主持的中华职业教育社也集中到农村工作上,沈定一则在他的家乡浙江东乡开始了乡村的改革。军阀对乡村运动的支持是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他们也很重视势力范围内的“民生”问题。在山西,阎锡山很久以来一直支持“村治”运动。而在河南,军阀冯玉祥、韩复榘委托王鸿一兴办了河南村治学院,专门研究乡村问题,并培养年青的乡村建设者。王鸿一是《村治》月刊的负责人,他被梁漱溟视为最杰出的乡村运动的同道。而韩复榘则成为梁漱溟在山东一系列乡村改革运动的支持者。梁漱溟在邹平的试验主导了30年代中国的乡村建设,他建立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还创办了《乡村建设》。乡村建设的另一个焦点在华北,晏阳初依靠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赞助,开展了在定县的一系列乡村教育计划。
虽然乡村建设运动的目标,都在把农村的改良作为解决中国种种问题的根源,但是梁漱溟和晏阳初代表了乡村运动的不同道路。梁更多依靠那些与传统中国有着密切联系的国内开明势力,而信仰基督教的晏博士则更多体现了西方机构援助中国农村的慈善义举。晏阳初认为中国人的四大缺陷是“愚、穷、弱、私”,他提倡四大教育来解决这四大弊病,即文艺教育、生计教育、体育教育、公民教育,综合而构成新民的教育。其中对中国问题的诊断,倒与胡适有相近的地方。晏阳初在农民中间推行了“识字运动”,改善农村的公共设施和医疗条件,推广了培植农作物和饲养家畜的科学技术。虽然梁漱溟也诉诸于这些手段,但他的目的是通过这些手段重塑中国社会秩序的基础。梁一系列乡村建设纲领的基础,是他的哲学观念。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他已经试图区分了中、西、印三种不同的文化发展的道路,他将中国文化的道路视为与西方是完全不同的。他将中西文化化约为一系列原则的根本对立:原地不前的/向前进取的,争斗的/和平的,讲究科学的/讲究道德的,农业立国/工业立国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中国一切的社会改造都必须从这一根本认识出发。他认为中国文明的根源即在“乡村”中间,“中国就在他的乡村里”。当作出这个判断的时候,梁是“价值论”的,而黄炎培和晏阳初则是“问题式”的,乡村是黄和晏解决中国问题的下手处,梁则希望从乡村基层发展出一种“新文明”,这将决定中国现代化的走向。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梁象西方的许多“民粹主义者”(比如托尔斯泰)一样,充满对工业资本主义的恐惧而将乡村美化为“世外桃园”。他的导向仍然是“现代化”的,只是这一切都根植于中国原有的儒家秩序的重生。梁坚信,一国的文明必须是从内在的条件自然生长出来的,而不是硬性从外面移植的。中国过去与西方走得是不同的道路,将来仍然无须走到同一条路上去。因此他对晏和黄以西方文明的方式来救济农村,并不以为然。梁的乡村改造模式类似中国古代的“乡约”制度。他希望恢复乡村的风化和美俗,掀起一种类似宗教的群众运动,从而把基层的民众组织在一个集体主义的社区中。那里成为道德和精神力量的发源地,从而可以挽救人类道德日益衰退的现实。梁希望乡村的领导者,既是贤者又是专家,他既可以利用他的道德力量使得“四方来归”,又精通专门的学问,可以指导民众掌握现代技术。梁自信地宣称,以这种方式才能真正在中国实现“现代化”,因此他并不否认西方的冲击,“西洋的近代文明,与中国固有的文明,结合演成今日状况”,但是他并不认为现代化就是“西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