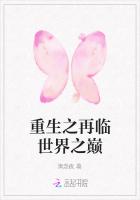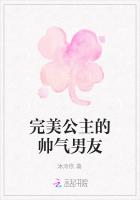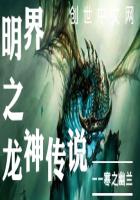1905年,27岁的特里达普搭乘海轮“旧本公主”号来到中国。他不仅面临着理想和现实的种种矛盾,暗暗有一种受骗的感觉,而且也面临着新教传教事业的分歧点。这时候西方新教在中国的传教已近百年。1807年,苏格兰人罗伯特·马礼逊作为第一个来华的新教徒,进人商埠广州,在27年的生涯里一边将圣经译成可怜巴巴的中文,一边发展了十个信徒。参与他工作的另一传教士威廉·米怜,则在研究汉语的同时感叹这种语言的艰深。美国新教的传教士以伊利亚·布里奇曼和戴维·阿贝尔为首,随后也在1830年到达中国。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到1907年纪念新教来华传教百周年的“世纪大会”在上海举行时,全中国已有3500多名新教的外国传教士。这一成果并不完全是信仰的力量,而是恃靠了军事上的强权:英法联军侵扰京津后于1860年签订的《北京条约》,强制清朝承认外国人在华的传教权,传教士并享有治外法权。
特里达普作为基督教青年会的地区书记参加了“世纪大会”。经过一位美国年轻同行的点拨,明白了会上表现出来的年长和年轻两代人对传教事业的不同理解,恰好呼应了他心中对旧的传教方式的怀疑。老一代传教士继续把拯救灵魂当做中心,收效甚微,反倒和异教孔子儒家注重道德的做法纠缠在一起。新一代传教士(他们是出席会议的大多数)认为传教的主要任务是帮助推动社会的进步,西方国家的文明进步正是因为信奉基督。他们不再宣称西方人能够免于罪恶,而主张至少有一种精神足以对抗那些让人性堕落的东西,不至于像落后的异教国家充满了腐败、盗窃、淫秽、因软弱导致的残忍,所以“我们的传教有责任给这些国家注入一种新的意识,使它们摆脱道德的废弛和社会的不公正。”特里达普被告知,“更有远见的美国传教士比美国政府更理解中国人,他们也比他们的前辈更少倾向于把帝国主义的行为当作上帝的行为。”会议通过的两个文件之一(它反映了新一代传教士的立场)声明:“我们对中国的最大愿望,是它的繁荣和在世界各国中取得领先地位;我们相信,我们传教事业的缓慢、渐进和稳定的影响所致力的方向,是带来建立于公正、美德与真理之上,而不是军事力量之上的繁荣。”
大会期间对特里达普至关重要的另一事件是他同老一代牧师约书亚·巴格瑙尔(JoshuaBagnall)的谈话,长者的智慧对他同样具有吸引力。巴格瑙尔参加过戊戌变法,是深受革新派人士信任的外国传教士,康有为邀请他加人强学会。如果不是变法突然夭折,光绪帝还准备聘他做顾问。他给特里达普算了一笔账,新教的传教士来华人数每年以千分之十五的比例递增,但中国新生儿每年有三百万,按照通常的传教方式单单在人力上就是大问题。所以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即“运用重力原则”,换言之传教士要在最上层人士中做工作,让基督的影响从上层向下层渗落。
两方面的启发使特里达普开始领悟到,要实现他的宗教启蒙理想,必须要通过和中国精英人士的接触和联系,投入一个“缓慢、渐进和稳定”的改革运动中,而不是像目前那样做一个教会学堂的英语老师,或跟着其他传教士到庙会上去唱唱圣诗,发发宣传品。从此他加倍发扬自己的语言天赋,迅速从书面和口头上掌握了官话(普通话的前身),并进而攻读《论语》、《红楼梦》等儒教经典和古典小说。他说自己的一生目标是“用中文为中国人服务”。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文化交往的具体方式。当异质的美国新教文化传入中国时,一度曾用自己的宗教信仰来改造广大群众,遭遇反抗和抵制后,其内部产生分化,出现了企图和中国本土的进步改革运动结合起来的倾向。其发挥作用的渠道,也由普通老百姓向上层的知识分子和其他人士倾斜。不过,新教文化自以为找到了和中国异教文化的嫁接点,却没有料到在上层同样会有拒斥和对抗。许多年后,特里达普才最终明白,美国新教传教事业20世纪初的这一新倾向,表面看来是非政治性的,实质是多么具有政治性。虽然它公开宣布不想让自己和信徒们违背政府的法令,也绝不干预政治事务,并和美国统治者保持着距离,实际却作为一股力量,深深卷入了中国的现代化行程,并为此付出了代价。小说里有个耐人回味的细节:在牯岭中文学习班期间,他和同事们去参观宋代朱熹执教过的白鹿书院,表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景仰,回来的路上两个年轻美国人(一个来自耶鲁大学,在长沙协助创办了中国耶鲁学校;一个是上海圣约翰大学教员)不间深浅跳入瀑布,被湍急的水流淹死了。这个意外虽没让特里达普陷入沮丧,反而悲痛化为了动力,但是否也在隐喻着什么呢?
但在当时,具体该怎么做,特里达普心里仍没底。从牯岭回到他原来的汉语学校所在地保定,通过中文教师川先生,他进一步了解到戊戌变法和太平天国(这是一次在新教传教士影响下策动的农民起义),也读了康有为重要的变法著作《孔子改制考》,并为川先生身上表现出来的旧知识分子的失败、悲愤和积弱而深深感动,还研究了明末清初利马窦等耶稣会教士的传教活动。随后他参加了为期三周的救灾活动,耳濡目染了灾民的悲惨境地,体会到灾民们首先需要的是面包,而不是福音。所有这些感受沉积在一起,终于有一天感悟突如其来地出现了,他漫不经心地合上了写利马窦事迹的书,目光落在川先生送他的小玉马和刚从美国老家寄来的陀螺仪上——
我感到突然一击。我站起来。仿佛有什么东西早就在那里了,但一直躲着我,忽然清晰可见了。陀螺仪!卡特老师的展示法!我可以用那样的展示法教会成千上万中国人!不再是北开中学(他在天津教英语的那所学校)的小教室——不,我可以去任何地方……对许多人宣讲科学的精确性。这将是传授上帝安排的复杂、简明及神奇性的方法。这将是运用我的技能,帮助川先生和天津博学的朋友林富成(北开中学校长),以及灾区嗷嗷待哺的饥民们的最好办法。我太激动了!我捡起陀螺,举到我眼前。它在黑暗中闪烁着,就像一只圣杯!
在特里达普看来,中国人的致命弱点就是缺乏科学精神,凡事都讲“差不多”。他接受巴格瑙尔的见解,只有科学才能令中国人信服,也只有科学能帮助中国走向富强,最后让中国人皈依上帝的智慧。但我们也看到,他得以感悟的前提,首先是对中国语言、历史、文化和实际情况的了解。由此可见,文化的交流过程,即使是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影响,也必须是双向适应的嫁接,否则交流不可能进行。
从此以后,特里达普成了一名展示各种技术发明和科学仪器的巡回传教士。他回美国争取到一些资助,利用调动到上海的机会,在北苏州路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设计制造仪器和道具,不定期地到各大城市一边表演一边讲授有关知识。他所表演的光、电、力学的最新成果,如无线电报、飞机等,被归结为上帝创造的自然的魔力,在当时落后的中国看起来如同神奇的魔术,在懂行的人目光中也是成功的创举(如无线电报的收发,有人认为表演得比发明者马可尼本人还要成功),因此造成了相当轰动的效果。袁世凯、黎元洪、孙中山等上层人物都支持他,有的还帮助组织和参加了他的宣讲。基督教青年会也为他的突破而感到鼓舞。特里达普沉浸在自己最初的成功中,根本意识不到要解决中国的落后问题,单靠科学技术是行不通的,他个人的努力也不可能改变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辛亥革命爆发了,他漠然无动于衷,甚至他的助手阿珠剪掉了脑后的辫子,他也只是说:“不错,你模样更漂亮了。”并因中华民国宣布宗教信仰自由,对自己传教工作的前景感到相当的乐观。
但不久以后,成都之行给了他意外的一击。还在入川前,长江三峡两岸陡峭山崖上的石刻、壁画、纤夫小道及悬棺等特殊景致,就让他深为震动:“大卫不断地感受着中国悠久的过去,感受着那种无穷无尽的生存的使命的意义,感受着那种不断轮回的期盼、辛劳和期盼的意愿,以至于他自己想帮助中国改变面貌的令人生厌的急切心,都开始变得似乎毫无效果了,就好像江水要摧垮岩石一般。”而到了成都,实际情况验证了他的预感,等待他的是完全不同于上海、广州、天津等沿海城市的内地落后和闭塞的情景。甚至他那些外国传教士同行们,也固守着传统的传教方法,局促一隅,却又颟顸自得,反对他的以科学技术为中心内容的新型布道。
特里达普重新陷入了沉思和反省,转而研读圣经,从中寻找力量,终于发现了自己的错误。一度他自以为是旧约中的先知伊利亚,在帮助迩南人反对异教的恶神帕奥尔,但在阅读和思考过程中——
……突然我被一个炫目的想法击中了:在这里,在中国,对中国人来说,我并不是伊利亚先知,而是恶神帕奥尔的祭司。因为伊利亚是抵抗侵略的本族人,不仅是外国的礼仪和偶像的侵入,也是外国的政治阴谋和权力的侵入。以伊利亚的宗教目的而论,他也是个爱国者。而我在中国,是一个外国上帝的教士,在我的背后(以及压在我良心上)是外国人的炮舰、鸦片、抢掠和领土扩张。
这是个令人震惊和沮丧的想法。我的内地之行,就像实践证明的那样悲剧性地不合时宜,已使我明白,真正的中国是不会因遥远的首府政体更迭而在一夜之间改变的。旧的势力要求孔儒之道下的伦常和顺从,还有中国人用以代替爱国主义的因古老产生的骄傲,它们都绝无可能因南京政府法令宣布宗教自由就一扫而光,后者本来是为我打通了大路的。
从逆扬子江而上的牧师身上,我们依稀再度见到了《孤石》中那位年轻工程师的身影和心情。但他阅读圣经时的反思,包含有更深刻的自我批评。这几乎是立场的大逆转。这位同样年轻的外国传教士(是年特里达普33岁),换了中国人的眼光来看待中西文化的接触和冲突。但他真正能像中国人一样来认识和解决祖国的现代化问题吗?他又处在焦虑中:“我该如何正确地工作?并用正确的方式?”
焦灼和困惑
随后的几年里,特里达普继续他的科学传教士的职责。人员增加了中方人士,有一些从美国学成归来的信仰新教的学者或科学家参与其事;实验室扩大了规模,成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传教和讲授展示的内容也扩充了,添加了公共卫生的讲座;宣讲的范围也在铺展:湖北、湖南、河北、北京……甚至福建的几个县城和“基督教将军”冯玉祥的兵营,都留下了特里达普的展示团(现在每次都有中方的宣讲者和他合作)的足迹。但焦灼和困惑仍如影相随。
他开始怀疑这些展示式宣讲的真正效果,觉得人们只是好奇地当作魔术来观看,所以自己的做法同老式的街头布道和巡回传教没什么区别;他不清楚在自己宣讲的社会启示中究竟还有无福音的启示;面对着层出不穷的自然灾害和水深火热中的人们,来自基层的责备一直萦绕在他耳畔:“我们四周全是苦难,你倒来讲解无线电报的原理?”他甚至嫉妒中国的同行,认为他们剽窃了他的方法,他们的加人使他从独一无二的首创者沦为普通的成员;他痛楚地觉察到中国人对自己的敌意,以及自己对中国人的居高临下的优越感……
因此,当他遇见冯玉样将军在部队中推行基督教信仰,从早到晚都要士兵做祈祷、唱圣诗时,着实激动了一番,以为这就是他梦寐以求的能够从上至下改造中国的强力人物。他轻信了冯玉祥当面的表白,忽略了后者之所以皈依基督相当程度上是躲避袁世凯迫害的权宜之计。其实何止冯玉祥一人!洪秀全、孙中山都曾是基督教徒,却选择了自己的革命道路;梁启超曾为北京基督教青年会指导委员会一员,后来变成保守派;蒋介石先和信仰基督教的宋氏家族联姻,后来本人也信奉了基督教,搞的完全是自己一套……包括袁世凯,他也宣布过宗教信仰的自由,支持过特里达普的传教活动,后来却证明是满脑子做着皇帝梦的独裁者。其实,刚踏上中国土地不久,特里达普的好友、天津北开中学(令人联想到著名的南开中学)校长林富成就告诉过他,中国人的最大特点就是对西方人所谓的真正的“宗教生活”不感兴趣。中国人出于自己的利益攸关,所做出的努力和奋斗,极少会以某一宗教学说为指针。
甚至在特里达普短期回美国期间,困惑仍纠缠着他。兄长保罗问他:“你真的继续相信耶稣基督是适合中国人民的答案吗?难道你希望这个病弱的巨人复制一个‘黄金的西方’?”特里达普口头强硬的回答并不代表他坚信这一切。事实上,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越来越繁荣的美国已夺去了家里的农场,迫使妹妹格蕾西当一个低收入的装罐头女工。但他照样为中国趋向现代化的任何一点进步高兴,感觉到中国才是他施展抱负的真正家乡。有一个细节很说明问题:和绝大多数传教士抵制五四运动的态度不同,他认为无论对中国和对基督教青年会,这一大风潮是件大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