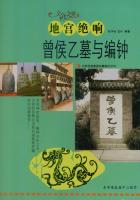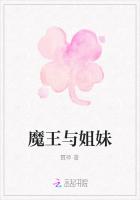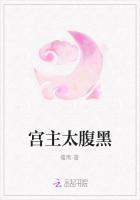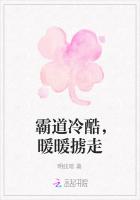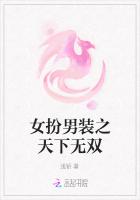《白莲》仍以第一人称的手法,讲述女主人公在中国的遭遇。故事从白莲已成为非暴力民权组织的成员,并面对赤贫省份的顽固官员开展静坐斗争的那一刻开始倒叙。她曾被转辗倒卖,从北京到河南,到城镇到乡村,更换了几个主人,逐渐学会了用黄种人的目光和标准来看待白种人,明白了白奴的法则就是:“不管你在黄种人面前多么恐惧,也不管多么愤怒,多么高兴,控制住你的面部表情和四肢;要显得毫无感情;让你的脸一无所动,就像画在弓弧上的人物图案。”经过几年的叛乱和斗争,奴隶制取消了。白莲和情人洛克来到湖南的一个小村子开始了新生活,但实际生活状况和美国南部的黑人相差无几。然后他们随着解放白奴向工业化城市移民的浪潮来到上海。白莲进人丝厂工作,以她的女性魅力吸引了黄种人中的自由主义者,并和其中一人坠入爱河。觉醒了的解放白奴和自由主义黄种人共同组织起了非暴力的抵抗运动,并把它从上海这样的工业中心推广到边远省份。小说以白莲真诚相信不同种族之间应展开对话而告终。
很清楚,白莲的经历实际浓缩了美国黑人长时期的苦难和斗争,只不过被倒置于白种人身上。作者的这一想象令人联想到斯威夫特《格列弗游记》关于慧驯国的描写。在慧驯国中,现实生活中的一切也被颠倒了过来。马成了地球的主人,而人类倒成了马豢养的家畜,彻底暴露出他们的劣根性。《白莲》同样是个尖刻的冷嘲,试图运用艺术的力量,促使广大的白人读者设身处地感受一下当奴隶的滋味。遥远的中国在小说中只是个虚拟的背景,虽然有赫西童年的回忆和采访的印象在内,但不可能将它看作真实的图景。
事隔20年后,《召唤:一个美国传教士在中国》(1985)才在历史维度上较为真实地表现了中国主题。这是一部兼有传记性和文献性的小说。从赫西的家庭背景来看,人们很容易将这部描写美国传教士生涯的小说当成他父亲的传记。小说也明白无误地题献给作者之父洛斯库·赫西,卷首还摘录了魏文帝曹巫的《悼父诗》:“长吟永叹,怀我圣考;日仁者寿,的不是保?”所以上述看法不无道理。但据小说后记的交代,创作时也糅合了其他五名来华传教士的事迹,因而主人公大卫·特里达普更多是虚构性质的人物,不完全是作者生父的化身(小说另有一个叫洛斯库·赫西的人物,不过基本见不到他的身影)。同时书中也提到了众多真实的历史人物,从慈禧、袁世凯、康有为、梁启超,到陈独秀、胡适、毛泽东、周恩来。作者利用了许多档案文献,包括有关人士的日记、书信、报告等,它们分别收藏于基督教青年会的历史图书馆、哈佛的休顿图书馆和耶鲁神学院和纽约市的国际乡村重建学院,还参考了有关题材的著作。
美国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的传教活动,是中美文化交流史上的复杂而敏感的大事件。它始于清末,延续到解放初期,是两国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但由于鸦片战争后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宗教上的不同信仰,从一开始中国人就对它是抵触的,并激发了公开的冲突,一部近代史,大大小小的“教案”不断。随着民主革命的进程,我们在政治上采取了鲜明的反帝和反美的立场,而且这时确也有人披着宗教的外衣进行与教会身份不符的活动,就使我们更把它看成美帝国主义侵略的一部分,或文化侵略一的先锋。所以长时期来,美国基督教青年会在华的活动,被一概打成“反革命”,它的成员也不由分说被视为文化特务或反革命分子,受到镇压或打击。实际情况当然不如此简单。国内对这方面缺乏从学术观点进行的研究,西方学者却做了不少工作。如费正清编有《美国人和中国的传教事业》(哈佛大学出版社1974年版)一书,收有多位学者的论文;还有谢利·加雷特的《中国城市的社会改革者:1895年至1926年的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哈佛大学出版社1970年版)和更早保罗·瓦尔格的《美国新教1890年至1952年在中国的传教运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都是具有历史跨度的专门论著。赫西的《召唤》也是在费正清、史景迁等美国汉学家的建议、启发和帮助下写成的。小说出版于1985年,也许正是中美邦交在20世纪80年代走向正常化后,才提供了一个契机,让人们得以更全面完整地回顾这一段历史。
由于以上的原因,《召唤》可以算赫西最典型的中国主题的作品。“中国”从小说第一页就开始出现。小说从大卫·特里达普1878年诞生在纽约州盐河村的一个农场的那一刻写起,但又穿插进他在中国闻悉母亲去世时的回忆,想起自己造成的难产差不多在60年前就几乎谋害了生母。这成了叙述主人公来华前事迹的基本笔法——以他后来的第二故乡中国为聚焦点,他的思绪、牵念,书写的日记、信札,及对往事或清晰或模糊的印象,总是来自那里。
现实的动机
一个年轻的美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他的基本动机是什么?相信这也是赫西在缅怀父亲时深感好奇的问题。时代早已跨越了中世纪,不可能再有什么“上帝之声”之类的神迹,召唤只能来自人间。小说在这点作了多方面的追溯和探究,力图从现实的视野找到答案。
从赫西的描写中,不难发现,大卫·特里达普具有相当纯粹的美国血统和文化背景。母亲一系出自新英格兰的最早移民,是虔诚的加尔文教徒,祖上做过牧师和殖民地官员,也炒买过地产;父亲一系来自征服北美原始森林的那部分移民,他们在树丛中设陷阱捕猎动物,和印第安人过往亲密,因而弄不好大卫身上还有印第安人的血液(他本人也不止一次怀疑过),然后这些猎手又通过自己的枪支、威士忌和梅毒让印第安人变得“文明化”。在一个平凡的多子女的农场主家庭里,小特里达普除了吵闹声高和个子大,并无多少天生的异察,但却是个不安分的孩子。在学校经常暗地里捣蛋,是大大小小恶作剧的幕后策划者和制造者,甚至进了大学的头一年都是老样子,似乎他体内潜藏着过人的精力和不守规矩的种子,足以推动他在后来选择一条不同寻常的生活道路。
把特里达普引向传教使命的众多条件中,人文地理环境是另一先天性因素。盐河村位于著名的安大略湖东头不远处的平缓的森林地带,原是印第安人昂农达嘎部落(Onondagan)出没狩猎的地方,后来成了移民们西进路上的驿站,同时也是培养传教士的理想温床。特里达普本人曾这样写道:“我越来越彻底地意识到,伟大的美国人急于去丈量地球旋转的尺度。”第一代人是新英格兰,下一代是纽约州的西部,然后是老中西部,一直前进,似乎美国人天生要向西走。这种“命定西进”的观念,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被舆论界提升为“显然天命”论,鼓吹美国人由上帝赐予了整个新大陆,因而“对外扩张,占领整个大陆是显然天命”。同一观念也让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和他的追随者们得出了太平洋是“美国的内湖”的狂妄结论。在一代代人经由安大略湖东岸向西进发的印象中,特里达普憧憬着先驱者匆匆西行的尘埃的情景是不难想象的。
中学生活也很关键。家里人商量决定让他离开家乡到丢考特上文科中学,这鼓起了他的雄心。他日后回忆道:“我那天回到家里兴奋不已,我准备去征服全世界。”中学的卡特老师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导师,引发他学习外语的兴趣,培养他对思考、体育和美德的爱好,指点他阅读富兰克林的自传、柏拉图的对话录、色诺芬的回忆录、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富兰克林的自传成了他第二部圣经,这位建国之初的大政治家的奋斗一生为他树立了榜样。高中阶段又正好爆发了美国和西班牙争夺古巴和太平洋上海岛的战争,马汉以海军赢得世界强国地位的理论也喧哗一时。加上少年时代在农场的日常劳动养成了他勤劳而不辞艰辛的性格,叔父送的一条赛艇又使他很早就做起了海军之梦。虽然像所有的年轻人一样,特里达普的成长道路充满了不稳定、挫折、沮丧、低落和青春期的精神危机,但所有不同成分的交互作用,最终注定了他将一跃跨越太平洋而来到中国。
更决定性的转折发生在大学时代。在经历了一年级的种种不得意(包括考试不及格、向学校规章制度造反而受惩罚)和休学两年多后,特里达普在卡特的督促下重新回到叙拉库斯大学。他开始摆脱自身的弱点,并从教士们的布道中得到启示,整个人换了样。他克服了灵肉分离的困惑,热心公益活动,加入了基督教青年会,成了活跃分子,并当选为该大学分部的主席。当他毕业时,可谓前途广阔。基督教青年会允诺他可以在美国任何一个城市工作,校长挽留他在母校任教,牛津大学为他提供了奖学金,叙拉库斯大学有钱的校友提供给他三份不同的企业中的职位……但他不顾父母的反对,接受了去中国传教的任命。
这里有必要补充介绍一下基督教青年会的情况。基督教青年会于1844年创立于伦敦,几年后迁往美国和加拿大,其宗旨原是为了改进城市青年工人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状况,但很快传播到大学校区。由于也吸收女大学生参加,在大学里受到了普遍欢迎。1877年基督教青年会建立了由路德·维夏特负责的学院分会,在美国东部和中西部扩大组织和影响方面创下了纪录。它在大学里的作用颇接近后来的学生会,强调学生的自治和共济,组织学生们进行各项活动,帮助经济困难的学生参加勤工俭学,协助管理学生,解决他们的思想问题和道德问题,并出版自己的刊物。不同于学生会的是它有强烈的宗教背景,而且致力于国外的传教。特里达普所在的叙拉库斯大学本身就是卫理公会派的教会学院,各种宗教人士来此活动频繁。一旦特里达普放弃自己个性的芒刺,必然被其强大的势力同化。他的转变,就直接导源于他复学后参加的一次宗教性集会。他目睹了一名青年不满外来教士的宣讲,拔枪准备行刺又被宣讲者的镇定无畏所慑服的情景,也听到另一位教士说:“啊,年轻人,享受你们的青春吧!现在记住了,你们的造物主就在你们的青春岁月中。因为多数人受到他的召唤,只有少数人接受他的选择。”特里达普在写给自己看的《我的誓言》中说:“我听他平静地说了三句话,就此改变了我的人生。”
小说多少有点落入俗套地形容特里达普获得启示后的感觉:“大卫感受到了基督教圣徒们的热情洋溢的喜悦。他在叙拉库斯大学周围的乡郊久久徘徊着,只觉得要展翅飞翔。”但同时也点明,他的抱负、权力欲和别的欲求都在,只不过被调整和统制在新的心态之下了。事实上,特里达普也对某些布道反感,只是和那个准备枪杀外来教士的青年相反,他不满的是更正统更保守的清教教义。其中反映的,正是经过了18世纪中叶的“大觉醒运动”和19世纪初自由主义神学的“第二次振兴”的加尔文主义新教在美国的发展演变。它的特点是走向情感主义,使信仰变为个人情感的事,让人的命运更多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而不是像严酷的“选民论”主张的由不可知的上帝预定,从而适应了美国人的个人意识,和世俗世界达成了妥协。特里达普所接受的宗教信条正好就是乐观而自信的卫理公会派的教义,相信有一个可爱的上帝在吁求男人和妇女的自由意志,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将因此获得救赎。他曾摘录过“大觉醒运动”中著名的爱德华兹牧师的一次布道,发表评论说:“我们的人民感到他们甚至能够和上帝一起玩耍。”
与此同时,19世纪和20世纪的美国清教也出现了新的因素。一是受英国清教徒的影响,认为千禧王国虽然遥远,但基督已重返人世间为这王国的实现做准备,所有基督的信徒也应加紧努力;二是年轻的教会领导人在宗教活动中增加了人道的成分,推广救济穷人的工作。这些都推动基督教青年会的成员,积极地试图通过拯救灵魂和更实际更广泛地帮助落后国家和地区的人民,为千禧王国的降临扫清道路。为此,基督教青年会于1888年创立了大学生海外传教志愿者运动。特里达普曾两次单独会见该运动的负责人詹姆斯·托德,正是在后者鼓动下,他志愿做一个远赴海外的传教士。而之所以选择中国,大形势是由于当时的美国正追随在列强之后,急于染指中华帝国的实际利益。基督教青年会也把注意目光投向了中国。一次大学生海外传教志愿者运动的集会上,发言人甚至说,新约中保罗致罗马人书就已列举了异教徒中国人的罪责。特里达普本人则从归国的女传教士索菲亚·洛克关于戊戌变法的报告中,萌发了积极投身中国改革事业的最初冲动。
通过以上描写,小说相当令人信服地展现了一个普通的美国青年踏上海外传教之路的轨迹。他并非天生的圣者,也没受到某种神迹的启悟。他的个人雄心、对权力的追逐和各方面的能力,经过和周围环境的冲突和自我调整后,正好在一个卫理公会大学的宗教氛围里,在基督教青年会为他提供的舞台上得到了充分的施展。而基督教青年会的信条和原则,又影响和引导他走得更远。他既是美国那种不断扩张的西进观念和以拯救与纯洁世界为己任的清教文化的共同载体,也是一个企盼在国外建功立业、有着自己的喜怒哀乐和青春梦想的大学毕业生。个人的动机和文化的动机就这样奇妙地混杂在他身上。而建立于大量文献资料上的追溯,正是为着提供一份翔实的证据,以证明一种思想文化的传播,即使是宗教信仰的传播,也并非想象中的光之源的直线照射,相反掺杂了许多个人的动机和微妙的偶发事件。
嫁接和渗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