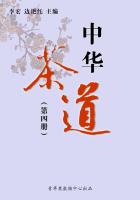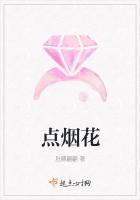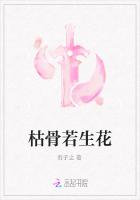如果说福克纳和苏童从一开始就抱着对现代文明的批判态度,力图从昨日的世界找到振起人类精神的素材,贾平凹却是从当前农村生活的新变化,又一步一步转向对过去的探视的。这个转变过程,本身就十分耐人寻味。我们发现在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说中,有一个时序递减的现象:创作时间越靠后,其时代背景越古老。80年代初期的商州故事,如《小月前本》(1983),《鸡窝洼的人家》(1983),《腊月·正月》(1984)等,作品的时间背景基本是与时代同步的,可是随后的小说,如《五魁》(1990),《美穴地》(1990),《白朗》(1990),《晚雨》(1991)等等,故事发生的时间却与现代越来越遥远。作者的态度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早期商州故事中的主人公王才、门门、才才、烟峰,无不是以农村改革者锐意进取的现代精神而被作者大加颂扬,可是到了《故里》(1986),我们发现作者的态度开始渐渐暧昧起来。
这部小说延续了前期商州故事的一贯主题,描写山民赵一仁全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生活变化。赵一仁当了十几年的堰长,德高望重,是玄虎山古老秩序的维护者,一种特殊的权利象征:
堰长虽然不是社长,亦不是生产队长,但它是天人合一的象征,其权力为惟德是馨的体现。堰长有专门的房子。即使这一年五谷歉收,他也有绝对保证的粮食。他有独自使用的铜锣,锣一响,庄人就得招之即来。而他决定给谁家放水,就给谁家放水,旁人不能闲言碎语。黑河水如若暴涨,冲毁了水渠堰,抢修时,堰长则必须挺身而出,第一个下水,死而不惜。
但在新一轮民主选举中,一个年轻人接替了堰长的位置。赵一仁的落选固然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而在家庭成员间这种变化早已不知不觉地开始了。几年前,二女赵怡嫁进省城,成了作家夫人,被家人引以为傲。小妹赵良进城跟二姐生活了一段时间,就想找一个城里人结婚,变得高不成低不就。其他的几个兄弟,也都不甘心像父辈那样种地过日子,纷纷卷人时代风潮,有的开厂,有的挖龙骨。生活的富裕并未给这家人带来预期的幸福。相反,由于经济实力的差异,兄弟间产生了隔膜与矛盾,婆媳亦无法和睦相处,家庭四分五裂。大儿子赵和顺应着社会潮流,停薪留职开办了一个培育蘑菇的加工厂,与妻子顾玲玲一同经营,迅速致富,成为县城知名企业家。他忙着在县城办厂赚钱,竟连老父病重都不愿回家探望。他的妻子顾玲玲倒是回来了,却带回一身新学得的城里人的虚伪与矫情。二儿子赵玄情况更糟,他靠挖龙骨发了财,就喜新厌旧,在外花天酒地,回到家中对妻子百般挑剔,拳脚相加。他口口声声叫嚣:“怎么着,我有钱嘛!”把妻子折磨得精神失常,搞得全家鸡犬不宁。曾经在玄虎山一言九鼎、语出令行的赵一仁,如今却对儿子毫无办法,只得长吁短叹:
都是钱害了人的德行啊!要是这几年还像往日那么穷,什么事都没有了!那年头,谁家有个什么事,乡里乡亲的谁不帮忙!现在呢,哪家死了人,抬棺材的人都叫不齐!从早先对农村现代化欢欣鼓舞表示乐观,到忧虑和批判意识占据上风,是贾平凹创作态度的明显改变。随着社会转型的加速和现代化程度的深入,经历了现代文明猛烈撞击的古老农业社会发生了更深层次的裂变,固有的社会秩序和道德伦理观念土崩瓦解,由此引发的种种现象是人们所始料不及的,而其中令人感触最深的莫过于农村人纯朴天性的丧失,这在贾平凹是刻骨铭心的。《商州再录》一文写下了他的直观:“……这次商州之行,亦有不同儿时在商州,甚至不同前年去年去商州,觉得有一种味儿,使商州的城镇与省城西安缩短了距离,也是山坳沟岔与平川道的城镇缩短了距离。这味儿指什么,是思想意识?是社会风气?是人和人的关系?我又不能说准,只感到商州已不是往昔的商州。这不免使我愤怒。静心思索,又感到,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些山民既保存了古老的传统遗风,又渗进了现代的文明时髦,在对待土地、道德、婚姻、家庭、社交、世情的诸多问题上,有传统的善的东西,有现代的美的东西,也有传统的恶的东西,也有现代的丑的东西。”
但在传统和现代的美与丑之间,贾平凹还是本能地选择了传统,将审美视野投向了过去的商州,结果便是《五魁》、《天狗》、《古堡》、《黑氏》等系列作品的诞生。在这个独特的系列中,故事的时代背景被有意忽略,生命的存在虚化了具体的时间形式,但读者可以明显感受到一种刻意营造的古老氛围。比如《天狗》,从人物的言行不难推断故事大约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但小说介绍故事发生地时故意强调了古老的称呼“堡”,并作了一番渲染:
之所以称作堡不称作村,是因为早年这一代土匪多,为避祸乱,孤零零雄踞在江边的土疙瘩振上。人事沧桑,古堡围墙早年就废了,堡门洞边的荒草里仅留有一碑,字迹斑驳。暮色里夕阳照着,看得清是“万夫莫开”四字。居家为二百余户,皆秦地祖籍,众宗广族却遗憾没有一个寺庙祠堂。虽然仍有一条街,商业经营乏于传统,故不逢集,一早一晚,安安静静,倘有狗吠,则声如巨豹。
这样一个虚构的古堡,就是作家用来抵御现代化潮流的最后据点。事实上,贾平凹曾一度指望商州这块和昨日世界有更多血缘和纽带的土地能提供一种活力,来疗救现代人日益疲软的精神状态和现代社会普遍下滑的道德水准。长篇小说《商州》(1984)一开篇,我们的主人公就在寻思——
商州和省城相比,一个是所谓的落后,一个是所谓的文明,那么历史的进步是否会带来人们道德水准的下降而虚浮之风的繁衍呢?诚挚的人情是否还适应于闭塞的自然经济环境呢?社会朝现代的推衍是否会导致古老而美好的伦理观念的解体或趋向实利世风的萌发呢?他回答不了,脑子里一片混乱,只直觉感到在这“文明”的省城应注入商州地面上的一种力,或许可以称作“野蛮”的一种东西。
但如今,残酷的事实却是,商州这个最后的营垒也已四分五裂,似乎逃不掉被现代文明所吞噬的厄运。怎么办呢?贾平凹惟有将他无穷的感慨、无限的眷恋,投射在越来越快地退向后方的过去的一连串幻影上。
人和历史
尼采在《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一文中谈了一种见解:人们需要历史的服务,但历史的意识必须有一个限度,一旦超越,凡生者就要走向损害之途,最后归诸沦亡,不管这生者是一个人、一个民族、还是一个文化。原因在于,“历史的意识,如果它不被约束地支配一切,而贯彻到底,它就根绝了将来,因为它破坏幻象,夺去现存的事物的气氛,而这些事物只能在这气氛里生活。历史的公正,纵使真正以纯洁的意识去行使,它也是一个可怕的道德,因为它总是消损生者而使之衰亡,它的裁判永久是一个毁灭。”尼采的话显得深奥、不易理解,其实他点破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历史本身是由人创造的,人们不必过分拘泥于历史来束缚自己的创造力。
处在新旧转型期的一大困惑,就是历史遗产和个人创造之间的两难。面对着历史的巨大阴影,我们还可能走出一条新路吗?然而,如果不超越历史,又怎么可能通向未来的彼岸?
正是这一点构成了福克纳笔下不少人物的悲剧命运。昆丁·康普生、盖尔·海托华、艾萨克·麦卡斯林……这许许多多不幸的南方后裔,莫不是泛滥决堤的历史意识的牺牲品。
从许多方面来看,昆丁也许是康普生家族仅存的几个后代中最优秀的一个。他和父亲一样,继承了祖先广博的才智,保持了旧世家代代相传的文化修养和道德品质。和他那冷酷无情的兄弟杰生恰恰相反,他的情感世界极为丰富,对母爱、亲情和爱情有着强烈的向往。但是他却成了康普生家最彻底的失败者,年轻轻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剥夺了他生的希望的,正是一种过度膨胀的历史意识,过去就像一个无法摆脱的梦魇始终缠着他。在《押沙龙,押沙龙!》中,我们看到他生活在20世纪的大学校园,可他的全部注意力被一个五十多年前的故事所占据。他身临其境般体验着祖先的光荣与梦想、痛苦与失败。他掩住耳朵,不想听到罗莎小姐死气沉沉的声音和父亲的唠叨,可还是一步步陷进汹涌如潮的往事回忆,无力抽身,因为——
昆丁是和这传统一起长大的;光是那些人的名字就是可以互相换过来换过去而且几乎是无穷无尽的。这些名字充塞了他的童年时代;他身体本身就是一座空荡荡的厅堂,回响着铿锵的战败者的名姓;他不是一个存在、一个独立体,而是一个政治实体。他是一座营房,里面挤满了倔强、怀旧的鬼魂,即使在43年以后,这些鬼魂也仍然在从治愈那场疾病的高烧中恢复过来,从高烧中清醒过来却居然不清楚他们与之抗争的正是那高烧本身,而不是疾病,他们那执拗、倔强的眼光回头越过高烧去谛视疾病,并真的感到遗憾,高烧使他们虚弱,但是疾病却被摆脱了,他们甚至不明白这自由其实是一种无生殖力的自由。
可悲之处就在于,昆丁“人还年轻,还不到应该做鬼的时候,不过由于他出生长大在南方边远地区,他仍然不得不做一个鬼”,他和他体内那些鬼魂一起承担着南方沉重的历史。战败是一场致命的疾病,是他们心头永远的伤痛,靠着对一个并不存在的辉煌过去的回忆,他们摆脱了疾病,可是回忆本身却像高烧,使他们虚弱,陷入一种“无生殖力的自由”。这一切压得昆丁喘不过气来,他不仅丧失了未来,也失去了现在,他唯一拥有的是过去。在昆丁眼里,过去无所不在,就连哈佛大学的校舍在他的叙述中也散发出一种阴森森的鬼气:
我们房间的窗户黑漆漆的。宿舍入口处阒无一人。我是贴紧左边的墙进去的,那儿也是空荡荡的:只有一道螺旋形的扶梯通向阴影中,阴影里回荡着一代代郁郁不欢的人的脚步声,就像灰尘落在影子上一样,我的脚步像扬起尘土一样地搅醒了阴影,接着它们又轻轻地沉淀下来。
于是,昆丁的存在就这样被规定了——他沉溺于过去,丧失了面对现实的能力,幻想中的家族荣耀和现实中无可挽回的衰败命运的强烈反差撞击着他原本就脆弱不堪的精神。而这一切,无从改变。我们忘不了他砸坏自己手表的绝望的举动,他想以此取消时间,因为历史正是时间构成的。但就像他迅即领会到的,时间的存在是什么手段也否决不了的。当他得知妹妹凯蒂失身,败坏了他视若生命一般宝贵的家风时,最后的精神支柱——家族荣誉感轰然倒塌,他只能选择自杀,来停止历史对他的折磨。
另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八月之光》中的海托华牧师。这位牧师从神学院毕业后,拒绝了所有职位,一心一意来到杰弗生镇。但他这样做“不是为这儿的教会和会众服务”,“他不关心别人,活着的人,也不关心他们是不是乐意接受他”,他之所以执意要到杰弗生镇来的真正目的只有一个——因为这里是他最最崇拜的祖父、一个南北战争时期南军骑兵最后捐躯之所。海托华一到杰弗生镇便兴奋异常,四处夸耀祖父的功绩,“半年之后这位年轻牧师仍然兴奋不已,还在谈论南北战争和他的祖父——一个骑兵,在战争期间被杀害,以及格兰特将军的军需物资在杰弗生镇被烧毁的事情,直到他的老生常谈叫人听来毫无意义。”“他似乎把宗教、奔驰的骑兵和在奔驰的马上丧生的祖父混在一起,纠缠不清,甚至在布道坛上也不能区别对待。”他一走上布道坛,便“双手挥舞,情绪激昂,声音震颤热切,在这如痴如狂的声音里,上帝、救世军、奔驰的战马、他已故的祖父都像幽灵般狂呼乱嚎,坐在坛下的长老们,全体会众,都感到莫名其妙,愤怒不已。”人们猜测“也许在他家里,在他的个人生活里,这些事儿也搅成一团”,牧师妻子的几次出走证实了这一点。他的教众从他这里得不到任何帮助,都开始讨厌他,而他的妻子由于无法忍受丈夫的冷落,与一男子私通,败露后自杀身亡。妻子死后,他被教会逐出,按说他应该立即离开这个带给他伤心回忆的地方,“但是他就是不愿离开这个城镇”,这使镇上所有居民都大惑不解,有人同他做了一番深入的交谈,找到了症结所在:
那是因为一个人宁愿忍受原来的困境而害怕遇到新的麻烦。在冒着风险寻求改变之前,他乐于逆来顺受。不错,人人会说他希望逃离活着的乡亲,但真正危害他的是死去的亲人。死人静静地躺在地下并不想作弄人,然而任何人都逃脱不了死者的阴影。
海托华着魔似的追随历史的幽灵,耗尽了全部的生命能量,“因为他总把宗教和他祖父在奔驰的马上中弹身亡的事儿混在一起,仿佛那天晚上他祖父传给他的生命种子也在马背上,因而早已同归于尽;对这颗生命种子来说,时间便在当时当地停止了,此后的岁月里,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甚至连同他在内”。他失去神职后为自己找工作做的招牌广告上写的“D”“D”(英文“神学博士”Divine Doctor的缩写),也完全可解读为“被神诅咒倒霉的人”(Divine Damned)。
在苏童的小说创作里,同样反映了人面对历史的困境。《罂粟之家》里的三四十年代的枫杨树,像福克纳笔下的美国南方一样,是一片美丽然而受到诅咒注定要灭亡的土地。当地的一千户佃农靠租土地种植罂粟为生,这片土地的拥有者是地主刘老侠。他不择手段兼并了河两岸所有土地,甚至连亲兄弟刘老信的坟地也不放过。他跑到妓院,找到因性病全身糜烂、只剩一口气的亲弟弟,威逼其沾着手指上的脓血按下地契卖掉坟地的一幕,带着强取豪夺的全部肮脏和血腥。从此一年中有半年时间,枫杨树乡村的土地上开满鲜艳的罂粟花,邪恶的气息久久不散。
刘老侠肆无忌惮的个性也体现在私生活方面。父亲没死之前他与父亲的姨太太翠花花有了苟且之事,父亲一死马上就将她占为己有。由于“血气旺极而乱”,刘老侠的前四个孩子都“像鱼似的没有腿与手臂,却有剑形摆尾,他们只能从水上顺流漂去了”。第五个孩子叫演义,是刘老侠与翠花花“野地媾和的收获,那时候刘家老太爷尚未暴毙,翠花花是他的姨太太,那时候刘老侠的前妻猫眼女人还没有溺死在洗澡的大铁锅里,演义却出世了”。演义虽是唯一幸存的孩子,却是个白痴,整天只知道叫:“我饿,我要吃摸!”除此以外,他还对每个人都抱有深切的恨意,因为人们怕他会吃光家产而不让他随心所欲地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