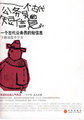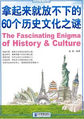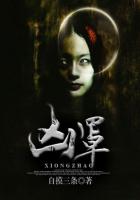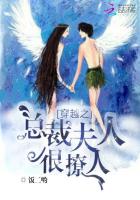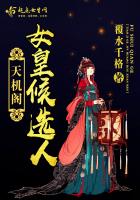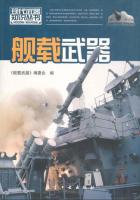郑:民族情绪与科学态度,这又是一对有趣的概念。其实,文学批评或文学研究的科学性为别的东西所左右,导致文学家及其作品几经沉浮的现象,古今中外都有。曾几何时,我国的日本文学研究界对日本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极尽批判之能事,说其作品“寄托着作者颓废没落的思想感情表明资产阶级文学陷入日暮途穷的境地,具有极大的毒害作用”;指责川端的《雪国》写的是“男女间猥亵的狠行径”,颓废主义和“下流情调”,他的《千只鹤》写的是一个纨绔儿的通奸;这是中国同样权威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外国名作家传(上)》的原文。可是时过境迁,20年后,川端文学的意义和价值得到完全不同的评价。他的成功被誉为是“传统文化精神与现代意识的融合”,“传统的自然描写与现代的心理刻画的融合”,“传统的公正性与意识流的飞跃性的融合”(叶渭渠、唐月梅译:《雪国,古都,千只鹤》“序”,1999年)同样国外文学研究界也不乏这种现象。日本女诗人与谢野晶子(1878—1942)著名的“新体诗”《弟弟哟,你切勿去死》大起大落的批评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弟弟哟,你切勿去死》发表于1904年,原是与谢野晶子写给其弟弟的。当时日俄战争正进入关键的中国的旅顺港争夺战,传说不少日本兵志愿成立敢死队,誓死要从俄国军手中夺取旅顺港要塞。因惮于自己血气方刚,容易冲动的弟弟不顾家中老母、新婚的妻子和家中糖果店生意参加敢死队,与谢野晶子作此诗劝阻弟弟。当时正值日俄战争的决战阶段,日本国内支持战争的呼声极其高涨,诗歌发表后不仅被批评家们骂为“辱君叛国”之作(因诗中写有天皇自己不上战场的话),甚至还有一班市民向诗人家房子扔石头表示义愤020多年后,在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处于高潮时期,《弟弟哟,你切勿去死》继续从相反的方向受到批判,说是该诗汲汲于老母娇妻,没有追究战争的真正根源并与其作斗争;诗歌斤斤计较于家中的生意暴露出诗人“资产阶级世界观”。战后的《弟弟哟,你切勿去死》虽然仍遭一部分批评家批判,但总的来说该诗得到正面的评价,被誉为日本最佳的反战诗歌,表达了民主主义精神,并曾几度被作曲家谱成曲,在战后的学生运动中被广为传唱。20世纪70—80年代以后,《弟弟哟,你切勿去死》更被奉为女权运动的先声。1972年大阪一位妇女甚至将《弟弟哟,你切勿去死》的文字缝到即将捐给外国的门帘布上,以鼓励和促进反战运动。
张:民族情绪并不限于某一个民族,它同样具有普泛性。从根本上说,它是文化交流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种文化保守主义,根源于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和坚守,目前是在全球化过程必然激起的一种反应。所有不同类型的文化中心主义实质都是民族情绪的产物。在反对欧洲文化中心主义的同时,很容易让别的文化中心主义取而代之而不自觉,这一点,应当有清醒的反思。对我们而言,华夏中心主义在历史上同样根深蒂固,称为“中原”,称为“中国”,就是最典型的表征。这样的一种民族情绪,在一定程度内是合理的,对本民族的自强自立有积极的作用,但推而广之到学术的研究上,就会出问题。学术研究需要的是科学、冷静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它追求的是知识的可靠性和确证性。不客气地说,在文化发展论上的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轮流坐庄”说,就不能算是科学的预测,而只是民族情绪的流露。
郑:刚才我提到美籍华裔作家谭恩美和汤亭亭。我注意到大作中还讨论了其他美籍华裔作家。不知张先生是如何定义“美国作家”这一概念的?既然大作是研究美国作家与中国文化的,你认为这些美籍华裔作家应占有怎样的地位?
张:只要考虑到这些华裔作家先后加入了美国籍,就不应该将他们排除在美国作家之外。事实上,所谓的华裔美国作家或范围更广的亚裔美国作家,正作为一个特殊的创作群体日益引起海内外学界的关注。对他们的看法,过去还有个语言的问题,即不用英语写作的算不算美国作家?近来这个语言的界限已被突破。台湾《中外文学》第29卷第11号早就报导过,美国学者威尔纳·索罗斯(Wemer Sollors)在20世纪末主编的《多语言的美国》(Multilingual America)中,主张只要用在美国境内使用的语言创作的作品就应该算是美国文学,相反如果只局限于英语,反而会导致美国文学和文化的贫乏。用这个标准看,不管是用汉语写作的(如严歌苓)还是用英语写作的(如哈金),毫无疑问都应列入美国作家。这其中还有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这些华裔美籍作家兼有双重的文化身份,他们作为中美文学和文化交往的媒介往往发挥了一般作家难以发挥的独特作用。像小说家赫西,也是因为他父亲就是来华的传教士,他本人在天津出生,他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来过中国,才能对文化交流和影响的实际过程有如此生动深刻的体会。研究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学的关系,理当将他们包括进来。
郑:与“美国作家”的定义相关联的是留学生文学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开始,大批中国留学生源源不断地去了美国。今天,其中很多人已经在美国开创了自己的事业,融入了美国社会。在异国他乡创业并融入美国社会的过程虽然有着成功的喜悦,但往往是伴随着难言的艰辛和痛苦,同时又伴随着不同价值观的冲突和较量,对故国的依恋和“去留两难”的选择,不少人还不断经历与在美国出生成长的下一代之间“不同脉冲的撞击”。所有这一切都在留学生文学中得到真实而生动的反映。
留学生文学中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纽约》因其在国内被改编成电视剧而最为著名。可是除了曹桂林外还有很多热衷于创作的留学生作家,其中最多产影响最广泛的也许是少君。少君,真名钱建军,1960年在北京出生于一个军人家庭,曾参加过1976年的“四五”天安门运动。1978年,少军考入北京大学,攻读生物物理专业,毕业后曾在《经济日报》、《经济学导报》任记者,并参与过中国政府的一些重大经济决策活动。1988年,他在人生得意之时毅然抽身赴美国德克萨斯州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以后,少君担任过美国匹茨堡大学的副研究员、普林斯顿大学研究员,以及TII公司副董事长等职。此外,他还兼任中国华侨大学和厦门大学教授。从1991年起,少君在因特网上发表了据认为是全球第一部中文“网络小说”《奋斗与平等》。从那时起,少君一发而不可收,连续在网上发表了诗集《未名湖》、小说《上帝保佑》、《大陆人生》、《活在美国》、《活在大陆》等,并分别在大陆、台湾和美国结集出版,可以说是留学生文学中最杰出的代表。按照索罗斯“只要用在美国境内使用的语言创作的作品就算美国文学”的主张,这些作品显然应归入美国文学。不过这些作品的场景虽一般都设在留学所在国,却一律用中文写成,而且主要以中国人包括广大留学生、国内读者为时象,也有部分作品以美国华人社区为对象。此外,留学生文学一般是首先在网络上发表的,取消了出版、发行和销售等环节,同时也意味着留学生作家毫无例外地是兼职而不是职业作家,不以挣稿费为目的(至少发表之初如此)。因此,留学生文学与传统意义上的美国文学是很不一样的。我认为以少君为代表的留学生文学一方面会为北美的华人文学创作做出自己的贡献,另一方面也会给大陆的当代文学带来新鲜的养分,提供来自异域的文学风景和不同文化意识的碰撞、交融的可贵的参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留学生文学既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中特别的一页,也是美国文学中特殊的一页。在全球化日益推进的当今世界,我们也许应该另立一种门类以便更加科学、准确地反映留学生文学这种新的文化现象。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张:郑先生说得很对,留学生文学是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其实从清朝末年开始派遣官费生以来就有了,应该给予特殊的关注。不过留学生文学有一个很大的特点,那就是流动性创作队伍不固定,作品也缺乏连续性,这是和留学生的身份不断在变化,创作又往往是自发状态的有关系,很多人留学生涯结束后也就中断了这方面的写作。像少君这样的情况是较罕见的,国内似乎介绍得不够,热诚希望郑先生借着在美国讲学和做研究的得天独厚的条件多给我们一些信息。
郑:在中外文学或文化关系研究的领域张先生今后的课题是什么?能够透露一点情况吗?
张:学海无涯,我只取一瓢饮。这不仅是个主观取向的问题,也是个客观条件的问题。有很多愿望或打算,未必全都能变为现实。等手头一些工作结束后,如果允许,我很想将吴宓作为一个个案,探讨一下他在中外文学和文化交往史上的经历、遭遇、贡献和地位。我感觉他在这些方面都是相当独特的,从中也可窥见中国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在文化思想和文艺审美方面的不少东西。更多的希望,还是寄予后来者,热诚期待有更多年轻的学人加入中外文学与文化关系研究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