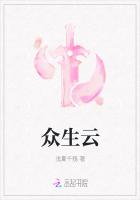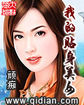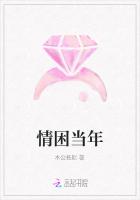张:谈到形成过程,可能复杂一点。首先应该说同生活经历或个性有关吧。我生长在上海,大学毕业后到了东北,在海滨城市大连又工作了12年,差不多每次回老家探亲都乘海轮从海路走,从小热爱海洋,那种惟有在海上才能体验到的天风海啸、大气磅礴的动荡感,是我很久以来就深深挚爱的一种意境。自识字始,我又喜欢历史,到东北林区还是“文革”期间,没有书看,差不多把当时特准继续出版的标点本“二十四史”读了个遍,厚重的历史让我明白一切都是在发展变化中的。有以上的基础,“文革”结束考上研究生后,在学习艺术哲学的过程中,就很自然地接受了尼采所阐释的古希腊阿那克西曼德的“不定者”(apeiron)范畴和赫拉克利特的流变哲学,相信万事万物皆在变化的动态中。中国古代的贤哲感叹的“逝者如斯夫”,把握的也是这样一种永恒的动态。但在我学术生涯的开始阶段,我仅是将这样的动态观运用于文学和文学史的研究中。20世纪90年代中国掀起了“文化热”,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新权威主义、新左派等各种文化主张先后都出现了,当时我隐隐地感到问题的所在,是这么多的主张都未曾将中国文化看成在不断发展中的过程。比方有一个相当流行的说法,认定五四是中国文化的断裂层。试问从哪里断裂?难道中国文化就是在五四以前就已定型的那么一个固定不变的东西?难道五四时期和五四以后中国人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就不属于中国的文化?当然,完全不妨对五四的功过得失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但认为那就是对中国文化的破坏与中断,无疑是一种典型的静态观。当时我写了一些文化随笔,谈了自己的观点,而卷入的较大规模的论争则发生在我从事的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国内有人受后殖民主义思潮影响,指责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者患了“失语症”,只会用西方的术语、概念翻译介绍外国的东西,充当了后殖民的“文化贩子”。这再一次让我见识了静止不动的观点的影响之广与深。在那些激烈的言辞背后,包含的是那么一种见解,否定文化需要发展并且实际也在发展,发展过程中会吸收其他不同的文化成分,同样也否定语言也在发展,否定现代汉语在形成过程中虽吸收了西方语言的语法和构词因素却永远不可能使它变质为外语的事实。争论在外国文学研究的权威刊物《外国文学评论》上展开,双方都写了大块文章发表,中国文联的机关刊物《文艺报》也专门作了报导。从那以后,我的“文化动态观”正式确立。可以说,这一观点的成形是中国当代的文化现实状况促成的。至于文化学上的渊源,当数美国著名女学者罗斯·本尼迪克特(RuthBenedict)《文化模式》一书提出的动态的文化整合论。她是杰出的人类学家博厄斯(FranzBoas)的高足,研究北美印第安人部落文化,虽不是理论家,书中根据实际调查得出这个结论在学界却影响极大,那本薄薄的书自1935年问世后被译成了14种文字。讲到底,“动态文化交流观”是“动态文化观”的一个派生或进一步发挥。
郑:具体而言,动态的文化观或文化交流观有哪些要点呢?
张:我尽量说得通俗明白些。
第一,文化并不是某种现成的固定不变的东西,它虽然表现为历史的积淀,但也是人类正在进行中的创造。这点很重要。人们往往看到了文化对人类行为的制约,但忽略了人类的行为对造成一定文化的主动或能动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人类会不幸地沦为既有文化的奴隶,不思进取,抱残守缺。那是很危险的。
第二,文化是在动态中存在的。一种文化总是处在和其他种文化的接触和交融中,同时内部也由于那些外部因素的加入而不断处在活动之中,因差异而产生对抗,因对抗而产生活力,并因而取得自己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在此意义上,可以认为没有文化交流就没有文化的存在。
第三,一种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或采纳不是简单的拼接,而是出于自身目的的有机化的融会和整合。这一融会和整合完成后,新的文化因素会表现出来,但本土文化的总体并不因此丧失它自己的属性。这个观点主要是本尼迪克特的,但就我所见,她没说清楚文化的自身目的是什么,给人哲学上的目的论的印象。我想指出的是,这个目的其实就是创造这一文化的人民的生存与发展。
第四,文化交流的实际过程,是多向度、多维度的,这不仅因为文化本身的构成是多元多维的,也不仅因为两种或更多种文化遭遇在一起时会互相有反应,也因为作为文化载体的人,他的行为和活动及其动机也是极其复杂的。实际上最终导致文化的交流的,是多种力量的作用的合成。还有一点我要补充,即我们在谈论文化与文学的关系时,也应注意双方的动态性,并不只是文化在影响文学(照有的人的说法是“文学充当了文化的载体”),文学本身同时也在创造文化。
郑:这是文化和文学交往中的互动关系,书中述及美国意象派诗歌受唐诗的影响,但意象派诗歌又促进了中国诗学的意象论的发展,就是个例子吧?
张:是的。提倡动态的文化观,也包括用动态的观点来看待和处理文化和文学的交往和交流。当某种影响过程发生时受到作用的绝不止于受影响的一方,通常所谓的“影响源”也会受到反作用。即便如此,这种互动关系也并非你影响我、我反过来又影响你就足以概括了。不是的,不能简单地想象成仿佛两个杯子的水,你倒给我,我再倒给你;要是这样想,会落入另一种简单化的模式。如果一定要打比方的话,那么它更像物理学上的弥散现象:一滴墨汁落入一杯水中,然后慢慢地扩散开来,边界不定,形状不定,水变黑了,墨汁也变淡了。
本书中有一章介绍美国作家约翰·赫西(John Hercey)的一部小说《召唤》(The Call),很能说明问题。小说主人公是位传教士,试图用西方的神学启蒙主义和科学主义影响中国的上层人物和普通民众,在这过程中他同时受到中国古典文化和康、梁改良主义思潮的影响,又遭到美国教会内部的新教原教旨主义和其他美国来华人士的殖民主义的排挤,结果他背弃了自己的宗教信仰,转而信奉人文主义,并真诚地在华北农村推行扫盲和农业改良工作,愿意尽毕生之力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然而最终,他还是被新政权宣判有罪,驱逐出境了。在这位传教士身上,不同文化倾向的矛盾斗争写得十分生动,既有外界环境代表不同利益和不同意图的各种势力,也有个人内心的复杂和矛盾的动机,相互交织相互纠缠,充分反映了文化交流的复杂程度。
郑:你提出一个民族的文化,始终在继续不断地生成和演变中。这一点非常有启发性。
张:不错。千万不能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已经固定不变,似乎经过多少年的发展后就已经定型、定格、定性,变成了凝固不变的某一个实体。现在许多人谈论中国文化,仿佛就是五四以前或鸦片战争以前就已固定下来的那点东西,而在那以后,就没有文化的发展了,有的只是文化的破坏。他们心目里的中国文化,其实只是中国文化的古典部分。由于缺乏文化的动态观,而抱着一种文化的静态观,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现代部分,对中国文化一个半世纪来的进展竟然能够视而不见。在我看来,这真是一种非常奇特的、令人难以理解的现象。在目前我所能见到的有关中国文化和外国文化或文学的关系的研究成果中,基本上都恪守这一信条,所谓中国文化对外国文学的影响,说到底其实只是中国古典的文化的影响,包括前面提到的刘岩那本著作也不例外。这种观点的背后,还有狭隘的民族情绪在作怪。在许多人看来,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只是一部屈辱史,这以前的祖上的业绩才称得上辉煌,影响外国的也只有靠那些古典或古董;不能不说这种民族情绪妨碍了我们在文化研究中坚持一种科学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