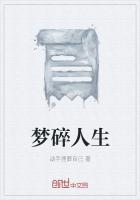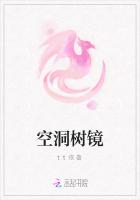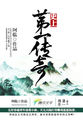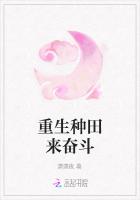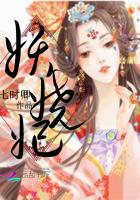经过两宋、元、明几代的发展,理学内部早已派别林立,有以张载为代表的客体理派,有以陆九渊、王阳明为代表的主体理派;而以二程、朱熹创立的绝对理派,在“道统”正宗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上升为元、明之际的官方哲学和意识形态。到了明朝末年,由于统治阶级的土崩瓦解和自身学术生命力的有限,理学出现式微。清初大儒们在深历亡国之痛后,更是对理学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其中以王夫之最为卓越。王夫之是湖南衡阳人,生于明神宗万历四十七年(1619)。崇祯十一年(1638),他肄业于岳麓书院,其间师从吴道行,吴授之以朱张之道。从事抗清活动失败之后,王夫之隐居着述近四十载,专门从事对传统学术思想的研究和整理,通过解释和挖掘进而达到继承和重建,成为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也成为宋明理学的完成者、终结者。他学承张载,提出“循天下之公”、“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的政治主张,强调“理依于气”、“天下惟器而已矣”,“无其器则无其道”,主张躬行实践,知行统一,批判理学中出现的空洞、脱离实际现象。王夫之“以艰贞拄世变,维人极以安苦学”,他身上所体现出来的艰苦卓绝、百折不挠、自尊自强、博大精深,都可以称得上是前无古人的。尽管他的着作在他死后近二百年才开始广为流传,但他与后来湘军集团中的很多核心人物如曾国藩、刘蓉、左宗棠、罗泽南等,都存在着一定的师承关系。光绪十五年(1889)的进士孔祥麟,在《拟请从祀文庙折》中曾说“咸同之际,中兴将帅,半湘省儒生,其得力夫之之遗书者居多”,由此可见王夫之在湖南士人中的影响之大。王夫之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巨人,也是湖湘文化的杰出代表,他的治学精神继承了湖湘学派的传统,使“济世救民”、“经世致用”的学风再次宏扬于湖湘大地。
清朝入主中原之后,十分重视运用程朱理学进行思想控制,康熙皇帝不仅称“自幼好读性理之书”,还诏升“先贤朱子于十哲之次”,并且颁行了《性理大全》、《朱子全书》、《四书注释》,定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作为科举考试的必考内容,又让一大批理学名臣高踞于庙堂之上,使理学再次出现表面上的繁荣。作为湖南的学术中心和理学重镇,岳麓书院始终为清朝统治者所警惕和重视,康熙于二十六年(1687)御书“学达性天”匾额,乾隆于九年(1744)御书“道南正脉”匾额。清政权对书院的抑制和思想禁锢政策,并没有改变岳麓书院历代山长对“经世务实”学风的坚持和努力,特别以李文炤、王文清、罗典三位山长尤为卓着,正是因为他们对明体达用、坚持实学的提倡,才培养出陶澍、贺长龄、贺熙龄、魏源等一大批湘籍经世派人才。曾国藩、刘蓉、郭嵩焘他们自幼生长在这样有着千年积淀的湖湘文化氛围里,又于青年时期一起求学于岳麓书院,在他们身上都洋溢着浓郁的理学气息,打着深刻的湖湘文化烙印,承载着乡邦先贤的遗志,肩负着传续和发扬湖湘学统的责任和使命。
刘蓉生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比曾国藩小五岁,作为曾的挚友和湘军集团的重要成员,刘蓉的人生可谓是以书生领甲兵的典型,特别是他早年的生活经历,真称得上天马行空、洒脱高洁。如果没有参与曾国藩平定洪杨的这出勘乱大戏,相信他也会以文名留载史册。刘蓉是后世学者公认的桐城派古文学家,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他的名篇《习惯说》,知道他幼禀庭训,有一位识见远大的父亲。而且在《习惯说》里他强调“君子之学,贵乎慎始”,那么刘蓉本人的治学之初又如何呢?在这里我们可以通过他与曾、郭等人论学的书信,一窥堂奥,并顺便一睹他的炳然文采。
道光十八年(1838),刘蓉写信给在京城参加会试的曾国藩、郭嵩焘,说:“窃以为文也者,载道之器,济治之方,非特记诵词章之谓也。”认为文章的成就,在于能传道和济世,并不限于仅谈论词章的记诵。又说:
虽然,作者苟无所关系夫世道人心之故,则犹花草之美,锦绣之文,犹末也。有关系矣,而于治乱之本原无所见,风教之颠危无所持,是犹迂阔之论,影响之谈,犹陋也。
体之精,故用之宏。积之厚,故流之光。由是充之以学,养之以气,济之以才,根之于经以正其源,酌之于史以尽其变,参之于诸子百家以定其是非,夫而后其功可程,其旨初备,夫又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在这里,刘蓉谈了他对文章的认识,认为如果没有济世之心,不见治乱之理,就是毫无价值的俗文、陋文;又提到他的治学观点,认为治学贵在静默沉潜,体积养济,经史百家,循序渐进。
道光二十年(1840),刘蓉在写给郭嵩焘的信中说:
早岁涉猎子史,博求典故,所资者,记诵之余,所志者,词章之末,泛览累年,茫无所得,然后退而求之四子六经,才觉圣贤所示修己治人之道,不出于是。
年少时喜欢博览经史子集中的典故,但收获不大,除了一些空泛的记忆,就只剩下对文章华美的追慕,后经反思开始研究四子六经,才感到圣贤的道理,都蕴含在其中不会超出这里。
道光二十一年(1841),刘蓉又在给郭的回信中说:
故某尝谓学者苟有志圣贤之道,必先玩索四子六经,沉潜反复,既得其宏纲要领所在,然后求之百家诸子以辨是非同异之故,考之史册传记,以察治乱得失之归。权衡定,则取舍不淆。辨别明,则是非不谬。学问之道,无有要于此者。
刘蓉所说的“四子”就是“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六经”就是《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刘蓉在这里强调的治学观点,无非是治学要以明圣贤之理为首,而途径就是精读四子六经。那么圣贤之理又以谁为依归呢?当然是程朱。我们随便看一下他写给好友陈懿叔的赠言,就可以清楚。
他写道:
圣贤往矣,其言之着于六籍者可考而知。自汉唐来,学者辈起,然道裂言庞,述而明者卒寡。程朱出而六经语孟之旨灿如日星,苟有目者,皆得见焉,非其心体而躬诣之,乌能昭晰若是。
纵观刘蓉的一生,他都是一个坚定的程朱理学信仰者,而且对程朱的门户持守很严,斥陆王为“阳儒阴释之家”,淆朱紫而混雅正。不过在看罢他的文章和书信之后,我们往往得到这么一个观感,就是刘蓉是一个非常自负的人,他不畏服权威,有一种恃道卫道舍我其谁的气势。他崇信理学,认为穷理之学“正所以破拘挛之见,尽变通之妙也”,这种唯理是尚理学万能论的治学态度,不由得使我们联想到王阳明对待“心体”的态度,以及王学的流弊“束书不观,游谈无根”。这里固然有刘蓉的性格成分,但其中是否也与王学有些相似之处呢?
道光二十三年(1843),刘蓉在《复曾涤生侍讲书》中写道:
王氏之学,自明嘉隆时已遍天下,至今逾三百年。弟往岁尝读其书,亦恍若有得焉,以为斯道之传,果出语言文字之外,彼沾沾泥书册求之者,殆未免乎泽薮之见也。
盖迷溺于诐淫邪遁之说亦已久矣。困而有悔,始复检孔孟程朱之训,逐日玩索,乃粗得其所以蔽陷离穷之端。
原来刘蓉自有一番沉溺和钻研王学的经历,是研习王学的经验和教训,树立了他对程朱理学的坚定信念。这无疑也透露了刘蓉在治学之初,曾以王氏心学为圭臬,时间应该是在进岳麓书院以前,而所受之影响又有非其本人所臆度者,怪不得知他颇深的左宗棠在与人议论时不无偏激之语,“霞仙生平好论学,且好以宋之程朱轨辙自命,实则不得于言,勿求于心,告子、阳明一路人耳。”
刘蓉对待程朱理学的态度,也招来一些其他朋友的非议,比如,陈懿叔的弟弟陈广敷就批评他“寄程朱矮檐,执方隅之见,以囿天下,其道已隘”。郭嵩焘也劝他“宜博览群书,不当墨守一经以自囿”。但刘蓉不为所动,深信孔孟之道即是程朱之道,“其能深契孔孟之微旨,则于程朱其终合乎!”在刘蓉的心目中,程朱理学“本末兼赅,精粗备举”,是上可以安邦治国,下可以修身齐家的屠龙之术。至于理学家被指责为“平时静坐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刘蓉则以为那是因为没有得到程朱理学的精髓。他醉心于理学,但并不赞成那种静坐书斋,漠不关心国家大事的治学方法,他强调义理和经世的结合,强调学问的实用,将“时事、利病、规画、得失之故,莫不视为学问要切之事”,这也是湖湘“经世务实”的学风使然。
其实真正影响刘蓉对待程朱理学态度的另有人在,那就是大他九岁的同乡罗泽南。罗泽南早年受学于着名学者张正笏的第五子张眉大,师承可以直接追溯到王夫之,是一位坚定的程朱理学信仰者,刘蓉尊称他为“湖湘儒者之冠”
。两人相识于道光十八年(1838),“遂订交莫逆”,“书札往来,彼此规劝,考求圣贤为学之要旨,身体力行,至明且笃”。刘蓉关于理学的很多看法,就是来自与罗泽南的相互探讨和受他的影响。比如刘蓉认为“濂、洛、关、闽实衍洙泗之学,若子静、伯安窃禅旨,乱儒宗,不当在五子列”。而罗泽南则专作《姚江学辨》,认为“惟姚江良知之说,窃禅门之宗旨,乱吾儒之正道”,由此可见他们在“尊朱黜王”思想上的认同痕迹。从刘蓉身上我们不难发现环境、阅历对于一个人治学的影响,同时也不难理解湖南浓厚的理学氛围对于湘军集团成员们所产生的影响。
尽管纸上得来终觉浅,刘蓉年轻时所做的学问充满太多书卷气,又囿于地域、个人阅历等因素而有很大的局限性,但这并没有妨碍刘蓉的洞察力和他参与现实政治的热情。道光二十二年(1842)鸦片战争之后,刘蓉议论时政,认为“国家承平日久,武备废弛,集游手以充兵,擢纨袴以为将,既未尝经历行阵,通习兵机,一夫夜呼,三军股栗”。国家长期太平无事,军事荒废,招募闲散游滑之人入伍,提拔纨绔子弟做将,既缺少军事训练,又没有指挥经验,结果一有异常,就军心浮动惊恐万分。他认为“夫攘外之策,守御为先,久罢之兵,精练为上。今诚以养兵之费,为招募之资,既省军粮,复收实用,又且熟知地道,谙悉敌情,因其爱护乡里之心,以作敌忾从王之气,将何敌之不克,而何功之不成”。在这里,刘蓉想到的“民兵御敌”之法,颇有些游击战全民皆兵的味道。然后他又指出当时政治有五大危机:“一、吏治不廉而民生日蹙;二、由于贿赂公行而官箴日败;三、风俗日坏而人心日沦;四、由于吏治、风俗之弊,财用日匮;五、盗贼横行奸民日众”。这些都不失为远见卓识之言。咸丰二年(1852),罗泽南的弟子王錱协助湘乡知县朱孙贻操办团练,刘蓉亦加入其中。从此之后,他先后出入曾国藩、骆秉章幕府,并且亲自领兵打仗,这些实际活动的参与,丰富了刘蓉的治学,使他更侧重于经术与治术的结合,这种治学特色一真延用到他征战和治理川陕。
同治四年(1865)灞桥兵败之后,刘蓉被革职回乡,命书斋为“遂初园”,“日取先圣昔贤之书,端坐而诵之”。虽不无萧艾之感,但仍“心盛志强,殆遇壮岁,方思追古人千载之上,而躬驾以从之”。他此时的治学方向深受曾国藩影响,崇尚“以礼经世”,“洞彻先王经世宰物之本,达于义理之原”。
刘蓉早年囿于地域因素,治学不能逾越程朱窠臼,后来戎马倥偬,又多行于秦、泯荒僻之地,于夷务少有接触,不可能具有站在时代前沿的开阔视野,因此晚年他也只能寄希望于传统经术,来维护清朝统治者的统治秩序,以达到稳定国家和社会的目的。
同治十年(1871),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在为父母改葬所写的《台洲墓表》里,谈到了少年时的学习情况。
国藩愚陋,自八岁侍府君于家塾。晨夕讲授,指画耳提,不达则再召之,已而三复之。或携诸途,呼诸枕,重叩其所宿惑者,必通彻乃已。
国藩愚笨,从八岁开始跟父亲在家塾学习。早晚讲授,悉心指点,不懂就反复重来。时而路旁,时而枕边,主要着力于那些一直搞不懂的问题,一定要弄明白为止。
这些情景的回忆不仅让我们看到了父子俩当时求学的刻苦,也让我们体会到在科考之路上攀登的艰难。
其实现代人对科考的知识了解甚少,只知道明清两代的科考是最难的,还知道八股文严重地束缚了知识分子的思想。说起八股文,我们且不论它的是非,只对它稍做一些了解。康熙十二年(1673)的状元韩菼曾有过经验之谈,他认为写好八股文虽是小道,但因为出题必主“四书”“五经”,所以需要“四书”“五经”烂熟于心,而且需要对宋儒代表人物周、程、张、朱等各家学术思想有全面、深入的认识和理解,要做到能融会贯通。这就需要下非常大的功夫,因为各种注释理论之间原本就纷繁芜杂,莫衷一是。他又接着说:
必旁而浸淫于古。自晚周、秦、汉以来,如左氏、公羊、谷梁、屈原、庄周、扬雄、司马迁、班固之文章,以迄于韩、柳诸家,皆能往复出入,变化于其行文之所以然,以养吾气,以达吾才。夫然后俛而为科举之文,皆彬彬可观也。
就是说仅仅这些还不够,还需要旁及古文,要有深厚的古文基础,对以上诸古文大家的文章要做到了然于胸,明白其行文之所以然,然后才能写出像样的八股文来。
科举考试的内容,特别是八股文的写作需要,决定了读书人的治学基础,在这一点上曾国藩和所有读书人一样概莫能外。道光二十一年(1841)正月十七日,曾国藩在写给弟弟们的信中说:
盖自西汉以至于今,识字之儒约有三途:曰义理之学,曰考据之学,曰词章之学。各执一途,互相诋毁。兄之私意,以为义理之学最大。义理明则躬行有要而经济有本。词章之学,亦所以发挥义理者也。考据之学,吾无取焉矣。
此三途者,皆从事经史各有门径。吾以为欲读经史,但当研究义理,则心一而不纷,是故经则专守一经,史则专熟一代,读经史则专主义理。此皆守约之道,确乎不可易者也。
从西汉至今,读书人做学问有三条途径:一是义理之学,一是考据之学,一是辞章之学。各执一端,互相诋毁。我私下以为,义理之学学问最大。
义理清楚则身体力行有原则,待人处世有根基。词章之学,亦是用以发挥义理的工具。考据之学,我没有从中得到什么。这三条途径,都可为研习经书史学服务,各有门径,我以为,欲读经书史学,就应当研究义理,那样专心一致而不会心绪杂乱。由此学经则应专守一经,学史则当专熟一代,读经书史学则专心致意于义理。这都是专的道理,确实是不可改易的。
由此可见,曾国藩的治学思路和刘蓉并无二致,都是强调治学以义理为首,这不仅是宗仰程朱理学的原因使然,也是“吾道一以贯之”的学术传统使然。而且曾国藩与刘蓉在对待文章的看法上也基本是一致的,刘蓉把文章看作是“载道之器,济治之方”,曾国藩则认为“载道者身也,而致远者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