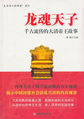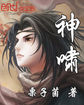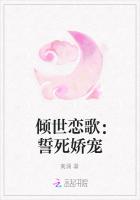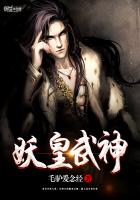天地民物之大,典章制度之繁,惟文能达而传之”。他们的分野,是在对待学习古文的态度上。刘蓉认为学古者容易师心自用,犯泥古、贼古的毛病,为使自己不犯这样的错误,则“举凡班马左史之文,韩柳欧苏之集,尽束高阁”,正是这种偏激的对待古文的态度,决定了刘蓉的治学方向,使他画地为牢,深陷程朱理学的窠臼而不能自拔。曾国藩正相反,由于对科举之业重视,所以他在试帖、律赋、时文等方面的造诣都相当了得,特别是道光十五年(1835)他首次参加会试之后,在北京准备来年的恩科,更是开始加大力气学习古文。由于重视对古文的学习,开阔了曾国藩的视野,使他后来既服膺于理学,又能对汉宋采取调和的态度,而且兼容并蓄,海纳百川。欧阳兆熊说他一生三变,先理学,后申韩,再后老庄;郭嵩焘说他“故其为学,因文以证道”
,都可谓知人之言。
曾国藩一生的成就最得力于他的修身功夫,那么曾国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走上自我修养的正途呢?应该说是从道光二十年(1840)之后,在曾国藩写给弟弟们的家信中开始提到倭仁、吴廷栋、窦垿、何桂珍、邵懿辰的名字,与他们一起订日课,相互监督,而这些人后来也都成为晚清的理学名家。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曾国藩执弟子礼问学于唐鉴。唐鉴官至太常寺卿,是湖南善化人,世家子弟,父祖不仅为官清廉,而且都是名闻一时的学者,唐鉴不仅家学渊源,而且深受湖湘文化学统熏陶,以程朱理学为正学,特立独行,在汉学兴盛之时受诟讥而不悔,并且大力提倡经世致用。他指导曾国藩“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核;曰文章。考核之学多求粗而遗精,管窥而蠡测;文章之学非精于义理不能至;经济之学即在义理之中。”又说:“经济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迹,法戒昭然,历代典章制度不外乎此。”尽管唐鉴等人的学问趋于保守,格局也有失创新,不过正是与这些理学师友的交往,增长了曾国藩的见识,使他走出科举之学,远离鄙识俗见,服膺于理学的自我修身之法,并且持之终生。
道光二十六年(1846)十月,曾国藩在城南报国寺养病,结识了国子监学正刘传莹。刘传莹精通古文经学和考据,曾国藩通过向刘传莹学习,才认识到汉学之长在博,“博则能究万物之情状,而不穷于用”,又认识到汉学讲究实证,实证则考而有据,“征诸古制而不谬”。于是开始重视汉学,并试图融合汉宋。曾国藩一生最为重视的是对礼学的研究,他不仅将学礼与切己体察结合起来,而且尤为注重礼学的经世治世本质,到了晚年视野则升华到习礼行仁的道德层面,在研究礼学的过程中,就明显体现了他这种兼容汉宋的治学特点。另外,曾国藩一生对易学也尤为偏好,善于体察盈虚消息之理,精详吉凶悔吝之道。通过学《易》,曾国藩明于知变,敏于应变,长于求变,又慎于用变,因此能够顺应时代潮流,与时推移,履险绝而不覆,并总能反败为胜,又能有条不紊,积累寸之功,成宏图之业。应该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学问的积累,拓展了曾国藩胸中的识度,使他后来在应对复杂局面时,能够实事求是,从善如流,选择出比较有力有效的思想和方法。咸丰元年(1851)湖南审案局时的严刑峻法,咸丰七年(1857)为父守孝时的化刚为柔,就是运用刑名和老庄之学来化解危机的具体应用例子。
纵观曾国藩一生治学,宗仰于湖湘学统经世致用之风,在时代的新形势下,又能不囿于传统而力求出新。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提出儒学四科“义理、考据、辞章、经济”,把“经济之学”从“义理之学”中独立出来,走出理学藩篱,并且有以“礼”代“理”的学术倾向,同时具有初步的法治观念,重视以“礼”治本,以“法”治表;坚持以“礼”践仁,以“法”惩恶,告别了礼法不分,单纯崇尚以“礼”治国的德治观念。在军事、外交方面也都能根据实际情况提出合理独到的原则和方法,包括后来的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引进培养西学人才,在这些学术思想和行为的背后,都体现了他务本求实、兼容并蓄、不拘一格、为我所用的治学特点。曾国藩通过自己一生的学与用,为世人贡献了自己丰富的思想和方法,充实、提升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品质和内涵,他不仅影响、改变了他所处的时代,而且也必将因其对待现实的态度和智慧,因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影响、改变他之后的中国历史以及民族的未来。
道光十五年(1835)郭嵩焘考中秀才之后,进入着名的岳麓书院学习。在校期间他表现得十分优异,还和素有大志的刘蓉结成莫逆之交,通过刘蓉他又结识了大名鼎鼎的曾国藩。岳麓书院提倡学生“共相切磋”、“端坐辨难”、“反复推详”、“共相质证”,这种学风与郭嵩焘的性格志趣极为相投,使他在治学上广为受益。其实岳麓书院坚持这种辨难求真的学风是极其不易的,因为从顺治五年(1648)开始,在每一个县学府的明伦堂上都设置卧碑,明确规定:
为学当尊敬先生,若讲说,皆须诚心听受,如有未明,从容再问,毋妄行辨难;为师亦当尽心教训,勿致怠情。军民一切利病,不许生员上书陈言,如有一言建白,以违制论,黜革治罪。
这些规定的实质,就是不让读书人有学术自由,不让读书人过问政治。由此可见,清朝统治者当时实行的文化专制制度对学术思想的束缚是何其严重,而郭嵩焘能够顺利进入岳麓书院学习,沐浴在这种学风里是何其幸运。
道光十三年(1833),经学大师阮元的弟子湖南巡抚吴荣光为改变当时书院教育中只注重科举仕进的陋习,培养通经史、识时务的经世致用人才,在岳麓书院的成德堂内创办了湘水校经堂,专门招收岳麓书院和城南书院的优秀肄业生,郭嵩焘有幸成为了其中的一员。湘水校经堂是湖南最早的专门学习汉学的机构,专课经史,强调治学“精微并举”,兼容各派,无门户之见。郭嵩焘自幼就兴趣广泛,尤其喜好辞章之学,通过对汉学的学习,更是开阔了视野,很自然地形成了汉宋兼容的观念,而且主张通经致用,侧重于将“因革损益”“治乱兴衰”“人事之变”与治经结合起来。
饱受湖湘文化熏陶的郭嵩焘,虽然内心里充满了特立独行和经世致用的精神,但青年时期的他依然一步一个脚印地追逐着读书人心中理想的士大夫之路,浸润在传统的思想和观念之中。真正引发他思想和灵魂发生嬗变的转折点发生在道光二十年(1840),郭嵩焘第二次参加会试落榜之后,应浙江学政罗文俊之邀前往浙江入幕,亲身经历了鸦片战争的硝烟烈火,并参与了浙东的防守。英夷的坚船利炮,战后百姓的流离失所、家破人亡,不仅激发起他强烈的爱国热情,更使他产生了强烈的忧患意识。之后他每到一地总是留意走访那些接触过“夷情夷务”的人员,通过和他们的攀谈交往,逐渐了解了鸦片战争的来龙去脉,而且也认识到外患与内政的联系,得出“自古边患之兴,皆由措理失宜”的结论。他后来一直强调与洋人打交道,要以“理”
交涉,便是来源于此。
咸丰元年(1851)太平天国军起,郭嵩焘为保境安民出力献策,先是促成左宗棠出山,再是劝请曾国藩“墨绖从戎”,然后又为好友江忠源代写了着名的《请置战舰练水师疏》,成为湘军倡建水师第一人。咸丰六年(1856),郭嵩焘为曾国藩去江南筹款,途经上海,至此才亲眼目睹了他日思夜想的“夷人夷情”,其间所见到的科技书籍和新闻报让他大开眼界,而对于洋人的居所器物他也认为“细致精妙,非中国所能为也”。咸丰八年(1858),郭嵩焘进翰林院,之后深得咸丰皇帝重用入值南书房。咸丰九年(1859),参赞僧格林沁防守津沽,极力反战,认为“战无了局”,僧王不听其言轻启战端,遂酿成英法联军入京,清政府不得不签订《北京条约》、《瑷珲条约》等。
郭嵩焘从此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洋务处理得荒谬失措,全属执政者于“国体、事要、商情、地势”毫无所知,背后透露的则是士大夫阶层的无识短视,昧于理势而不自知。更为可忧的是,这些虚骄之辈动辄“春秋大义、华夷之分、君父之仇、宗庙社稷”,站在舆论和道德的制高点上,博取时誉,左右朝廷决策,盲目鼓动国人排外,致使外交局面再无挽救的可能。郭嵩焘深感自己的主张得不到重视,报国无门。
如果说郭嵩焘的识见才干有百分之二十取决于他的天分,那么剩下的百分之八十就完全取决于他的经验和阅历了。
作为最早的亲历鸦片战争的知识分子,郭嵩焘不仅目睹了战场上的血与火,更亲身体验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决策过程,这些独特的经历是他之所以比同时代其他知识分子敏锐深刻的主要原因。命运的安排还远不止于此,同治二年(1863),郭嵩焘受命出任广东巡抚,广东当时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唯一渠道,与洋人打交道最多最繁情况也最复杂。郭嵩焘虽然任期短暂,又多受掣肘,但在任期间于洋务多有建树。他晚年回忆说“在粤处置洋务,无不迎机立解”,由此可见郭嵩焘当年的豪情和自信。光绪二年(1876),郭嵩焘以花甲之年出使欧洲,首任驻英法公使,欧洲之行使他真正接触到西方文明,对当时的世界局势有了基本的认识,他超越了洋务派一直认同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理论,明确指出西洋之强在于民主政治和文化教育,而非仅是船坚炮利;并认为“西洋之入中国,诚为天地一大变,其气机甚远,得其道而顺用之,亦足为中国之利”。
郭嵩焘不仅是洋务派一直推崇的“第一流”理论家,对于西方文明有着高人一筹、超越时代的见解;另一方面他也是一位造诣深厚的学者、思想家,他对于传统文化的整理和研究也有其独到精深之处。作为湖湘文化的继承者和弘扬者,他目光如炬、用心良苦,定屈原、周敦颐、王夫之、曾国藩四者为湖湘文化的坐标,以屈原的忠贞爱国为魂,融合改造周敦颐的诚、神、几相统一的方法论,对王夫之严以治吏、宽以养民的政治思想,以及尊实有、务实行的实学思想和理势统一的历史观,都有着十分深刻的理解和吸收,并一直在政治实践中身体力行;对于老朋友曾国藩,他更是称为并世之内无人能超越的知己。在治学方面,他的学术取向也与曾国藩大体相同,主张从学术入手,规范人心,试图通过“循理”、“尊礼”以达到“通经致用”。他在理学、礼学、史学方面都有丰硕的成果,特别是他对礼学的研究,通过疑礼、制礼、习礼、践礼,形成了系统的礼学观点,是连梁启超都十分推崇的晚清礼学名家,他的礼学成就要超过曾国藩。正是因为有深厚的传统文化作为基点,他才能融会贯通西方文化,形成自己独特的洋务思想,认识到西方文明的本源在于它的民主和制度,并巧妙地把西方科技归并到中国的实学中,克服了国人学习西方文明的文化心理障碍,在时代趋势和世界潮流面前因应时势,慧眼独具地认清了中国这艘古老航船应该前行的方向。
曾国藩、刘蓉、郭嵩焘一生治学,或兼收并蓄,或趋于保守,或超越时代,但他们的学不可谓不深、识不可谓不广,而这些学识向内收缩到最核心的地方,就是对圣贤之道的践履。作为真正的儒者,当他们的赤子之心、理想与信仰,投入现实的人生和政治之中,会激起怎样的滚滚红尘?——我们简要看一下他们的人生际遇。
(第三节)命有所定,运有所乖
“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里的一只蝴蝶,因为偶尔扇动了几下翅膀,结果微弱的气流导致身边的空气系统发生变化,由此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两周之后在美国的得克萨斯州出现了一场罕见的龙卷风。”这个现象叫做蝴蝶效应,是美国气象学家爱德华·洛伦兹提出的。在中国文化里面,有一个故事堪与此媲美。“北宋治平年间,洛阳城内有一座天津桥,一天,有一位名叫邵子的高士正和客人在桥上漫步,忽然听到杜鹃的啼声,邵子不禁愀然不乐。客人问他缘故,邵子说:‘天下太平,地气自北向南;天下将乱,地气自南向北。洛阳本来没有杜鹃,今天忽然有了,说明地气已经由南向北。用不了多久,皇帝就要重用南方人出任宰相,变乱纲纪法度,终有宋一代而不得太平。’”——大家看看,这位北宋邵子的思维跨度,丝毫不比爱德华·洛伦兹逊色,爱德华讲的是昆虫和气候,邵子讲的是飞禽和政治。而在这个飞禽和政治的故事里,就蕴含着一定的中国人的命理观念,出现了像“地气”这样的名词。故事里的这位邵子,就是大名鼎鼎的邵雍邵康节;即将受重用的那位南人,是指北宋的改革家王安石。
邵子是在易学发展史上占有特殊地位的易学大师,宋史称他“远而古今世变,微而草木走飞之性情”,无不“深造曲畅”、“通达不惑”;民间称他“智虑绝人,遇事能前知”,是江湖术士们顶礼膜拜的祖师爷。
中国人的星相学、星命学虽然是集宗教、神学、文化、民俗以及心理、骗术等为一体的混合物,但其中也有一些值得人关注的未知领域。在这一点上,颇似蝴蝶效应所揭示的混沌学理论,从无序不规则的现象中找出有序必然的联系。说到这里,一定有朋友会问:我们要了解曾、郭、刘的生平经历,怎么把蝴蝶效应、混沌理论、邵康节和江湖术士都扯进来,难道他们之间有什么联系?——说得没错,因为曾国藩会看相,郭嵩焘也以觇看风水知名,刘蓉对此也颇有研究。曾国藩最着名的一次看相经历,是预言后来的湘军第一名将江忠源。道光二十四年(1844),郭嵩焘和江忠源一起进京赶考,两个人是道光十七年(1837)的同科举人,关系很近,所以郭嵩焘把江忠源引见给曾国藩。江忠源是一个性格豪爽的人,“任侠自喜,不事绳检”,与性格拘谨的曾国藩恰好相反,但是第一次见面,曾、江却谈得非常投机。送走江忠源以后,曾国藩对郭嵩焘不无欣赏地说了一句“生平未见如此人”,然后沉默片刻他又突然冒出了一句“此人必立名天下,然当以节烈死”。江忠源后来官任湖北按察使,咸丰四年(1854)战死于庐州(安徽),曾国藩的预言应验了。郭嵩焘看风水的知名度不啻于曾国藩看相的知名度,曾国藩和刘蓉两位老朋友最后的墓址选择,郭嵩焘都不辞劳苦亲身参与其中;刘蓉在与人往来的书札中于此方面也多有解语。尽管命理之说颇多虚妄,又尽是以讹传讹的成分,但曾、郭、刘自有他们的时代局限性,而且作为传统文化里根深蒂固的观念,对他们的影响是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