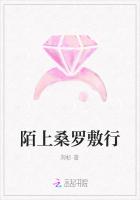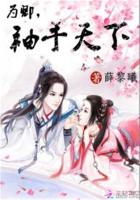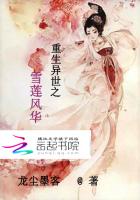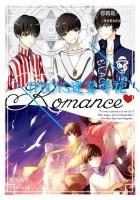《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初成时,中华书局总编赵守俨师弟即相邀约,后以时机相错,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守俨为此一直引以为憾,并不止一次相告,如日后增订,还是交由中华来出。故友已逝,言犹在耳。在增订本即将定稿时,山西古籍出版社的张继红先生和岳麓书社的曾主陶先生都先后过问此书稿,而继红持之尤力。中华书局李岩先生亲与继红沟通,并电告我由中华以较优厚的条件承接此稿。他责成汉学编辑室负责落实,由该室主任李晨光亲任责编。这些情意,令我感动,我也深感增订本所托有人,可告慰于守俨师弟。我庆幸能在有生之年,完成宿愿!
我两次通读过增订本全稿,统一体例和文字,订正讹误,补充不足。如果这本书能给读者以某些用途,那是我和朋友们共同努力的结果。如果尚存在错谬和欠缺我应独任其咎。
我真诚地感谢所有关心和帮助过我的朋友们!我也期待读者们的教正!
(二八年八月一日写于南开大学邃谷)
3、《来新夏书话》序
近代以来,书话的写作日盛一日,许多名家多有书话之作,报章杂志也时见书话的发表,其单独成书者也为数不少。前两年,写书话的名家姜德明先生更搜罗了名家书话十六种,成《现代书话丛书》两辑,对爱读书话的我来说确是带来了一种极大的喜悦。这不能不感谢老友倪墨炎兄惠赠《倪墨炎书话》而引发我即目求书,使前辈时贤的文字风范可因书而究学。我在读诸种书话时,狃于旧习,总想探求书话的渊源流变。姜先生在其《现代书话丛书》总序中曾明确地把书话界定为:
源于古代的藏书题跋和读书笔记,并由此生发、衍变而成。书话不宜长篇大论,宜以短札、小品出之。书话以谈版本知识为主,可作必要的考证和校勘,亦可涉及书内书外的掌故,或抒发作者一时的感情。书话不是书评,即不是对一本书作理论性的全面介绍、分析和批评。书话不能代替书评。
姜先生把书话推源于题跋与读书记,我很赞同。的确如此,在古人的许多札记、随笔中都有谈成书缘由、书林掌故的条目,有的散见,有的也集成一书,如清代黄丕烈的《百宋一廛书录》和周中孚的《郑堂读书记》、李慈铭的《越缦堂读书记》等都类似书话;叶德辉的《书林清话》是以讲书林掌故为主,兼及版本、目录。它们多未用“书话”之名。所以姜先生认为“中国有诗话、词话、曲话,唯有书话,似乎是近六十年始为人所用,并为公众所认可。”这恐怕也是指没有书话之名而言。若从诗话、词话、曲话的载体来说,仍然应算是书话的一种,只是没有书话之名而已。书话之名据说是三十年代初,老作家、老学者曹聚仁在报刊上发表以书话为题的读书小品时开始的,因此对书话的缘起可以这样认为:“书话自古即有,而其名则始于本世纪的三十年代之初。”
我也读过善写书话的唐弢先生的《晦庵书话》,这是一部对读者颇有吸引力的书话。唐先生根据多年写书话的体会,对书话别有一番见地,他提出了四个“一点”说:
书话的散文因素需要包括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的气息;它给人以知识,也给人以艺术的享受。
还有一位写书话的大家黄裳先生,他在《黄裳书话》选编后记中曾表示他写的书话近乎传统的书跋,并且粗略地分为两类:
其一是讲究书的内容、版本、校勘这方面的事的,科学性强,缺点是不免枯燥,可做资料用,但不能是通常读物……此外就还有另一类,在上面所说的种种内容之外,又添上了书林掌故、得书过程、读书所感……不只有科学性,还增加了文艺性,是散文的一部类了。
我基本同意后一种写法,因为他把书话的内容作了比较全面的概括;不过,不一定每一篇都要面面俱到。我认为,写书话不要自我限制得过窄,而应兼具科学性与文艺性,最好能以随笔的形式来写,使其更有可读性。所以我更赞成冯亦代先生的意见,他说:
私意以为书话的内容,可以不必予以界定,写书话的作者要写什么就写什么,只要引领读者去读好书,增加国内外的新旧知识,便是达到了目的。(钟敬文主编《书话文丛/竹窗记趣》序)
这是一种通达之见。我亦觉得,凡是与书有关联,不论是述说书的本身,还是写由书引发出去的论辩,都可以属于“书话”圈圈之内。至于笔墨不妨随便些,篇幅不妨短些,内容不妨有趣些,不需正襟危坐地去读,而能轻松自如地随读随辍,偶有所得,可资谈助,正如墨炎所言,“书话随笔是零食”。他还说过,能写书话的书有两种,一是比较鲜为人知,二是要有点意思。如是按这一界定来看,写书话的书应该范围较宽;那么,我近几年所写有关书的小文,都可以从容缓步地迈进“书话”之列,而无非议之虞。于是把散刊各处的“书话”搜集在一起,经过筛选,得八十六篇,约分为六卷,曰藏书、曰读书、曰论书、曰书序、曰书评、曰书与人,而总题目《来新夏书话》。我把书序、书评列入书话似乎不太符合书话的规则。因为姜德明先生曾说过“书话不是书评”,如果倒过来理解,是不是书评也不能算书话。连带想到书序是否也不允许列入书话一类。如果把书的序评都排斥在书话之外,那么,书话的范围似乎又显得太窄了。书序和书评的主要对象是书,好的书序应该是对一本书钩玄纂要的精心之作,古人很重视写序,古代的《书序》、《诗序》和《禹贡序》等都有点书话的味道。后来的许多学者都对序有所论述,汉孔安国说:“序者,所以叙作者之意也。”宋王应麟说“:序者,序典籍之所以作。”可见序是记写作缘由与体例以及对书或文的解评等,很类似书话。清初顾炎武在《日知录》的《书不当两序》一文中还对“序”作过专论,严格地规定:“凡书有所发明,序可也;无所发明,但记成书之岁月可也。”这样的序应该是可作书话来读的。今人之序,除庸俗捧场之作外,大都是能“引领读者去读好书”,起到导读作用的,所以说读书不读序是不会读书的人。在《现代书话丛书》中所收的许多种书话里都有很值得一看的书序,具有书话引导人去读书的作用。至于书评则是一本书问世后社会价值的反馈,是公众对作者的期望与呵护。书评不一定都是对书作“理论性的全面介绍和批评”,只要是善意的真话,三言两语,点评一二,也是有益读者和作者的。再说,有不少书话本身就是一篇好书评。所以我认为书序和书评也应包括在书话的范围之中,也许我会遭到把书话范围放得过宽的讥评,但这也算是我对书话的一点看法!
我的书话编好后,即蒙台湾目录学研究者、友人陈仕华先生为介于台湾学生书局。学生书局经过讨论审定,很快接受出版,并由游均晶女士为责任编辑。行见我这本雕虫之作,将灾枣梨,特陈有关书话的拙见,并志陈先生与游女士援手之情云尔。
(一九九九年初夏写于南开大学邃谷)
4、《中国图书事业史》后记
《中国图书事业史》是在《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年四月)和《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二年十二月)的基础上,经过删订整合,用以反映自古代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前中国图书事业悠久历史进程的一部通史。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我开始由研究古典目录学而逐渐延伸到图书馆学领域。并由于我受命在南开大学组建图书馆学系和承担教学行政管理工作而需要对有关学科作具体剖析与探讨。在教学实践中,我朦胧地感觉到在图书馆学教学领域中某些课程存在着重见迭出的弊病。如《中国书史》、《中国图书馆史》、《中国目录学史》和《中国藏书史》的分设,就出现无可避免的重复,使人有数见向、歆父子之烦。我想为什么不能将这些课程合而为一,写成一部《中国图书事业史》呢?于是准备先从鸦片战争前的古代部分入手,并在一九八年写成《试论〈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的研究对象与划阶段问题》一文(《学术月刊》,一九八年八月)。这是《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的最原始提纲,得到一些同行们的支持与赞同,于是开始作组织力量和进行编写的准备。
一九八一年,我对此书的规模进行构思和设计,并邀约我的几位不同时代的学生参与合作。我以那篇论文为基础,撰写了四万字的提纲,作为共同写作的基本依据。这份提纲先付油印,后在天津《津图学刊》以讲话形式连载。一九八六年,《中国图书事业史》七十万字的初稿完成,并据此简编成《中国图书事业史概要》,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先行出版。同时将初稿审阅后提出意见,交由原撰稿人分头修订增补,最后由我全面删定为五十万字的二稿,油印后曾分寄有关人士求教。当时上海人民出版社正筹划编组《中国文化史丛书》,常务编委朱维铮、刘泽华等好友,力邀我将此书列入丛书。维铮兄又多次提示,既入丛书,宜与其他书大体划一。于是又经一次删定,于一九八七年冬终于完成一三十余万字的定稿,于一九九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
在《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编写过程中,我就考虑着手进行近代部分的编写,曾邀请几位朋友讨论,比较一致的意见认为:近代部分少所依傍,资料散在报刊,搜集难度较大,不要匆匆启动,应先从专题研究作起。我也想这样急就成章,恐难保证质量。于是暂时搁置。
一九八五年后,我开始招收中国图书事业史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在考虑如何安排他们的学习和研究时,产生了一个构想:我把中国近代图书事业,按历史时期分成若干专题,作为他们学位论文的题目,要求按专题写成材料较充实、论述较完整的论文。经过十年的积累,取得了比较理想的效果,于一九九五年完成了《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的初步架构。为了书稿的早日问世,我从一九九六年至一九九八年,用了足足两年时间,毅然搁置手边的其他工作,全力进行修订、增补、删略、通读,终于在一九九九年将书稿完成,交付上海人民出版社。二年十二月,《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正式出版,了却了我二十多年的夙愿。
二六年秋,上海人民出版社原二书责任编辑、老友虞信棠编审专门以电话向我建议,该社拟将原二书合一为《中国图书事业史》,列入该社的《专题史系列丛书》中,征求我的意见,并称考虑我年事已高,不宜过度耗费精力,主动表示愿承担合一工作。盛情厚意,令我深感欣慰,当即表示同意,并致谢意。于是就由信棠约请另一编辑毛志辉先生,共同进行重组合一。
将原二书合一,不是机械式的拼接,而是重加全面审视,统一体例,删繁就简而不失原意的再创新整合。经过虞、毛二先生一年多不懈地艰辛劳作,终于成为一部以自成体系,通贯古今面貌出现的《中国图书事业史》。这不仅给读者一部完整的专史,为图书馆学领域填补空白,也为我实现了多年来的一种期待。二八年秋,这部经过对原二书瘦身三分之一强的新版《中国图书事业史》的三校清样呈现在我的书案上。我以一个多月的时间,夜以继日地通阅了全稿,除了个别的手民之误和引文校核等有所订正外,应该说已经臻于完善。
二书合一的成就,明显地表现在两点上:
一是体例的统一。原《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虽以中国古代历史时期分章,但每章标题均以图书事业发展的阶段为名。而《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则均以近代历史时期分章,二者体例显然不同。因此,对原前书各章以图书发展阶段所作的标题进行适当处理,使全书均以历史时期为标题,以求体例统一,加强“史”的概念。
二是内容的简练。原二书存在内容叙事过多和琐细的不足,但因原分为二书,问题不显突出。但在合成一书时,全书令人有臃肿之感,于是根据“以图书事业为核心内容”和“要言不烦”的原则,将某些与图书事业外延过远和叙事过于琐碎的部分,精心删节而不失原意。特别是在古今二书衔接部分,尽力删其重复,略其承接,以求古今通贯。
至此,新编《中国图书事业史》的大局已定。又经复决审诸先生详加审定,精雕细刻,再予订正,终使一部新创着作,得以问世。为图书馆学领域增一新着,为对图书馆事业关注的人们得借此了解中国图书事业源远流长的历史进程,为文化事业的积累增一品种。
这部新创着述,是在《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和《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的基础上编写而成。过去曾参与过前二书的朋友,在前二书中曾有所致意。在此我仍忆念当年的友情。而这次的改编,则端赖虞信棠和毛志辉二先生。虞信棠先生是前二书的责任编辑,又是我多年的老友,而毛志辉先生则尚未谋面。他们不论旧识,还是新知,都给予我和我的着作极大的关注。他们从若干成书中选择二书,历尽辛劳,重加整合,编成新着,不能不令我感动,在此再致谢意。我以望九之年,得睹旧着新颜,又何得不至感欣悦?我默祷这部新着当为社会所接受,有更多的读者喜欢它。
(二八年十月下旬写于南开大学邃谷,行年八十六岁)
5、《来新夏说北洋》序
《大家说历史》是一套通贯古今的通俗历史读物。我非“大家”,但愿意为“大家”说说历史上的事,也很想把自己的知识反哺给民众。所以就接受丛书组织者的邀请,承担这套丛书最后一种——《说北洋》的编写任务,说些清末民初北洋军阀三十二年的历史故事。
我和我的妻子焦静宜从事北洋军阀史的研究多年,并写有专着《北洋军阀史》和一些有关北洋军阀的论文。我们就根据这些着述和论文,选择若干与北洋有关的重大事件和为民众感兴趣的片段,简编成书。前有总说,概述一下北洋军阀的总貌;继有分说,选择十个专题,每题一篇,大体按时间顺序编次,连读亦可得一较完整的认识。各篇文字虽未注资料出处,但我们努力做到事事有来源,字字有出处;最后为附录,一是我与北洋军阀史的研究,说说我的治学历程;二是参考书目,提供一定数量的书目供读者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