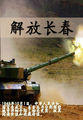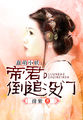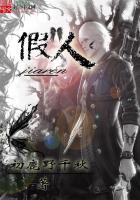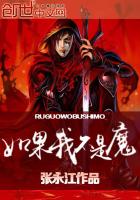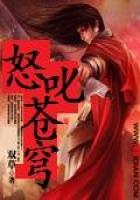(第一节)炎、黄二帝的族源
在本书第二、第三章,我们描述了仰韶文化半坡与庙底沟两个文化类型的主要内涵及其文化特征,目的是试图说明这两个文化类型是《山海经》的文化载体。而《山海经》便是仰韶文化的文字记录。然而文化的产生不是凭空而降,它是人与自然的产物。因为一个民族文化的形成,是由它所属的群体劳动创造的结果,其中也包含着他们中的英雄人物所发挥的作用。若离开了人群或氏族部落及其首领的作用,所谓民族文化便成了见物不见人的空洞的名词。那么,缔造仰韶文化的实体,是黄河流域这块黄土地上哪一个古老的群体——氏族或部族呢?根据我的考订,主要是炎黄二族缔造了仰韶文化的实体。具体地说,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当是炎帝族的文化系统,庙底沟类型为黄帝族的文化系统。
根据《山海经》的记载,实际上缔造仰韶文化的群体,不仅仅是炎黄二族,还有不少的同时的其他氏族或部族的首领。其中极为烜赫者是为帝俊,这位人“神”在《山海经》中曾16次提及,连现代不少学者都曾为他树碑立传或正名,竭力说明其身份和在历史上的地位。有的研究者甚至说他是帝喾,有的研究者说他是帝舜。对此,徐旭生曾有一番很得体的考释,他说帝俊、帝喾、帝舜确是三个人或氏族。
而帝俊的世系,在《山海经》主要有以下几条记载:
有中容之国,帝俊生中容。中容人食兽、木实。使四鸟:豹、虎、熊、罴。(《大荒东经》)
有司幽之国。帝俊生晏龙,晏龙生司幽,司幽生思士,不妻;思女,不夫。食黍,食兽,是使四鸟。(《大荒东经》)
有白民之国。帝俊生帝鸿,帝鸿生白民。白民,销姓。黍食。使四鸟;虎、豹、熊、罴。(《大荒东经》)
有黑齿之国。帝俊生黑齿,姜姓。黍食。使四鸟。(《大荒东经》)
有神,人面、大耳、兽身。珥两青蛇,名曰奢比尸。有五采之鸟,相乡弃沙,惟帝俊下友。帝下两坛,采鸟是司。(《大荒东经》)
有人三身。帝俊妻娥皇,生此三身之国,姚姓。黍食。使四鸟。(《大荒南经》)
有人食兽,曰季厘,帝俊生季厘,故曰季厘之国。(《大荒南经》)
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日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大荒东经》)
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二。(《大荒西经》)
帝俊生禺号,禺号生淫梁,淫梁生番禺,是始为舟。(《海内经》)
帝俊生晏龙,晏龙是为琴瑟。(《海内经》)
帝俊有子八人,是始为歌舞。(《海内经》)
帝俊生三身,三身生义均。(《海内经》)
《山海经》中所记帝俊的多条事迹,在列出的13条中便有10条是说他所繁衍的庞大子孙支系,并分布于东西南北各地。而其世系之脉络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古今史家的考证主要在《大荒东经》所记的“帝俊生帝鸿”条上。经中的“帝鸿”据杜预注《左传》文公十八年说“帝鸿,黄帝”。而传文“昔帝鸿又不才子……天下之名谓浑敦”。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引“《庄子·应帝王》云:‘中央之帝曰浑沌’。罗泌《路史》引干宝言曰:‘鸿、黄世及’之语,提示鸿、黄有别,鸿在黄前,分明为二人,如此则鸿是帝鸿,黄是黄帝,世系相及”,又刘氏再引“贾注《山海经》‘帝鸿生黄帝’。而帝俊生黄帝之说:上列《大荒南经》言:‘帝俊妻娥皇,生此三身之国’”,而皇与黄古相通,或皇与黄为异体字。《诗·豳风·东山》:“皇驳其马,传曰:‘黄白曰皇’,正义:‘黄白色,名曰皇矣’。”由皇与黄通,则黄帝族是从帝俊与娥皇族联姻而衍生出来的黄帝,然也仅见此一说。
又有关帝俊的世系,据袁珂先生也说:“《山海经》中的帝、群帝、众帝和至高无上的上帝,开始是帝俊,稍后才是黄帝等的出现。”文中虽未指明黄帝出自帝俊,但先后关系是明确的。总之,古今注疏家对帝俊、帝鸿和黄帝的关系,说法歧异,也多是学者的比附,就现有传世的历史文献资料看,尚缺乏史迹的依据。如果硬要牵强,则有人为安排古帝系统之嫌,实属无谓。但有一点则是明确肯定的,即氏族社会时期,是一氏族部落“万国”林立的局面。就是说那些帝、群帝、众帝和经文中的帝俊、帝鸿的身份和在历史上的地位,都应当看成是那时的大大小小的氏族、部落或“国”的首领。
前面就《山海经》所记的古帝神人作了些介绍,其目的无非是借此阐明氏族社会时期,人类群体的氏族、部落林林总总的社会情况,却都囿于史料缺失,其史迹和世系不易确定。而历史记录较有头绪者,炎黄二帝尚有一定的史迹和传说为依据。尽管如此,有关炎黄二帝的史迹,从历史学的角度看,其史迹许多都还被神话和传说所包裹,同时对其所处原始社会的社会性质等方面也都缺乏研究和认识。所以近代在疑古思潮的影响下,一些研究者对炎黄二帝的史迹一概予以全盘的否定。
然而从考古学的角度看,炎黄二帝的事迹又都是客观存在的。这主要表现下列三个方面,首先在时空上,炎黄二帝的活动地域与其所在的仰韶文化分布的时空相当。其次在遗存方面,仰韶文化的许多文化内涵,特别是彩陶纹饰,往往蕴含着十分浓郁的神秘图像。这些图像与中国古文献所记载的炎黄二帝的神话传说有颇多相合之处。例如上述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彩陶图像中的人面鱼身纹饰、人面鱼头纹饰、鸟嘴鱼身纹饰和人首兽身合体纹饰;又庙底沟类型的彩陶花卉纹,即为我解读为变化多端富有神秘蕴意的柿花图案,与《山海经》所记炎黄二帝的人神形象和果树食物极为相近。图如其人(神人)其事,文如其画其物,为我们从考古学的角度认识炎黄二帝及其史事提供了帮助。所以炎黄二帝在中国历史上并非虚构,只不过由于炎黄时代的历史悠久,所处的时代又是原始氏族社会时期,在人类意识形态上,初民在人兽混同的原始思维的指导下,以离奇的神话方式来表现罢了。
在研究炎黄二帝的问题上,若要获得一些较为可信的信息,其方法除了结合考古学外,重要的要有史实可证,就是说要有相应的历史文献为依据。在研究方法上,必须拂去古史所蒙上的神秘面纱和神人的光环,拨开被神话所笼罩的谜团,才能澄清先贤们所持的质疑,还其历史的本来面目。据此,本章拟以《山海经》为主线,辅之“出土文献”,并结合有关的古文字学和考古学资料,将炎黄的族源、炎帝的事迹、黄帝的事迹,逐一述其我见。
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将炎、黄二族一贯称之为炎黄,这种二族并举自然与两者历史上的族源、亲缘密切有关。这一点传世文献记载得十分清楚。然细察历史与考古整合研究又发现二者虽同时并举,但也有着先后发展的关系,为此本节拟将对此予以考释。
而有关炎、黄二氏族的史迹,最早的,同时也是比较可信的史料,为《逸周书·尝麦解》。此书据刘起的考证为周成王亲政后的记录文献,保存了西周原有的史料,文字可能是在春秋时根据民间久远口耳相传的历史写定。其文谓:
昔天之初,□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宇于少昊,以临四方,司□□上天未成之庆。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河,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以甲兵释怒。
这段文字中的“□作二后”,其中的“后”,据三代帝王的称谓封号,夏称“后”、商称“帝”、周称“王”看,《尝麦解》确是一篇记载“夏”代或以前史实的篇章。而该篇的内容,徐旭生先生在其《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有个很好的解释。他说“‘昔天之初’是说最早的时候,‘□作二后’是说当时有两个首长,也就是两个最重要的氏族,一个是赤帝,一个是蚩尤,‘赤’与‘炎’篆体字形相近,赤帝就是指姜姓的炎帝族系”。又秦汉时期的《淮南子·时则训》也说:“南方之极,自北户孙之外,贯颛顼之国,南至委火炎风之野,赤帝、视融之所司者万二千里。”高诱注:“赤帝、炎帝,少典之子,号为神农氏。”《尝麦解》中所记的黄帝,据李学勤在其《近年出土文献与中国文明的早期发展》的学术报告中说:“1973年冬,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帛书中的《黄帝书》,有学者认为即《汉书·艺文志》着录的《黄帝四经》……篇中说:‘昔者黄宗(即黄帝),质始好信,自作为象,方四面,传一心……践位履参,是以能为天下宗’”。可知,无论是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中均已表明,在周代抑或以前有关炎、黄二帝的事迹已有文字记录于世了。这大概是毋庸置疑的。
至于炎、黄二帝的族源和发祥地问题,治史者向来皆依《国语·晋语四》载“昔少典氏娶于有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为说。所以《国语》这段文字是一篇很重要的史料,但古今史家或注家质疑声也不少。例如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就曾指出,旧史说炎黄是“少典之子”,实则“少典者诸侯国号,非人名也……炎、黄二帝虽则相承,如《帝王(世)纪》,中间凡隔八帝,五百余年,若以少典是其父名,岂黄帝经五百余年而始代炎帝后为天子乎?何其年之长也?又案《秦本纪》云:‘颛顼氏之裔孙曰女修,吞玄鸟之卵而生大业,大业娶少典氏而生柏翳,明少典是国号,非人名也,黄帝即少典氏后代之子孙……故《左传》:‘高阳氏有才子八人,亦谓其后代子孙而称为子是也’”。韦昭《国语》注:“言生者,谓二帝本所出生也。”徐旭生强调指出远古社会单位是氏族,而“氏族的名字与个人的名字常相混淆,而说少典生黄帝、炎帝……是说这两个氏族由少典氏分出,不是这两位帝是少典个人的儿子”。徐氏把炎帝和黄帝看做是两个氏族名,是十分正确的。但在这里我们还必须强调指明的是,炎、黄二帝之名号是氏族名、首领名混同累世相因的名号。正是由于混同的原因,才给后世古人带来了不少的误解。
检讨澄清了炎、黄二帝的身份和地位,现在再来考察其族源。其源《国语·晋语》里讲的“昔少典娶于有氏”。有氏之,据《说文》云:“虫也,从虫,乔声”。据郑杰祥先生引梁晓景的考证,虫就是现今所称的蜜蜂,“认为有氏族就是以蜜蜂为图腾的氏族,也是以蜜蜂为名分的氏族”。其说很有意义。其意义在于它在披露炎、黄二帝出自同一母族的同时,也说明大自然赐予当时人类一个重要食物的馈赠——蜂蜜。因为蜜蜂所酿之蜂蜜,它不单补给了人类副食,还成了人类敬神媚神的佳品。考古学的资料表明,蜂蜜自旧石器时代以来,就是人们采撷的对象,自然也是新石器时代人类重要的副食来源,这一点在《山海经》中得到了说明。例如《中山六经》云:“平逢之山……有神焉,其状如人而二首,名曰骄(即)虫,是为螫虫,实为蜂蜜之庐。其祠之,用一雄鸡,禳而勿杀。”郭璞注云:“蜂凡数种,作蜜者即称蜜蜂”,经文的“禳而勿杀”,就是说在祭祀蜂神时,是用活的鸡。可见蜜蜂在原始人心目中是作为生活来源之神来对待的。所以,有氏确是善养蜜蜂的氏族,这就为我们说炎、黄二帝发祥于黄河流域做了一个很好的铺垫。
有关炎、黄二帝的发祥地及其族属的发展走势,自古以来说法不一。2000多年前的司马迁,就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指出黄帝的事迹“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是说黄帝的传说遗闻到处都有。而2000多年后的今天连专治传说时代历史的专家徐旭生先生也曾感叹地说,想要找到黄帝真正的发祥地,实在不容易。目前对黄帝发祥地的说法虽然很多,但归纳起来基本上有两种:
一是徐旭生说,认为炎、黄二帝所居之地是姜水和姬水流域,他根据历史文献、民间传说和有关的考古资料,作一番深入考察之后,证明炎帝氏族的发祥地是在今陕西境内渭水上游一带。而黄帝氏族的发祥地大约在今陕西的北部。两族相距不很远。嗣后二族向东迁徙。黄帝的一支东迁路线大约偏北,经大荔、朝邑一带,东渡黄河沿中条山及太行山边渐向东北走。炎帝的一支东徙路线大约顺渭水东下,再顺黄河南岸向东。
二是郑杰祥先生据梁晓景说,黄帝母族有氏是平逢山以蜜蜂为族称号的氏族,平逢山之山名平逢,而“‘平逢’即‘蜂’之缓读,平逢山也就是蜂山,今称北邙山,位于嵩山西北洛阳市北郊,有氏族因居于此山而得名。黄帝氏族既出于有氏族,显然该族最早也应活动于这一地区……当在今河南西部的嵩山周围一带……以炎帝为首领的炎帝族是与黄帝同源的一个部落,当黄帝族向东到达嵩山周围地区的同时,炎帝族则溯伊河、洛河西上进入淆山和熊耳山区……(其地应在)今河南宜阳县的岳山。”
以上徐、郑二氏对炎、黄二族发祥地之说,对考古历史研究者来讲均有很大的启迪。但在我看来,却都缺乏历史与考古资料整合研究的完整性,就是说前者多以文献出发,而少有考古的实证。而后者仅凭借有氏字义的考订训诂,论据是很单薄的。其缺陷是没有将考古学纳入其中作整合研究,即没有考虑到被考古发掘证实的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由陕西渭河流域向东往豫西北和晋南发展的态势,在探讨炎、黄二族发祥地和其拓展时还局限在古文献考释上。我认为要确知炎、黄族源、发祥地和其拓展,在研究方式上必须摒弃旧的静态的观念,以动态的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下面将分四个方面对此问题予以论述。
其一,遗址群落。考古调查发掘表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遗址,在陕西渭河流域呈网络状,星罗棋布,分布十分密集,说明半坡类型文化的人们共同体人口繁衍甚旺,人口增加很快。
其二,文化的发展。在陕西宝鸡北首岭出土的半坡类型的“鸟啄鱼”图画纹饰,为豫西北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阎村出土的同类图像“鸟叼鱼”所承继,这是半坡类型的文化向东发展的例证。
其三,墓葬埋葬现象。半坡类型的以多人二次葬为特征的埋葬制度,也为东边的晋南和豫西北的庙底沟类型文化所吸收和容纳,成为很有文化特征的一种表象。
其四,地层学的证据。经半个多世纪的发掘和研究表明,半坡遗址的文化层,往往被庙底沟文化层所叠压,说明在年代上是后者晚于前者,自然在文化上是有所承继的。
凡上四个方面的考古现象,表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群体,在人口增殖的前提下,促进了群体的向外拓展和文化的传播,如果我们在前面有关章节中认定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人们共同体族属是为炎帝族、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族属为黄帝族的话,那么这与文献记载炎、黄二族发祥地和文化的发展走势为由西向东是何等的一致。考古资料表明,炎、黄的发祥地和文化也正是由陕西渭水向其东的豫西、晋南发展的,那么而今豫西北新郑处只能看做是他们其中一支迁徙至此的拓展地,是其族群亲缘关系的延伸。
有关炎、黄所处的时代问题,从一些文献和考古资料所反映情况看来,他们所处的时代在年代上是不尽相同的。在历史文献方面,有两种不同的记载:
一、先秦时期的典籍。如《国语·晋语》载:“昔少典氏娶于有氏,生黄帝、炎帝”,《左传·昭公十七年》载:“昔者黄帝氏以云纪……炎帝氏以火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