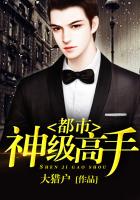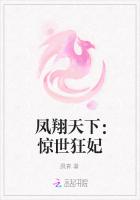材料的来源、选择、生发开掘,坚持什么原则,都是构思的关键。尤其是“生发开去”这一点,极其要紧。我经常与朋友说起,一篇文章,一个讲话,并不要许多材料,关键在于发掘要深,立意要新,思路理顺了,写起来并不困难。
关于《阿Q正传》的构思,我读鲁迅,并没有遇到完整的关于构思的论述。但他在不同情况下,多次说到《阿Q正传》,从中可以看到较为丰富的关于构思的消息。
在《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中,鲁迅有一个很高的期许: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灵魂来。鲁迅先生尽管谦虚说:虽然已经试做,但终于自己还不能很有把握。鲁迅这样说,或许也不完全是谦虚,因为这确实是一个很高很高的期求。从我们读《阿Q正传》和《阿Q正传》几十年来引起的反响看,可以强烈地感受到,鲁迅揭示事物的功力之深,活画出中国人的灵魂的高强本领。这恐怕正是鲁迅高于中国现当代一切作家的地方。构思有此期许最难效法,却也是最值得效法的。
在《《阿Q正传》的成因》中,鲁迅谈及构思的酝酿:阿Q的影像,在他心目中似乎确已有了好几年,但一向毫无写出来的意思。经这么一提,忽然想起来了,晚上便写一点。又说: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还恐怕所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这既说明《阿Q正传》构思的长久性和效果的永久性,又说明一篇好的作品,绝非一蹴而就,也非十月怀胎那般容易,正是因此,其寿命才非人的一生可比。我们写一篇讲话,尤其是一个重要报告,或者是当时需要逼出来的,但真有价值的东西也是长期酝酿的结果。有些根本性的东西,必须在心里长期温着,融化着,一旦出手,才会产生应有的效果和长久的效应。
在《答《戏》周刊编者信》中,鲁迅先生的话尤其深刻和高明。他也特别看中这一点。这应该是大文豪互相赏识的地方,一般人未必有如此高的欣赏水平。就是果戈里作《巡按使》,使演员直接对着看客道:“你们笑自己!”这句话之后,鲁迅特意在括号中说:奇怪的是中国的译本,却将这极要紧的一句删去了。他的主张是使读者摸不着是在写自己以外的谁,一下子就推诿掉,变成旁观者,而疑心倒像是写自己,又像是写一切人,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我认为,这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谈构思了,而是将自己的根本目的、伟大志向和盘托出。鲁迅的巨著构思之宏深,用心之良苦,由此可见一斑。无论写什么,没有良苦用心,文章的成色、成效、根本作用和意义,恐怕都会大打折扣。
我说《鲁迅全集》是文章构思的宝库,或者也可以说是宝山。入此山寻宝,是一项很艰辛的劳动,但绝对是一项有意义的劳动。我采取的态度和办法是,像旅游一样,走进去随便玩玩,与专家的考察研究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但从我旅游留下的印象看,构思者何?何以构思?何构为好,何构为不好,都可以找到答案。即使遇到的是一草一木,一枝一叶,何尝不是一花一世界,一叶一乾坤。这都是极为令人神往的,也是取之不尽的。作为一个观光旅游者,我只能将浮现出来的一点感受说出来,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揭示鲁迅构思的伟大、高远和精深。
有人这样评价贾平凹的文章:文章无论长短,总有出人预料的语言在某处蹦出来。或者说到文尾,一句话一出,让你回味无穷;或者是随他的思绪走着走着,在拐弯处冒出一句来,让你惊诧之余赞叹奇遇……无论语句长短多少,其说人则直挖人的心灵,言物则必尽物的妙用……为此,评者感叹说,这就不只是文学了,是哲学;这就不只是文字了,是文化;这就不只是妙思了,是思想。
我觉得,这是说语言,更是说构思。这个说法也可以用于鲁迅,只是鲁迅又高一层。不只是从一篇文章某一处蹦出什么,而是像《红楼梦》一样,有其整体的大谋划:每一篇既有每一篇的位置、用意,又有着全局的意义;每一句既有每一句的位置和用意,也有着全局的意义。这才叫伟大的构思,伟大的著作,在中国恐怕无人可比。
说到思想的文章,文章的思想,思想的文学,文学的思想,在我心中最推崇的还是鲁迅先生。我想,贾平凹,尤其是鲁迅,其妙语、其妙思、其妙想、其思想,都是习惯成自然。他们似乎用不着构思,就有佳构出现,其实都是呕心沥血的结果。那种自然之妙的养成,是吃尽别人受不了的苦。当然,也有其天才在。贾平凹说,写字、写文章,就像信佛一样,必须有慧根,你命里要有兴趣。还说,我觉得怪的、有意思有味道的,看着很憨厚,但是里面有灵性的我就喜欢。为了寻找灵性,他曾到江南每个县走了一遍。他说那里一个县就出三四十个状元,而陕西历史上才出过一个半状元。贾平凹是值得效法的,虽然也不是那么容易效法,但较之鲁迅,又容易些。这是为什么呢?我认为,其高下,在作文的基本目标和主导思想上就分出来了。
我读书,经常是为了找灵性。在书店搜书,一本书或者并不怎么好,但有那么几处有灵性,就爱不释手。我说的这些,看似与构思无关,其实是从本质上讲构思。当然,我的雄心尤其小,或者没有雄心,所思所想,所求所寻,也就极为有限了。
文学创作要求推陈出新,要讲构思,要讲佳构。公文写作,也要讲构思,也要求全面的文字修养,也是一种创造性劳动,也应有一个较高的追求。除了在哲学、文学等方面广泛汲取,不断追求,还应该将这追求的结果直接用于公文写作。除此之外,还应该考虑与形势任务联系,与领导的意图统一,与适用的范围环境协调。这就是所谓合时合意得体。
如果对形势不了解,弄出来的东西给人以出土文物的感觉,必定大煞风景;自以为了解,实际并不了解,弄出笑话的例子也很多。我今天的讲课,就有出土文物的感觉,是老化和僵化的表现。我在路上问同来的几位同志,是否有此感觉,他们用客气话告诉我,本质性的东西是不会落后过时的。有了对形势了解这个前提,在很大程度上就有了共同语言,对领导意图也就有了几分把握。
干我们这个的,给领导写材料的,讲构思首先是领会领导意图。不按领导意图办,构思再用功也不会有用,所以我想专列一条,谈谈把握领导意图。
3.意图
把握领导意图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领导都很忙,不可能每起草一件文稿,都把意图原原本本告诉我们。即使告诉了,领导的想法也在变化、升华,令人跟不胜跟。较好的选择是从本质的把握上用点功夫。所谓本质,可以是领导以往的文章、讲话体现出来的思想和意图,可以是时势变化可能对领导产生的影响,也可以是领导个性特征在工作生活中的反映,当然也包括我们观察、分析、判断所得。
再讲一个老故事。“文化大革命”前夕,当时的柯庆施到上海任市委书记,他是很善于揣摩毛泽东意图的人。到任后要作一次重要讲话,大概就像我们袁书记的“7·29”讲话一样。开始分别由当时好像都是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张春桥和姚文元,各写一个稿子。他们写出后,认为较为满意,甚至很有把握,送呈后却被否定了。当时的徐景贤,还是个处长,看到这种情况,也想表现一下。他用了几天时间,认真研读了柯庆施以往的讲话和发表过的文章,把握了他的基本思想和行文习惯,包括讲话的语气。写出一稿,一炮打中。后来他的官升得比较顺利,成为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红极一时;再后来,与“四人帮”一起垮台。我不是要大家学习徐景贤,更不是提倡投机取巧,而是想说明把握领导意图的途径和窍门。
我写材料,服务的对象,没有柯庆施那一级的,有的是后来上到了省一级。包括上去的还有退休的,他们对我都有很多指导和帮助,我终身难忘。更让我难忘的,是为他们服务的日月。诚然,感激的话,培养之情和殷切期望,都没有必要在这里多讲。回顾这些,无非是想说怎样领会领导意图。我与各位领导的接触、交往、深交,也是由不了解,到比较了解,再到较多了解。许多往事历历在目。他们对文字工作都很重视,都很关心;对从事文字工作的同志也给予极大的关心、支持和爱护,甚至有袒护、有偏爱。这也不是今天要多说的话。我可谈的领会领导意图,恐怕只能从可以找到的一些影子,略加谈谈。
有的领导,意图很明确,主题是什么,大标题的要义和各个部分的要义是什么,简明扼要几句话,指示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甚至标题也大体拟好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具体内容写什么,也不像考试填空,还需要在完善和丰富领导意图上用功用力,甚至有所发挥。有的人,不作深入思考,不去进一步挖掘,直接“依题作文”,结果往往还是碰了钉子。
有的领导,习惯于让先写一个稿子,在已有稿子的基础上进行思考、讨论,提出新的要求。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可以认为,反正不可能一次成功,需要先搞“原子能”试验,至少是投石问路,因而应付塞责。这是不可以的。有诚心的下级,必然先作认真准备,精心构思,才会与领导形成对话。整体过程都是认真的,负责任的,才可能顺利完成任务。玩小聪明,最终玩住的还是自己。如果做到事事真诚,领导除了对你的材料满意、放心,还会与你真心交朋友。
有的领导,对满意的材料,也未必说什么,脸上或许略露满意之色。满意也只是“就这样吧”;不满意了,也只是“还不行”。也可能说点别的什么,甚至顾左右而言他;或者只吐露半语只字。不说,不等于没有想过,没有思考,也不等于没有深入思考。所思所想,不一定当面交待,也可能在某次会上讲出来,某个场合露出来。有句话叫做“要琢磨事,不要琢磨人”。这是就思想作风甚至思想品质而言。做个称职的文字工作者,要既琢磨事,又琢磨人。不琢磨,怎么能切合领导意图呢?怎么能将一些思想、观点,恰当合意地表达出来呢?不是不要琢磨,而是要多方面去观察,去“解构”。
有的领导非常谨慎,总想处处有出处。所谓出处,就是中央、省以上文件、讲话中有的,至少是“两报一刊”发表过的观点。这就要求,随时留心新观点及其出处,还要弄清楚是在什么情况下如何使用的,精心处理好“雷池”内外的关系。同时,谨慎不等于没有创新意识,不等于没有对新意的要求。如何把握“分寸”与“超越”的关系,同样需要费心费力。
有的领导文字欣赏能力很高,绝对懂文字,创新意识也很强,对文字的气势、布局、起承转合都很讲究,没有创新这一口,不能将你“烹制”的文字端上“餐桌”。这是最好办的,也是最难办的。你是个“好厨师”,可以餐餐如意;手艺不到位,怨不得别人。应该说,为高手服务,是一种幸福,吃苦受累以至吃亏都值。
就“有的”在这里吧。这似乎有点近乎说黑话,而且似乎也只能说出这些了。还有一点,就是弄文字的,尤其是为领导弄文字的,摸清意图固然重要,而恰当处理大胆与谨慎的关系,也应是经验之谈。有的人常碰壁,总招来不满意;有的人常赢得满意,以至欣赏,大概与正确处理大胆与谨慎有些关系。出现一些不如意,都是因为自己没有弄好。这个“弄”字也很有意思。《现代汉语词典》的“弄”字下有四层解释:①摆弄或逗弄。②做或办。③设法取得。④玩弄。除了第四个含义,其余三个含义,或者说三种动作,对文字工作都有些关系。有的人,至少是历史上有的家伙,玩火自焚,将皇上玩弄于股掌之间,这就是奸臣所为了。怎样才恰到好处,恐怕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了。
至于得体,应该说是最难的一个层面的问题。就文字的长短而言,该长则长、该短则短,是得体;就声调的高低而言,该高则高、该低则低,是得体;就语言的文白而言,该文则文、该白则白,是得体;就文字的风格而言,该气壮山河、风起云涌则气壮山河、风起云涌,该小桥流水、娓娓道来则小桥流水、娓娓道来,是得体。大会讲话要高昂而有气势,小会座谈要恳切而平缓,公审大会要有杀气和威严,表彰大会要鼓舞人心和催人奋进,命令要坚定干脆,请示要恳切委婉,批评要中肯,谈心要亲切,都是得体。这是就主要方面而言,微妙方面,很难用几句话讲清楚。做到得体,无论是领导接受请示、报告,还是听者接受指示、讲话,都会感觉舒服和满意。我认为,这是构思中要考虑的,更是文字修养需要用功的所在。诚然,立意的高与新,布局的精与巧,思考的周与全,选择的准与省,更是构思的应有之义,以后有机会再讨论吧。
4.标题
拟定标题是文字工作的一个难点。
一篇文章有一个简洁有力或者简明透亮或者含蓄优美或者醒目大气的标题,很有必要。标题怎么就好,有几个要素?可以到公文写作的书中去查。在此,我仅从自己的读书与实践中,抽取一点自以为是的意见,主要是从直觉的角度谈点粗浅体会。
有人说,标题好比招牌,文章讲什么,先从标题交代出来,读者看了标题,决定看不看这篇文章。看报尤其是这样。看书,包括诗词方面的书,也未必不是这样。清代的大艺术家郑板桥有过关于标题的议论,讲得很切实。他说:“作诗非难,命题为难。题高则诗高,题矮则诗矮,不可不慎也。”这样的经验之谈,切当之论,可谓是诗人论诗人,高人看高人,一般人难有此贴切体会。他举例说:“少陵诗高绝千古,自不必言,即其命题,已早据百尺楼上矣。”郑板桥生活的时代,百尺之楼应该是很高了,当时大概只有寺庙的塔楼或许有此高度,这话说在今天,应该是“早据摩天大厦之上矣”了。
杜甫的诗题好在何处?郑板桥说:“只一开卷,阅其题次,一种忧国忧民忽悲忽喜之情,以及宗庙丘墟,关山劳戍之苦,宛然在目。”如:“哀江头》、《哀王孙》,伤亡国也;《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前后《出塞》诸篇,悲戍役也;《兵车行》、《丽人行》,乱之始也;《达行在所》三首,庆中兴也;《北征》、《洗兵马》,喜复国望太平也。”郑板桥甚至说:“其题如此,其诗有不痛心入骨者乎!”这倒有点孔夫子名正则言顺的意味。不过我想,这“痛心入骨”的感观,也不是单从题目得来的感觉,一定是阅其题读其诗一并而来的感受。一篇诗文题目好,正是联系诗文,越想越好。
那么,就普通读者和听者而言,对好题目的要求是什么呢?据说一是求知,二是好奇。希望从题目知道自己感兴趣的知识,或者从新、怪、神秘等方面获得心理满足。一个好的标题,既可使人“一见钟情”,又需产生“表里如一”的效果。不能“一见钟情”之后,像有些广告,言过其实,给人留下受骗上当的感觉。资深总编辑杨牧之先生出过一本书,叫做《编辑艺术》。可以从中领略编辑的要义,也可以作为心理学著作来读。由此悉心体会文字包括文章标题和书名的艺术,是一种享受,我只是艺海拾贝,从中采摘到一枝半叶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