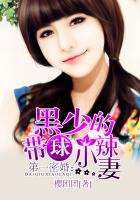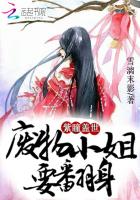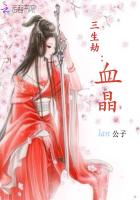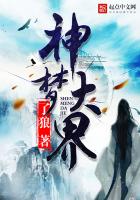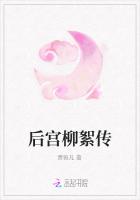以往,我曾多次讲到《人民日报》总编辑范敬宜先生的《总编辑手记》。他在任期间,我没有机会向他请教,只能从报上注意他的名字及其文章。后来,得到他的《总编辑手记》一书,从这个“窗口”探头进去,看到许多编报背后的来龙去脉,了解到许多编辑的艺术和标题处理手段。再后来,我到北京出差,通过朋友沟通,特意将范敬宜先生请出来喝过茶,并向他求取《敬宜笔记》一书。尽管自己见识有限,却也老早就认识到他出手不凡。如何不凡?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说:他的文章如行云流水,舒卷自如,不加雕饰,秀色天成,读后让人明白很多人情事理,得到极大享受。尤其是读的时候,思想感情受文章的吸引,或卷或舒,得大自由,得大自在。
范敬宜先生后来又出过《敬宜笔记续编》,两本“笔记”,我都拜读过,读起来很舒服,处处可以感受到他的“流利畅达而灵气内溢”。读过之后,回味起来,竟有说不出的舒畅。即使时间久了,回味从记忆中渐渐褪去,再次浏览目录,随着题目的提示,又回到阅读时的快乐,仍然会有流连忘返的感觉。其实,即使不作那样的回味,只看目录中的题目,也是一种享受。他的题目,不像鲁迅那样尖锐深刻,却多了几分静、美、秀。具体的好,我难以一一道来。
《总编辑手记》中有诸多关于标题的真知灼见,而且切合报纸和公文写作。一是提高把握大局的能力,抓住带全局性的问题;二是高屋建瓴,先声夺人,研究“重磅炸弹”;三是树立精品意识,精益求精,在“新”上用功用力;四是在研究问题上下功夫,以思想深度取胜;五是要有抢制高点的观念,高出一筹,还要先走一步。这五条都是做好题目的大原则,也是一些基本要求。再具体一点,也有五条:一是抓住传神的细节,把埋在饭碗里的肉挑出来;二是画龙点睛,把“精、气、神”提高一个档次;三是深入一分,抓住传神的细节,把“题眼”拎出来;四是要“活”不要“油”,在庄重的前提下求活泼;五是硬软搭配,长短结合。
范敬宜先生退休后出任清华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我很想去听他的课或是讲座,一直没有找到机会。下面,从我自己的摸索中,讲一点与标题有关的方法性的东西。
一是在广泛浏览中借鉴。大量的书刊和报纸,特别是名人文章,都是借鉴的材料。这方面有三件事对我印象较深。一件是刚参加工作不久,有一阵对研究标题产生浓厚兴趣,从报纸上抄了一本标题,从中寻找拟定标题的规律。这当中,引我上钩的,是总在心里问,人家为什么能把标题拟得这么好?这个问题虽然至今没有得到明确的答案,也没有从中找到可以用三言两语概括的揭示内在规律的概念,但总算多少摸到一些门道。一件是曾把毛主席编辑《中国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改定的与未改的标题抄在一起对照研究。其中有一个标题,至今记忆犹新。就是“看,大青山变了样子!”原来的标题是山西省委打的报告,报告的标题有三十多个字,经毛主席这么一改,感觉特简洁、特亮堂、特潇洒,伟人的风度也跃然纸上。使人觉得有声音,有色彩,绘声绘色,蛙声十里报喜来。再一件是通过研读叶圣陶《修改文章的艺术》一书,其中也包括对标题的修改。在我心目中,叶圣陶先生始终是一个诲人不倦的好老师。他特别扎实,总是有十桶水,才奉献出一滴水,而这一滴水却可照出太阳的光辉。他的《修改文章的艺术》、《文章例话》以及与夏尊合著的《文心》,都是我喜欢并对我产生过影响的书。我最突出的感觉,就是在这平易扎实中,慢慢体会他的修改艺术,标题怎么好,怎么才能好,文章怎么好,怎么才能提高,都有了。
我思也钝。虽然用过一点功夫,至今仍处于较为低级这么一个层次。有时为拟好一个标题,真有一种为伊消得人憔悴之感。但我始终相信,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做诗尚且如此,多读书,读书多了,拟定标题当不是太难的事。眉头一皱,计上心来,随着一个点子出现,一个好的标题,也会很快浮上来。
二是反复比较中选择。一个标题的出现,尤其是形成,其实是对几个方案选择的结果。这种选择,一般是在自己大脑这个加工厂中私下进行,有时也在讨论比较中选择。
记得在长轴搞大规模调研,领导安排起草调查报告。那样兴师动众,调动“千军万马”,折腾了一个多月,肯定要出点“成果”,至少在材料上要出点效果。这样的材料,期望值和要求上都比较高。在拟定大小标题时,为了达到较为深刻大气的要求,几位朋友通宵讨论比较,不知东方之既白。领导看后说,不看内容,只看这几个大小标题,就知道真下功夫了。
有谁会像用尺子量布、用戥子称斤两那样,拿教科书上的概念,来衡量一个标题的优劣呢?好与不好,不过是比较而言,更何况教科书上的概念,也是比较后的概括。所以说,一个标题的好与差固然有基本的衡量标准,但主要是在比较中分优劣。可以在较大范围比较,也可以在较小范围比较。可以自拟几个标题比较,也可以几个人同时拟出一批题目在比较中选择。比较是升华的最好途径。在几个标题的比较中,汲取各自优点,或者叫取优重组,就升华了。我前面讲到协同作战,其中就有集思广益的一面,也有促进比较的一面。
三是几经修改中升华。我们往往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拟出标题,写完文章后,感到文章的深度和广度都不为原有标题所涵括,为此更换标题是常有的事;标题更换后又引出新的思考,内容再度充实扩展。这样,在反复修改中升华,材料就会深刻厚实的多。
记得有一次领导交办修改几个案例。拿过原稿一看,事实与结论基本清楚,就是文稿与案例的体例不合,题目也很别扭。体例不合就不像案例,题目不好,门头不硬,怎么出手呢?即使硬着头皮拿出去,也会碰回来。经过修改,大体合“体”了,题目也好了,又觉得内容不够完整,便又调查充实了内容。这样,经过形式(体)与内容(实)以及标题(目)的反复修改,无论是体例还是内容以及标题都达到一定的完美度。这样的稿子出手时有信心,一般都会收到好的效果。这批稿子对当时的领导留下较深的印象。具体的效果是“能干你就多干点”,好像是更受重用了,当然也更累了。
四是向大师学习中拔高可以说,这方面的大师很多,学习的机会随处可得。虽然就高度而论,我们与大师的距离较远,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向大师学习。就像我们天天可以看天,经常可以感受阴晴圆缺、蓝天白云、日月星辰,虽然未必达到诸葛亮夜观天象的水平,达到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要求,但总归会有自己的感受、收获和提高。
应该说,对于大师我崇拜有余而朝拜不足,请教就更谈不上了。看过我的《旷思敛语》等书的朋友说,我是一个文化崇拜者,中西文化都崇拜,古今中外的大师都崇拜。这是因为我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文化缺失而产生的一种敬畏和向往心理。我自己也并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好,所以几十年来,虽然也接受过一些在职培训,还混上个研究生的文凭,但一直就这么崇拜着。在大师级的人物中,我最崇拜的还是毛泽东和鲁迅。讲在向大师学习中拔高,我虽然没有拔高,还是把鲁迅请出来谈点感受吧。
鲁迅先生的书名很耐人寻味,那才真是前所未有,空前绝后,而且简短到不能再简短,精确到不能再精确。比如小说的《药》,只有一个字。《明天》、《白光》、《风波》、《故乡》、《社戏》、《祝福》、《肥皂》、《伤逝》、《离婚》都是两个字;散文和散文诗的《雪》也是一个字,《无常》、《琐记》、《秋夜》、《复仇》、《希望》、《风筝》、《过客》、《死火》、《立论》、《死后》、《腊叶》、《一觉》也是两个字。两个字和四个字的标题最常见于文艺作品。《孔乙己》是鲁迅最喜欢的一个短篇小说,于寥寥数页之中,将社会对于苦人的冷淡,不慌不忙地描写出来,讽刺又不显露,确有大家风范。孙伏园问鲁迅小说最喜欢哪一篇,鲁迅毫不犹豫回答:“是《孔乙己》”。这三个字据说是从描红纸上的“上大人孔乙己”中取来的。可见鲁迅的留心,思维的活跃和诡谲,其不可比拟的深厚和天才的感悟力都在其中了。
鲁迅杂文的标题实在是好,新意叠出,变化多端,机智俏皮,凝练隽永,端庄大气,深刻通透……不必一一分析,只要将不同类型的标题抄出一些,就足见其匠心独运。如:《一点比喻》、《二丑艺术》、《三月的租界》、《正是时候》、《“人话”》、《刀“式”辩》、《天上地下》、《文学和出汗》、《未有天才之前》、《“彻底”的底子》、《出卖灵魂的秘诀》、《《杀错了人》异议》、《这个与那个》、《现代史》、《推背图》、《辞《大义》》、《“骗月亮”》、《“意表之外”》、《漫与》、《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最长的给我印象最深的有《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和《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联系文章细加品味,会感到色香味俱全,空与实并存,妙趣横生,让你不得不读,不能不钦佩。
鲁迅的标题可以给我们许多启示。好像也不单是由于大师的启示,从文件材料看,有些标题短而有力,很大气;而在文中的小标题,有时用较长几句话作为标题,也很舒展大气,而且能准确全面地表达意图。所以,我想,从大师那里朝拜后,再回到自己的园地来耕耘,收获一定会有的。
总而言之,标题的拟定,窍门肯定有,但取巧并不可取。其中的窍门也是众里寻她千百度,却未必能见之于灯火阑珊处。有人说过这样的话:“什么叫智慧?就是把生活中贯通的一些东西,领悟的一些东西,慢慢积攒,积攒多了,就叫智慧。”标题的拟定,也有智慧,也是这个道理。
5.内容
材料的内容不是客观存在的复写,而是客观存在的提炼和升华。抓住事物本质,通过准确概括,简洁表达,使内容丰富,生动有致,并不是一件容易事。苏东坡的“一意求”,是一种门径。有人说取舍材料就像木匠使用木材,可以八面下线,也是经验之谈。内容的收集与表述,涉及到时代性、思想性、具体性、生动性、准确性,是一个很复杂的劳动过程。
有人说冯友兰教授的特点是把很复杂的内容说得很简单,金岳霖教授的特点是把很简单的问题说得很复杂。为此冯先生开玩笑说,我是头脑简单,把丰富的世界说简单了,金先生水平高,把简单的事情分析得很深刻精微。这又涉及到写文章的风格,各有千秋,非短论长,都在情理之中。
鲁迅先生与李霁野谈到他的小说内容的来源,是这样说的:“偶然有一点想头时,便先零碎地记下来,遇到或想到可写的人物特性时,也是如此。这样零碎的记录在心里慢慢融化,觉得人物有了生命,这才将段片的拼凑成整篇的东西。全篇写就以后,才细看哪些地方要增删。最后注意到字句自然的韵调,有读起来觉得不合适的字眼,再加以更换。”又说“我的文章里找不出两样东西,一是恋爱,一是自然。在要用一点自然的时候,我不喜欢大段描写,总是拖出月亮来用一用罢了。”他还说过:“我总想把绍兴社会黑暗的一角写出来,可惜不能像吴氏(指吴敬梓)那样写五河县风俗一般的深刻。”
可见,鲁迅已将搜集、融化材料,融入他生活的日常中,或者生命的全过程中。他总是在搜集,也总是在融化和谋篇;总是在注意文章内容的韵调,也总是在借鉴前人的经验,在比较借鉴中追赶、超越。我崇拜鲁迅也是全方位的,他的天才,他的勤奋,包括对他搜索、融化材料也特别有感觉。但我不搞创造,写一点随笔之类,也是近几年的事。多去的岁月主要是接受安排写讲话稿和文件之类,好像也不全是阿Q的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内心似乎更多一点主动和创造的意味。所以,鲁迅的话对我也很有启发。不管写什么,总是先有一点意念,在心里温着,融化着。为了深入进去,我喜欢与人讨论,也喜欢在散步时深思。
关于内容表达,回想起来大体经过三个阶段。开始,就是刚写材料的初期,总觉得没有东西可写,材料不够,生编硬造,还常常无米下锅;后来,大概可以称为中期,好像不觉得搜集材料是太困难的事了,又总是舍不得,惟恐材料丢掉,结果像现代人营养过剩得肥胖病一样,臃肿拖沓,自己难受,别人看着也难受,而且无可奈何;再后来,懂得做减法的重要了,越来越知道简洁的可贵了,却又总是因为不能简洁而困惑。这样的困惑,至今仍然纠缠着自己,如何减,怎样洁,成为无休止地横在自己面前的沟坎。散步思考时,常常是为这种取舍在心里斗争,当然也是在深化。
我崇拜鲁迅,所以读鲁迅比较多。越多读鲁迅,就越崇拜鲁迅。仔细审察,我之所以读鲁迅比较多,虽然是为他的伟大追求和求索精神感动,同时也是为他的深厚、深刻、深邃、深广、深郁、幽默、智慧,特别是简洁、精妙而入迷。去年以来,读了北大出版社王炜烨先生精编的大学者随笔书系,已出二十多种。有徐梵澄、王佐良、冯友兰、闻一多、顾颉刚、顾随、胡适、叶圣陶、朱自清、许地山、胡风、周一良、启功、徐志摩、林徽因等。他们都是文章大家,也都是简洁精妙的大师。为向他们学习,每读一本,便写一篇随笔,称为《读书小语·师者系列》。这是一种练习,重在练“减法”;还写了读鲁迅和其他人的随笔,也是在练“减法”。王炜烨先生读后说,你的《小语》很凝练,好读。说明我的“减法”有一定进步。
讲到文章的内容,轰动也招非议,非议也产生影响,但总需言之有物,言而由衷,言而中的,有所指向,有所表述,有所作用,识大体,识时务,合要求。以此为限,我主张尽可能大胆一些,泼辣一些,刺激一些。写作态度狂一些,思路就宽阔一些,内容就丰富一些,可读性也强一些。我们服务的对象识别力都不低,不必担心被引入歧途。最重要的是怀着一颗什么样的心来写?怎样写?
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先生的著作《鲁迅书影录》,对鲁迅的书和文章有很精确的把握和心悟,不妨抄几段以供体会。
《呐喊》:内蕴怪异,意绪深广,流畅沉郁,有悲慨之气。先生内心的苦楚和希冀,都渗透到纸面上,现在读来,给人的震荡仍是不小。奇书行世,天地为之一动,那是自古而然的。
《彷徨》:此书的调子更为沉郁、悲怆,意蕴也更深广了。黯然凄迷之调,不绝如缕。书的开篇引用了《离骚》的诗句。屈子诗句,可解《彷徨》之意。此哀人警世之书,虽迷蒙隐晦,而真情毕现。《彷徨》问世至今,久畅不衰,盖以其哲思诗情兼备焉。
《坟》:此书之文章,老到精妙,幽黯然,读之可谓一唱三叹,吟咏不绝。有“高山流水”之境,而无“和者盖寡”之陋,这是后人服膺仰慕先生的缘故吧。
《朝花夕拾》:篇篇生辉,均为珍品。笔韵之美,构想之奇,未有不三致意焉。以凝重的目光叹流年碎影,空幻之中有大悲大爱,确是天地之间的真性情。不惟是天然性灵的闪烁,亦人生奥义的咀嚼与内省。70余年过去,读之仍无隔世之感,此正先生的魅力所在。
《野草》:鲁夫子以散文诗的形式,究天人之际,思想的广博,令人叹为观止。文体奇崛,字句阴晦,似现代主义绘画,也如印象派的音乐。调式玄奥,情韵苍凉。悲愤与绝望杂糅,空幻与热力相间。寓意深广,有佛家慈悲之心,又似尼采、萨特式独白。心事浩茫,奇思迭起,多大哲之襟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