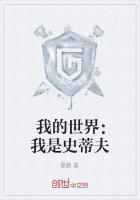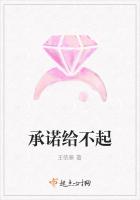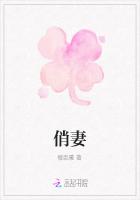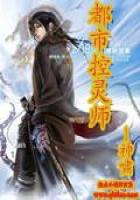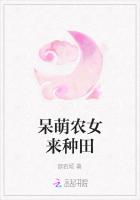若是宁中直知道张载的声名,一定会后悔自己的无知。人家张载三十八岁与苏轼同榜的进士,这人看起来岁数不小了才中进士,似乎大器晚成。而实际上张载年轻时,就因组织义军从党项人手中夺回洮西失地而声名鹊起,得到了当时西北重臣范仲淹会面机会而受到青睐,范仲淹劝他读书,而后他返乡苦读《易》、《大学》、《中庸》等儒家经典,至三十八岁自感大成,这才赴汴京应试。而就在等待应试之前,他在当朝相公文彦博的支持下,在开封相国寺设虎皮椅讲《易》。宁中直和苏氏兄弟的联名请帖发出没几天,谓州的张载就派人给予了肯定的答复。一天晚上,遇洛阳程颢、程颐兄弟,张载是二程的表叔,但他虚心待人,静心听取二程对《易经》的见解,感到自己学的还不够,第二天,他对听讲的人说:“今见二程深明《易》道,吾所不及,汝辈可师之”。于是撤席罢讲,但又对二程说“吾道自足,何事旁求”,表现了他在学术上积极开拓精神,他的《易说》就是在这个时期写成的。而宁中直这个速成的“名士”虽然墨水灌了不少,可毕竟信息闭塞,以至于连张载这样学术界风头正劲的关学学宗都不知道。由于张载正担负着谓州军事判官之职,环庆路经略使蔡挺对张载又极为器重,事无大小都要和他商量,目前西北情形紧张,谓州军备事务繁忙,张载故而约定在西北大战之后前来讲学。
宁中直见他并不前来,心里倒有些看不起张载,他还以为张载是徒有虚名,不敢前来。然而他只是把这样的想法刚一透露给苏轼,苏轼顿时大惊失色,连忙掩住宁中直的嘴,提醒道,“中直可不要把这话说出去了~张子厚所作的《易说》据说大内的官家读了也赞不绝口,何况张子厚年轻时便曾在西北组织义勇为国效力,收复了洮西失地,此人绝非夸夸其谈之辈,中直不要轻视于他啊。”
宁中直望着苏轼郑重的表情,只得点头称是,可是心里却嘀咕着,“他真这么厉害怎么不敢现在就来讲学?”不过当着苏轼的面,宁中直也不好意思说出口。眼见张载这个之前还以为的近水却解不了岐山学院的渴,宁中直不禁挠起了头……
正当宁中直在西北还在忧虑岐山书院之时,汴京朝廷上却已经进入备战的状态。这些日子,随着西北探子们如雪花般传来的情报,朝廷的风向也为之一转,大臣们的奏章仍然没有离开西北大战这个议题,不少臣工也同样向大内递着各种陈条。然而当党项人冰冷、带着血腥气的刀锋逐渐从鞘中缓缓显露出来的时候,大宋朝廷内文人的软弱便赤裸裸地显露了出来,这几天摆在英宗御案上如山的奏章,其内容已经只有少部分是慷慨陈词的御敌之策,而大部分则是希望官家能派使臣到西夏处求和息兵。其中尤以知谏院的司马光与侍御史吕诲为首,他们激烈反对帝国在财政入不敷出的情况下进行一场胜率不高的战争冒险,司马光的奏章里意思很明白,与其花大笔军费用来支持这次帝国三十年来首次大型军事行动,不如抽出其中十分之一去贿赂西夏。他在奏章中算了一笔账,如若此次战争失败,帝国除了之前高昂的军费,还要付出大笔的款项去赔款,司马光和吕诲等人认为与其冒险不如求稳,像以往一样,只要满足了西夏蛮族的贪欲,对党项人来说庞大几百万贯而对于帝国来说只不过九牛一毛,而如果帝国用于发动这次战争的费用则至少要花去一千万贯以上的国库款项。而司马光的奏章在政事堂上一经几位相公的商议,不知被谁透露出去。司马光的主张一被透露出去,很快引起非常多臣工的赞同,而司马光的主张也得到了三司使蔡襄以及御史台中丞吕公著的支持,而就连金陵尚在丁忧中的王安石也上疏反对朝廷发动战争。不论这些人的动机是否真的是为大宋考虑,但是其愈演愈烈的声势就已经逐渐引起英宗的注意。而这也直接导致主战派的韩琦、文彦博、富弼等人显得有些势单力孤。
“韩公,如今西北鏖战在即,然而朝野内外求和之声渐成气候,朕虽然有心一战复震我大宋声威,但若朝廷臣工反对太多,朕也会很为难。”御座上的英宗皱着眉头说道。
韩琦听了官家的话,原本绷紧的心却稍微松弛下来些,韩胥从西北带来的消息显示宁中直对这场战争充满了信心,而自己儿子工部兵器将作监韩忠彦也曾经提到宁中直正在西北秘密为禁军制作新型军械,只要官家还没有因为朝臣的压力而改变心意,他韩琦就还有信心劝说官家坚持下去。略作思考,他说道,“官家,老臣斗胆问陛下一句,官家以为此战胜率几何?”
“这……”赵曙明显一愣,自己一国之君,岂能轻言胜负?赵曙望向韩琦身后的枢密使文彦博,“文公执掌枢密,军情当娴熟于心,文公可试言之。”
这让本来正专心听赵曙和韩琦说话的文彦博始料不及,他下意识地挪出队列,拱手道,“此番西北大战,彦博观之,郭逵西北宿将,与西贼对峙日久,兼其智勇俱备,可作胜算两分;秦王年纪虽轻,但到西北后一向勤于军务,差缺补漏,惩戒不法,军中士气为之一振,可作胜算一分;西北番兵经过几月经营,边境军寨林立,这可作胜算一分……”
说到这,文彦博却有些迟疑道,“只是……秦王长史宁中直,此人极富谋略,本是极好的参谋,但是这些日子臣尝听闻他在西北正试制些奇巧之物,若到时两军对阵,并无效果,动摇了军心,臣……臣不敢言。”
文彦博说到宁中直,赵曙脸上却悄悄挂起了笑容,接着文彦博的话说道,“此事朕自有计较,文相公无须担忧。”宁中直前几日便已经派人将纸铠样品秘密送回汴京,赵曙昨日刚刚让李宪和几名御直班侍卫试验了一番宁中直那神奇的纸铠。“中直奇谋一出,足足可抵三分胜算,算起来足有七分胜算啊……呵呵,宁中直这小子……”自言自语间,赵曙不禁回想起昨日读过的宁中直的奏章。
“咳咳……”韩琦见赵曙明显有些走神,连忙作势咳嗽了几声。“机会是争夺而来的,而不是等来的……宁中直的话虽然有些古怪,其中却不乏真知灼见啊。”赵曙兀自仰头感叹道。
“诸位相公,朕决意西北一战,诸公可安守各职。”富弻等人不禁错愕,之前准备大大段说词顿时没了用处。官家脾性一向求稳,什么事都要谋定而动,怎么此次胜算不过七成却突然就下定了决心?
此时,殿外一只不知名的小鸟突然闯进了殿阁内,惊慌地一边唧唧喳喳的叫着一边拍着翅膀四处乱撞。原本严肃的气氛顿时变得有些滑稽,殿外的侍卫们赶忙进殿,狼狈不堪地追逐着那只昏头昏脑的鸟儿,几位相公于是赶忙告罪,依次退出了勤政殿。
英宗赵曙安坐于座上,望向殿外重重宫墙,不知是在观望宫外已经盎然的*还是遥望着西北那逐渐消失的血色落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