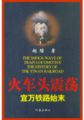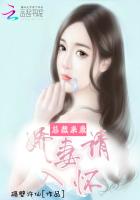邱易东诗歌中的叙述、抒情也有从作者的角度出发的。作者是叙述者,是抒情主体,儿童作为画面中的人成为较客观的描写对象。“在秋天,春天般的小女孩透过蓝色的窗口/想象着遥远的落叶季节”(《一个女孩的落叶季节》);“春天,他奔跑的时候/风开始流动”(《告诉你,男孩倾听什么》);“山里的孩子对海的向往/由一片天空引起”(《山里的孩子对海的向往》);“小女孩上锁的抽屉里/有一本连环画讲一只蝴蝶与另一只蝴蝶的故事”(《一个小女孩的〈梁祝〉连环画》)这里显然有第三人称叙事的特点。叙述者向读者描述一个处在瞬间的画面,画面里有人物,有时也有某些事件,它们共同构成一个单一的或并置的情景。这时作品中的抒情主人公多是作家的自我形象,其情感可以通过直接的抒情、议论表现出来,也可以通过作品的系统结构含蓄地暗示出来。在很多时候,邱易东作品中的视点并不是单一的。就是在同一作品中,在邱易东的诗歌中,上述叙述中的各种角色很多都是拟人化形象。视点也是可以转换的。比如在《地球的孩子不要黑雪》这首长诗中,作者就设定了太阳、珠峰、雪花、孩子作为叙述者,且每一次叙述都有不同的叙说对象(“太阳对珠穆朗玛峰说”、“珠穆朗玛峰对太阳说”、“地球的孩子对珠穆朗玛峰说”……)叙述者、叙述对象互相交叉,像一首宏大的交响诗诉说着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有一种用一般的单一视点很难表现出来的立体效果。就是在局部,这种视点的改变也常在邱易东的诗歌中表现出来,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括号和插入语的使用。邱易东常在正常的叙述中加入一段放在括号里面的话。有时是一个句子,有时是整整一个段落,在不同的叙事语境中,语义及其在句子中的作用也各不相同;有时,它只是一种简要说明,类似戏剧前面的提示,如《地球的孩子不要黑雪》,开头就是一个介绍性的提示:“(一场战争使圣洁的世界最高的山峰也覆盖了厚厚的黑雪,孩子在呼吁……)”括号里的句子可看作是叙述者提示剧情的话;有时,它是人物的内心独白,如《蝈蝈》,“既然,孩子/你喜欢我/绿宝石般的歌/那就为我准备/一只笼子吧/(虽然,我也/会痛苦地思念/草丛星空)”,括号里就是蝈蝈心里想着但没有向孩子说出的话;有时,它是对已叙述出来的内容的一种补充:“我最喜欢大海/(蓝天白云属于小姑娘)……”有时,作为叙述者的作者会突然站到叙述中来,面对面地跟读者说话,如《一个小男孩的陀螺》,在作者叙述小男孩忘情地在寒冷而又透明的世界旋转他火焰般的陀螺时,忍不住以括号的方式插入了一段描写作者自己心情的话:小男孩,在写这首诗的时候/一个和你一样充满童心的儿童诗人/禁不住想提个古怪的问题——/谁在旋转我们的地球/谁在旋转你的人生?
这是从第三人称叙述突然地改为第二人称叙述。叙述者由描写人物改为面对人物,拉近了叙述者与人物的距离,产生一种真诚、客观的情感效果。作者诗歌中许多视点的改变都产生相近的效果。
视觉美感
艺术空间的重视和创造,美感是一项基本原则。邱易东诗歌极注重这方面的美感,尤其是视觉上的美感,包括意象的选择和创造,空间位置的经营,色彩上的调配,都尽量和谐,并和诗的内在意蕴统一起来。有时,这种对视觉美感的追求甚至会成为作者形象创造的触媒和主导性因素。比如,在谈及我们上面说到过的《一个男孩和他的陀螺》的创作时,他就曾说:“我觉得这首诗的‘诗眼’就是陀螺的颜色。这是诗的末尾把陀螺比拟为‘小红马’,升华诗意的关键所在。”①从红色的陀螺到红色的骏马,“红色”不仅是诗意升华的内在线索,而且,将一团火焰般的红色放在一片洁白、透明而寒冷的背景上飞快地旋转,视觉上就有一种强烈的美。同样,在《寄给小城》中,将乡村的大柿树和小城的阳台叠印在一起,以大柿树上的柿子和阳台上的太阳相重合将“鲜红”这种颜色凸现出来,影影绰绰地有一种印象派风景画的效果。类似的描写还出现在邱易东的许多诗作中。
①邱易东:《少年诗话》,伊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1页。
那一片枫树林/像岁月的红纱巾/在北风的脖子上挂着//美丽了心的风景画//这个冬天没有寒冷——《冬天的红纱巾》
我们村庄的炊烟和笑声/在繁茂的枝叶间袅袅地/升起淡蓝……——《我们村庄的银杏树》
把一片经霜染红的枫树林比喻成一条飘动的红纱巾,首先把握的就是二者都有鲜艳的红色。从前者到后者,虽仍是以实喻实,但“红纱巾”比枫树林更虚化,更柔和,更轻灵。这红纱巾又系在北风的脖子上,使本属凌厉的北风带上一种喜庆的温馨的色彩。且北风没有实体,这就将枫树林进一步地虚化、轻灵化了。经过几次转化,留在视觉里的就是一片纱巾般的柔和、轻灵,带着人的体温的鲜艳的红色,给那本属严寒的冬天带来美丽和暖意,所以作者称其为“美丽了心的风景画”,并预言“这个冬天没有寒冷”。总体而言,邱易东诗歌因为面向少年儿童,描写对象也是少年儿童接触较多的事物,加之他本人较多地接触乡村,在价值取向上更倾向他笔下的“远山”,他诗歌中的艺术世界多投射着清亮的童年人生的感觉,色彩鲜艳、明丽,充满清新的蓬勃的色调。从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将邱易东视为属于远山的儿童诗人。
三
诗歌艺术主要是意象的创造和组合的艺术。意象变了,意象组合的方式变了,诗歌的意蕴自然会发生变化。或者说,正是诗歌意蕴的变化,作者感知世界的方式的变化,作者思想情感的变化,才使作者笔下的意象及意象组合方式发生了变化。邱易东在诗歌意象创造、意象结构方式等方面对传统儿童诗歌的超越,从深层看,自然也是作者感知世界的角度、方式,作者面对世界感悟到的内容、意义发生了变化。比如,在作者的诗歌中,很少看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充斥儿童诗的社会政治生活的画面,很少从社会意识形态的角度对儿童进行品德教育的内容,也很少借儿童说事,以儿童的某些特征如天真纯洁之类去表达作者某些愤世嫉俗的情感。他有他自己的世界,他的诗歌富有特色的意象及意象组合反映着作者对生活对世界富有特色的理解。
远山畅想
在邱易东诗歌、特别是其早期诗歌中,“远山”是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意象。他的许多重要作品,大都是为远山写的。如《去远山堆雪人》《来到静静的深深的大山》《山里少年幻想曲》《我们村里的银杏树》《山里孩子对海的向往》《远山的两个村庄》《寄给小城》《到你的远山去》《远山致小城》《我们村子冬天的味道》《农家的向日葵》《失学的女孩》《远山、风、鸟和一个孩子》《远山的孩子对汗的理解》《在远山放风筝》《到我们的山谷里来》等,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邱易东就是一个属于远山的儿童诗人。
邱易东写远山,首先是因为远山是作品中描写的孩子们的家乡,赞颂远山表达孩子们对自己家乡的爱;推远一点,也是对家乡文化、历史,甚至对祖国的一种爱。家和国有时是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大巴山本就是一个十分美丽的地方。蓝天、白云、微风、细雨、大柿树、老水井,组成一幅幅古朴、清新,充满生命活力的美丽画面。“我知道浪花只绽开一瞬的美好/最不容易打捞/如果我远山淡黄的槐树花/从这条小河流来你会细细地撷取到/我的遥远的初夏”(《远山致小城》);“远山有雪/我们去那儿堆雪人……雪人在远山雪人不会融化/雪人在远山很纯洁很坚强”(《去远山堆雪人》);“把稻谷收进粮仓/把稻草架在村口的树上/冬天就来了……在我们村子里/没有稻草垛/就没有冬天的味道”(《我们村子冬天的味道》);“三月来到青青的果园/来到满园嫩得发亮的叶尖/……三月青青的果园/一片深深的多梦的海”(《三月来到青青的果园》)。作品中的孩子们,包括借孩子之口抒情写意的作者,都是怀着赞美、自豪的心情来写这片古老而又清新的土地的。有时,为写远山,作者甚至以“小城”作衬托:“远山的朋友啊/我多么羡慕你们/在北风的呼啸里在洁净的雪野上/把笑声和脚印尽情抛洒/我的这座小城/大街上薄薄的积雪已被无数车轮碾成稀泥了”(《祈望雪花不要降落小城》);“十三层高楼的某一面玻璃/贴着你寂寞的眼睛……看远山朦胧的烟雨朦胧的清新”(《雨季的遐想》)。作者也写远山的艰辛,远山的苦难。“还有村口的老磨盘/我不能给你寄去/我们的小村曾经在它的沉重下旋转/让它待在我们的展览室/给许多年以后的小村孩子讲述我们小村长满青苔和杂草的历史”(《寄给小城》)。有了这种苦难的深化,邱易东诗歌对远山的赞颂有了更丰厚的底蕴。
在邱易东关于远山的描写中,人是最亮丽的风景。他们勤劳,他们淳朴,他们坚毅,他们善良,他们用自己的双手给本属自然的远山打上人的烙印,使远山有了人的性格和感情。“在我们小村湿漉漉的早晨/星星总是落满井边汲水的脚印”(《寄给小城》);“你总是把远山神奇而富饶的故事/变成米花在我的嘴里脆脆地融化/你一边擦动火苗上旋转的砂锅/一边给我们讲叮叮当当的牛铃、稻草人/夏天烟雨朦胧里披着蓑衣的辛勤”(《远山的爆米花爷爷》);“在我们远山/有时候汗水,像雨/有时候雨点,像汗”(《远山孩子对汗的理解》);“离城市最远离太阳最近的村庄/离繁华最远离质朴最近的村庄/巴掌般的晒场只晾晒/金黄镀成的季节/窄窄的小巷只来往勤劳忙碌的脚印”(《到我的山谷里来》)。作者写得最多的还是远山的孩子。他们和远山融为一体,是远山最有生气的部分。“总希望和太阳同时从山顶升起/总渴望望见更远的蓝天/有着太多的幻想/有着太浓的浪漫”(《山里少年幻想曲》)。和别的地方的孩子一样,这里的孩子也有艰难,也有痛苦,也有“酸涩的记忆”(《到我的山谷里来》),也有失学的女孩,作者用很现实的笔法记下了山里孩子的艰辛和奋斗,远山也因这些孩子而生动。
远山是一种自然,一种生活类型,一种历史,一种文化,更是一种具有特殊意蕴的美。在作者描写的远山的许多特点中,作者最强调的是它的质朴和清新。“把这满树的水珠摇给你……摇给你/初夏的繁茂与明净朦胧与神奇/刚刚拱出地平线的/花蕾般的太阳/与泥土一起编织的梦”(《把这满树的水珠摇给你》);“在我们小村湿漉漉的早晨/星星总是落满井边汲水的脚印……在我们远山色彩芬芳的秋风里/阳光和遍地果实总是互相辉映……在我们牛角上挂着星期天/绿色总是在村子里呼唤”(《寄给小城》)。这当然和作者写的是儿童诗有关。儿童诗偏重写儿童,偏重从儿童的视角去感受,儿童和大自然亲密地融合在一起,质朴、清新自然作远山最突出的特点表现出来。而“山”前加一个“远”字,突出一种距离,这远山是从小城的角度看的,或是相对小城说的。有了这种距离,远山在质朴与清新之外,更平添了一层隐约和朦胧。这距离是就空间而说的,也可以看做是就时间而说的。相对于小城的现代,远山更有一种历史的悠远,这就更增加了一种文化积淀的深度。作者深情地抒写远山,赞颂远山,也是在用全部的心呵护一种美。所以,当作者看到为了橘红的客车的到来,世代屹立村口的银杏树轰然倒下,作者在欢呼未来的大道“坚实和平/坦”的同时,不由产生一种深深的隐忧。“尽管我也梦想沿着它走向山外/但仍然渴望用我们稚嫩的双臂/将我们村庄的银杏树/扶起在我们村庄的上空/……望不见那巨大的银杏树了/还望得见我们的村庄吗?”(《我们村庄的银杏树》)对远山的呵护其实也是对一种美学理想的守卫。
诗化的童年
因为是儿童诗,自然要较多地写到儿童、儿童生活。一直以来,人们有一种倾向,似乎一说到儿童、儿童生活,就是纯洁的、天真的、蓬勃向上的,等等。其实,这不过是人们习惯了地看待儿童、儿童生活的角度,一种多少定型化了的美学观念而已。许多人持这样的美学观念,说明这样的美学观念有客观依据,深入人心,但即使如此,也不能说这就是儿童、儿童生活本来的、客观的属性。无论是儿童还是儿童生活,都是多侧面,多角度的。面对这个“文本”,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解读。有人从儿童生活中读出纯真无邪,有人从儿童生活中读出幼稚无知;就是同样读出纯真无瑕,各人的感受和呈现方式也不一样。邱易东有良好的诗化生活的能力,他笔下的儿童、儿童生活是诗的,也是现实的。虽然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作品,依然有五十年代某些儿童诗曾经有过的纯净。这或许是因为他笔下的儿童、儿童生活主要属于远山,有着和远山一样的性格和特点。
和许多写儿童、写童年的诗歌一样,邱易东的许多作品也表现出对儿童、童年、童心的赞美。但不同的是,他很少从社会的道德人格的角度去赞美童心,他主要是从人生、自然的角度去写儿童和童年的。“告别童年这是注定的,但不会告别你/我童年梦中的小雪人”(《不会告别童年的雪人》),这集中地体现着作者对童年的理解及作者表现童年的角度。童年作为个体人生的一个阶段注定是要过去的,但童年的美好会永远地留存在记忆里。它如那梦中的小雪人,纯洁、晶莹,纤尘不染,静静地矗立于远山并成为远山的一部分。在堆雪人的过程中,人们堆进自己的理想、欢乐,堆进自己的童年。即使长大,离开童年,那个世界将永远地鲜活在内心深处,作为一个梦幻永远地成为生命的一部分。所以,邱易东常常捕捉、创造童年生活中一个个具有永恒价值的瞬间,像雕塑一样将其凝定下来,组成生命的远山中一道最为纯朴、自然、清新的风景。“伫立在四月的海岸/你等待一只红帆船”(《游向红帆船》);“对谁也说不清楚说不明白/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小女孩开始栽种一棵白杨树”(《一个小女孩的白杨树》);“在你的笔尖挂一幅雨帘/让它朦胧在你的雨季”(《你的雨季》);“举着风筝/伫立山顶/等待着山谷的风来临”(《在远山放风筝》);“在秋天,春天般的小女孩透过蓝色的窗口/想象着遥远的落叶季节”(《一个小女孩的落叶季节》)。在《寄给小城》一诗里,作者曾说:“在我们远山色彩芬芳的秋风里/阳光和遍地果实总是互相辉映。”在邱易东的诗歌里,童心和远山也总是互相辉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