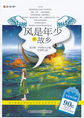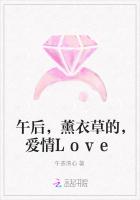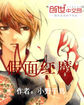8.《沙的字》初次发表时题名《沙滩上,有一行温暖的诗》。改成《沙的字》,意蕴更含蓄了。它表现的是互不相识的人之间的默默的关心。据作者说,这个小作品的产生还有一段和作者自身经历有关的背景。20世纪八十年代末,斑马因一些作品和文章受到一些人的批评,一段时间颇感压力和紧张。但据作者说,就在那段时间里,一些相识和不相识的朋友、读者在不同场合,以不同方式对他表示了关心和支持,这使他非常感动。这篇《沙的字》,就是要表达自己对这些关心、支持过自己的人的感激。当然,作为一篇文学作品,它一经产生,就从作者本人的生活遭遇中超越出来,我们可以不知道这篇童话产生的背景,但会一样体会作者表现在这篇作品中那份极为美好的情感,感受社会生活中那份美好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沙的字》构思的好处全在结尾的那个情节。作品要表现的是“互相关心”,但写作时并未在两个角色间平均用力,也未让视点在小蟹和小女孩间来回跳动。而是侧重写了小蟹,百分之八九十的篇幅都将视点放在小蟹一边,只是到最后,才突然跳到小女孩的视点,通过小女孩的视点告诉读者她写在沙滩上的那行字究竟是什么。这最后的两行字篇幅很少,但分量很重,所以能在结构上使整个故事显出平衡,同时使整个结构变得简洁。将人与人之间的美好情感放到小蟹和小女孩身上,一方面使故事充满瑰丽的童话色彩,一方面也使作品的主题更好地表现出来:两个生活在不同世界但同样还需要别人保护、关心的小生灵却有那么美好的情感,能默默地去关心别人、帮助别人,自然使我们更加的感动。
9.《山的话》。在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出版的《斑马作品精选》中,《山的话》被列在“幽幻小说”中。但我觉得,《山的话》并不怎么幽幻,倒是一篇很有现实意义的小说。一个美术学院的女大学生深入蛮荒的山地去寻找原始古朴的美,可她的向导,一个本地的十三四岁的黑少年却被她所吸引,终日跟着她。她感到有些害怕,用很粗暴的方式摆脱他。可秋天到来时,她乘车返回城市,却发现对面的山坡上,少年用红色的荆草种出的一幅巨大的牛头的画像:“这苍红的牛头威武地下睨,神色野蛮又凶狠,像是作一种示威。再看,那邈远古怪的样子又十分可怜,流露出不能劝止的无奈。”女大学生为寻找原始的美而走进这个原始的世界,她的到来同时就为这个原始的世界打开一扇小小的窗户,透进了一线外面的世界的光明,不知生活在这原始世界的人对外面的世界的渴望其实比这女大学生对原始美的渴望还强烈得多。但女大学生能走进他们的世界,他们却不能走进女大学生的世界。当寻找原始古朴的人胜利完成任务带着他们的成果返回城里以后,少年和他长在山坡上的牛头还将继续地留在深山老林里,悲哀而绝望地望着这深深的峡谷。本来,没有外面的世界的比照,他不会痛苦。可现在,平静被扰乱了,渴望被唤醒了,留下的只是无望的痛苦。幸还是不幸?斑马是一个创造典型画面的高手,只要读过这篇作品,故事末尾那个由红荆草长成的倔犟而又悲哀的牛头形象就会留在心里,久久无法释怀。
10.“我本人也写作现实主义小说,它很有意义。但我始终质疑已被一贯强调又强调的‘儿童文学现实主义道路’这一至尊口号。”①斑马如是说。
①斑马:《游戏精神与文化基因》,甘肃少年儿童出版社,1994年版,第60页。
斑马写作现实主义小说是认真的,我们以上谈及的小说可以作证。斑马对“儿童文学中的现实主义道路”的质疑也是认真的,这质疑从他最初的理论专著《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与构想》已经开始。特别是1998年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出版“大幻想文学”丛书前后,据说还因此和被斑马称为“儿童文学主流批评界”的一些朋友闹了点小别扭。个中情形局外人不甚知晓,但也反映出斑马在这个问题上的执著和认真。
斑马对现实主义的批评主要是在两个层面上进行的。一是在较为具1949体的层面,认为二十世纪的中国儿童文学,特别是年以后的中国儿童文学主要是在现实主义的旗帜下进行的。“本世纪并直至今天的缺乏这些立足点的中国儿童文学界,在各个阶段服从于各段‘现实’,客观上制约了各时期中国儿童的原生性心灵和基本人性的健全发育。我认为,我们的创作和评论中的最大不良倾向就在于浓重的‘社会性’价值取向(就连‘新时期’也有此不足)。”②这种服务于各阶段现实需要的价值取向将儿童封闭在狭小的现实空间中,向后,取消了悠远的历史线索,向前,取消了无比广阔的未来空间,内容上又用最不符合文学规律的理性灌输去影响读者,强调认知而非感知,造成了整个儿童文学的僵化和枯槁。这种创作理念和评论作品的价值取向在“文革”后理所当然地受到青年一代的儿童文学作家的唾弃和反对。“他们几乎齐集地避开了写学校生活,并非学校生活难以接触,而一定有一种内在的感觉,即认识到现行学校教育的趣味中有使他们产生抵触的根本性不良之物,所以,他们有意于欲用作品去设法抵消当代学校所带给孩子们的某些短浅和危险的东西。”①尽管斑马的批评有些偏颇——以学校、家庭生活为主要表现对象的儿童文学也有些较好的作品,包括斑马自己的作品;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一些写中心画中心简单地以具体的一首诗一篇小说去配合政治任务的作品算不算现实主义也大为可疑,但在总体上,我对斑马的上述批评是赞同的,我在一些过去的文章中谈到相关问题时也表达过相近的看法。我较有疑义的是斑马在第二个层面上对儿童文学中现实主义的批评。这是在相对抽象的层面上进行的。即斑马认为,儿童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类型,本质上不太适合现实主义。它应该偏重于蛮、野、神秘、幽幻或亦真亦幻,应该从学校、家庭、社会生活中走出来,走向外面的广袤而蛮荒的世界。不过,斑马不只是用理论也是用他的创作来表达他的这一理念的。因此,我们也只有在了解了他的这些作品以后,才能对他的这一追求进行更深入的评说。
②斑马:《游戏精神与文化基因》,甘肃少年儿童出版社,1994年版,第57页。
①斑马:《你们正在悄悄地超越》,见《游戏精神与文化基因》,甘肃少年儿童出社,版1994年版,第17页。
二
11.野出去。《六年级大逃亡》题名“逃亡”,但其实是写“归来”。但所以有“归来”自然是因为先有“逃亡”,只不过作者这会儿还没对其进行正面描写罢了。但读过《六年级大逃亡》的人都会感到,那个略去的空间里有故事。后来,作者将《六年级大逃亡》扩写成长篇,新增的两部分果然是写李小乔在外面的生活。其实也不只是李小乔。几乎就在写李小乔的同时,斑马笔下的人物正越来越多地从学校、家庭中走出来,走向海边,走向古镇,走向荒野,在月光下在雾气里在阿里巴巴的山洞中踽踽独行,“从这儿通向幽古或神秘的地方去,就像走进内部的深处,眼睛在暗中看到了幻象、秘觉和神灵”。“野出去”,一时成为斑马笔下人物对自身生存方式的一种“齐集性”的选择。“野出去”,从学校、家庭走向丛林、旷野,这首先自然是一个文学题材的转变,是故事中人物活动空间的转移。这转移又不只简单的表面人物活动环境的变化,而是标志着人物生存状态生活状态的改变。从学校、家庭、社会走向蛮荒、文明未启的旷野,首先就在无言中将社会、文化、传统悬搁起来了。而父性话语主要是以社会传统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悬搁了社会传统,也就悬搁了父性话语。即是说,在走向荒野、古镇以后,李戈的教训、任素芳的唠叨、郝老师痛惜的目光连同曹大头练过什么狗屁功夫的手都对李小乔不起作用了。那儿有摩托王、白头翁、斑马叔叔,有康叔、丁宝,有谜一般的古镇,有迷蒙的河汊和若隐若现的大鱼。总之,那是另一世界,李小乔们将在这儿苏醒、更新,寻找和创造一个新的自我。
12.《野蛮的风》。我以为,这并不是斑马写得最好的作品,但却是作者非常重要的一篇作品。说它重要,因为它最早、也比较全面地反映出斑马在以后的创作中要一再表现出来的“野出去”的美学追求。如以后在斑马的作品中一再出现的主要意象如男孩、叔叔、海怪、石刻般的老人、野蛮的风、近似魔幻的现代科技等,都密集地在作品中表现出来。可以将《野蛮的风》看做是作者要在学校、家庭题材之外另开一个世界的信号和宣言。
《野蛮的风》的感性特征是野蛮。作者无意表现某种理性的意蕴,相反,作者首先要人从传统的理性意蕴中挣脱出来,获得一种充满野性和蛮力的感受。一个叫赵晓峰的少年(作品中大部分时间称其为“男孩”“他”)从遥远的内地西安来到一座滨海的城市,正好赶上一场突如其来的台风。在风的激扬下,大海以它全部的野性卷起万丈风浪,向这个第一次来到海边的男孩展开一个充满蛮力的世界。在这种外在力量的激发下,孩子身上的原始野性也升扬起来了。“紧张的肌肉里窜动着一股蛮劲,一刹那竟渴望跳下车去,让身体被那狂风压着,然后站在岸上面向大海作长长的嘶喊。他马上就觉得搅动着这海的,是藏着的一个什么野蛮力量。”风、云、浪、孩子的心理组成一个直接刺激人的感官的画面,浓墨重彩,泼墨般的充满力感,和现代社会的机巧纤弱恰好形成对照。但这又不是一个文明未启的蛮荒世界。在故事中,作者特地安排男孩住在海洋研究所,安排一个叔叔式的人物驾着飞船飞向近地轨道空间站,海洋研究所的人们也正用最先进的科技利用台风产生的巨大能量。最先进的科学和最原始的自然力就这样紧密地联系起来了。这是作者将童话、小说、科幻综合起来的一次试验。或许是要表现的内容太多了,或许是意念性太强,这篇作品的人物和故事没有获得自身的生命力。这不是一篇可读性很强的作品,它的意义要在它以后的一些类似的作品中才能表现出来。
13.沿着《野蛮的风》稍向前延伸,便有了《康叔的云》。依然是一个男孩,依然有一个似从远古走过来的老人,依然是让这个男孩从远处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但这个环境不是以高科技为主要特点的海边,而是现代文明尚未到达的乡村。《野蛮的风》要激发的是男孩原始、野蛮的心理,《康叔的云》要激活的是男孩原始的、自然的感觉。
你突然觉得只有自己一个人在这儿神灵般地独醒着。真是奇怪,自己怎么会坐在了这里?你从来没有这样静地独自一人坐在整个天地之间,而且这么长久、陌生地望着它——“大地。”
你心里第一次清楚地感到这就是大地。——《康叔的云》
粗大的雨点直接打在你光身的肉体上,激起一股酥痒的感觉……你一刹那间那么清楚地获得一个意识:这雨是从天上下来的,天上!你是站在大地,赤脚的掌心中触着软软的细泥,你一用劲,细泥就从脚趾间滋出,这就是大地!你仰脸张口在大雨中这么想着,觉得自己真像原野上的一棵植物,心里身上在长着什么……——《康叔的云》
你眼中突然看到木桩上的绳结在滑脱松动,绳梢悄悄在扭转,两手不能离开,你急忙龇出白牙低头凑去,一口咬住了粗丝的绳头,用牙根死命地咬定,强扭着脖子用劲,咔咔响地收紧绳结。这样用牙齿撕咬着用力,一下子使你心里发野,在一股蛮力中绳结抽得绷绷紧。待松开牙齿,吐着泥水和沙质,你觉得整个人升满了一种动物般的生气勃勃。——《康叔的云》
不是强调人的精神、文化,不是强调人在精神、文化方面与动物的差异而是强调人回到动物,有了动物以至植物般的感觉,这不是一种倒退,而是寻回那种本属于人,但却在习惯化的文化中失落了的、被异化了的东西。这些描写使人很容易联想到胡塞尔的“现象学还原”和什克洛夫斯基“使石头显出石头的质感”的话。在整个教育都趋向知识、理性、精神、文化的时候,对野性、生命力的张扬确给人一种重新回到大地的感觉。
14.与此相近的还有《鱼幻》。《鱼幻》是一篇在当时引起许多争论的作品,只是争论的焦点不是在作品写了些什么、写得怎么样,而是集中在它是不是儿童文学上——不知道斑马是否曾为此感到悲哀。
《鱼幻》是一篇写得很纯粹的艺术小说,它和《野蛮的风》《康叔的云》等作品一样,显出作家很自觉的美学追求。当作品中的“你”——一个生活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中的中学生逆黄浦江而上一步步走进蛮荒的江南腹地时,他就从体现着人的创造力的都市文明走进了近于原始的自然,走进了一个半开化的、尚未明显受到现代文明濡染的充满大自然本身野性和生命力的世界。作品极力渲染了这个野性世界的迷蒙、浑茫,如混沌之未开的感觉;同时,这也如同驶入了历史。考古学家说,历史是可以以地表的堆积层次来划分的,后来的历史堆积在原来的历史上,越向纵深,时间越久远。西方人说,历史是写在羊皮纸上的,羊皮纸分好多层,今天历史上有昨天的痕迹,昨天的历史也会在今人的读解中现出新的意义。其实,历史更是活生生地存在今天的生活之中的。现实生活也有不同的层级。当少年乘着小火轮离开大上海一步步走进江南腹地的乡村时,他也是在逆历史之流而上,从最文明的现代一步步走向人类历史的半开化期、未开化期,一种地老天荒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甚至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葛天氏之民的境界;再进一步,少年沿黄浦江一步步走向它的源头,也是一次心灵的探险,是在一步步地走向自己心灵的深处。越在表层,人越属功利化的现代文明;越走向深处,现代文明强加在人身上的桎梏就越显松动、消解,人的原始的生命活力一点点显露出来。在现代都市文明与传统乡村文明的矛盾中,斑马不是简单地否定前者而走向后者,如五四时期一些作家所表现的那样。他倾向的是一种原始的没有异化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可以表现在现代人以高科技的手段征服自然的活动里,也可以存活在乡野人普遍的日常生活里。
《鱼幻》写得迷蒙、浑茫,也体现着斑马离开理解走向感知的艺术追求。在淡淡的象征中,作者将空间时间化了;也可以倒过来说,将时间空间化了,将外在的世界心灵化了;或者说,将内在的心灵物质化了。这也是作品对浑茫、原始的美学追求的一种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