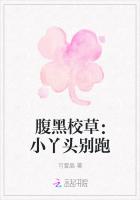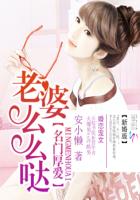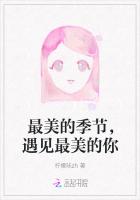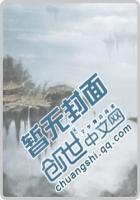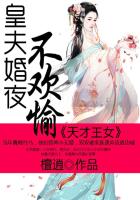在中朝文学比较研究中成果最显著的,首推北京大学的韦旭升(1928—)教授。韦旭升在朝鲜—韩国学研究及中朝文学比较研究方面的成果,都收在了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六卷精装本的《韦旭升文集》中。该文集收入了作者1980—90年代的专著、论文、古籍整理等方面的成果。其中第一卷收《朝鲜文学史》,第二卷收《抗倭演义〈壬辰录〉研究》(附《壬辰录》朝文本、汉文本),第三卷收《中国文学在朝鲜》及相关论文,第四、五卷分别收朝鲜古典名著《谢氏南征记》、《九云梦》和《玉楼梦》的文本整理及相关论文,第六卷收翻译、创作、朝鲜语言方面的研究成果。《韦旭升文集》作为我国出版的第一种个人著述的朝鲜—韩国学及中韩文学比较研究的文集,在近二十年来的学术史上是引人注目的。
《韦旭升文集》中的《中国文学在朝鲜》,1990年由广州的花城出版社出版初版本。这是我国第一部、也是世界上第一部系统全面地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在朝鲜的传播与影响的学术专著。出版后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和反响,先后被译成韩文、日文,分别在韩国(1994年)和日本(1999年)出版。该书不是按历史的时间线索,平铺直叙地描述中朝文学关系,而是以中国文学在朝鲜传播与影响的若干基本问题来谋篇布局。全书共分四章,论述了四个基本问题。在第一章《中国文学得以传播并作用于朝鲜文学的基础》中,作者从地理条件、政治关系、文化关系三方面入手,论述了中国文学传播和影响于朝鲜文学的历史背景、文化氛围。第二章《朝鲜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吸收和利用》是全书的核心部分,作者分为十个问题来谈。
一、作品的输入与传播。其中重点谈到了唐代的张文成小说《游仙窟》、《昭明文选》,苏东坡、黄庭坚的作品,还有《太平广记》、《剪灯新话》等作品的输入和传播情况。二、文学样式(体裁)的采取与借鉴。作者从比较文体学的角度出发,研究了汉诗的各种体式、词、散曲、传记文学、传奇小说、章回体小说等文体对朝鲜汉语文学和朝鲜国语文学的影响。三、“作品的变形与加工”,论述了朝鲜作家将输入的中国作品加以改动、变形,使之以朝鲜国语文学的面貌和形式出现。四、“主题、题材、情节的仿效与复现”,以比较文学的主题学研究的方法,对朝鲜文学与中国文学中的基本主题与题材做了比较。
五、韦旭升指出了中朝文学作品中人物的“客串”情况。即中国文学作品中的人物进入了朝鲜文学作品,和作品中其他虚构的人物一起“演出”,起“客串”的作用。如《三国演义》中的关云长出现在朝鲜的抗倭小说《壬辰录》中,诸葛亮出现在朝鲜长篇小说《玉楼梦》中,等等。六、韦旭升分析了朝鲜文学对中国文学中的艺术手法的引进和运用。七、研究了中国的思想、风气与流派对朝鲜文学的浸透。八、从文学语言学的层面上论述了朝鲜文学对中国文学中的词语、词藻典故的吸收和利用。九、谈到了朝鲜作家笔下的中国形象,以及以中国为背景的传奇与小说。十、论述了中国文学批评对朝鲜文学批评的影响。
在第三章《中国文学作用于朝鲜文学的途径和结果》中,韦旭升运用比较文学传播研究的方法,描述了中国文学是通过什么渠道到达朝鲜、进入朝鲜作家的书斋及作家的创作中的;他指出中国文学进入朝鲜文学的渠道有两条,一是以书籍为渠道,一是以人为渠道。关于中国文学作用于朝鲜国语文学的“路线”,韦旭升概括为一个公式,即:“中国文学→朝鲜汉文文学→朝鲜国语文学”。关于中国文学作用于朝鲜文学的总体结果,韦旭升概括为“四大一深”,即:“大量的汉文文学作品、大量的以中国为背景或描写对象的作品、大量的针对中国文学作品的评论、大面积的投影,深层次的影响”。
在第四章《中国文学在朝鲜的余波和功过》中,韦旭升总结了中国文学对朝鲜文学的发生和发展所起的重大作用,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在中国文学影响朝鲜文学的“功”的方面,韦旭升概括为:“提供文学的工具、手段(对汉文学),提供借鉴(对朝鲜国语文学),缩短了朝鲜文学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关于“过”的方面。韦旭升写道:
中国文学在朝鲜广泛深入的流传过程中,也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这就是它也曾使得一些文人士大夫产生了对中国文学的依赖性,阻挠过朝鲜国语文学的及时产生和迅速成长,在某种程度上压抑了国语文学的生机。
由于有了汉文作为书写工具,加上可以不费力地从大量成熟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吸取体裁、技巧、经验,再加上统治者在政治、教育上的提倡,朝鲜文人长期已习惯于以汉文文学为正宗的古老传统,对于还处于幼稚和粗浅状态的国语文学采取了轻视态度,不愿花大力气来推进国语文学的建设。(中略)
这种情况,对国语文学的发展、成熟,是很不利的。它使得处于古典文学阶段的朝鲜国语文学作品,含有太多的中国文学辞藻,在修辞、写法、艺术技巧上,也未能迅速脱尽稚气,臻于妙境。
作者以文学的民族风格与民族文学的独创为根本的文学价值观,站在纯学术的立场上,对中国文学输入并影响朝鲜的“功过”做了科学、客观的分析与总结,既看到了中国文学的正面影响,也看到了它的负面作用。对于一个中国学者,特别是比较文学研究者,这种开阔宽广的文化胸襟是可贵的。
韦旭升在中朝文学比较研究中的另一部力作是《抗倭演义〈壬辰录〉研究》,初版本1989年由太原的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抗倭演义〈壬辰录〉》是以16世纪最后几年中国明朝和朝鲜官民联合抗击日本人侵略朝鲜的真实历史为题材的历史小说,也是朝鲜古典文学名著。因那场战争开始于1592年,即壬辰年,故称为《壬辰录》,又名《抗倭演义》。韦旭升的《抗倭演义〈壬辰录〉研究》共分十章,运用文学与历史学、文学与战争的跨学科研究方法,以中、日、朝三国的关系史研究为出发点,对《抗倭演义〈壬辰录〉》的历史背景、壬辰战争的特征与性质、《壬辰录》产生之前朝鲜文学中的以壬辰卫国战争为题材的作品,做了背景性的梳理。
对《抗倭演义〈壬辰录〉》中抗击倭寇的英雄人物形象和侵略者、卖国贼的形象,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对《抗倭演义〈壬辰录〉》所反映的中朝友谊的主题、所描写的史实、所体现出的艺术性以及它的各种汉文版本、它的意义和影响等,都做了深入的论述和研究。这种以一个文本为中心的多角度、多层面、跨越多国、跨越学科的研究,在比较文学研究中,是有着相当大的学术价值和方法论意义的。而且,这种研究的意义甚至超出了学术价值本身。一般读者对400年前那场持续六七年的中朝联合的抗日战争,已知道的不多了。《抗倭演义〈壬辰录〉研究》可以提醒人们:日本军国主义以朝鲜为跳板入侵中国大陆,是四百年前的丰臣秀吉时代就已暴露出来的狂妄野心。联系当今日本军国主义蠢蠢欲动的现实,我们不能丧失应有的警惕。
进入1990年代后,我国的中朝—中韩文学比较研究事业,取得了更多的成果。1990年,我国延边大学自己培养的第一位朝鲜文学专业的博士金柄珉(1951—)的博士论文《朝鲜中世纪北学派文学研究——兼论与清代文学之关系》由延边大学出版社出版。所谓“北学派”,是“实学派”中的一个流派,是以提倡“北学”(即当时先进于朝鲜的中国清代的文化科学技术)为特征的思想与文学流派,其代表人物有朴趾源、洪大容、李德懋、刘得恭、朴齐家等。金柄珉的论著在吸收和消化韩国的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首次将北学派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学流派,并对该派的文学活动、文学观念、创作意识、审美表现、与我国清代文学的关联、在文学史上的性质与地位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梳理和研究。1994年,金柄珉、金宽雄博士合著的《朝鲜文学的发展与中国文学》一书,由延边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部著作按纵向的历史线索,系统地描述了中国文学在朝鲜文学发展进程中的影响与作用。全书共分五章:第一章,上古至新罗时期(9世纪之前),第二章,高丽时期(10—14世纪),第三、四章,李朝时期(15—19世纪),第五章,近代和现代(19世纪至1945年)。该书对中朝文学关系的这种纵向的历史考察,正好可以和韦旭升的《中国文学在朝鲜》的横断面的论述方式相互补充。
1994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又出版了两部关于朝鲜文学的研究著作。一部是李岩(1950—)的《朝鲜李朝实学派文学观念研究》,一部是朴忠禄(1928—)的《朝鲜文学论稿》。李岩的《朝鲜李朝实学派文学观念研究》也是一篇博士论文,论文的研究对象——“实学派”是17—19世纪中叶朝鲜封建社会末期出现的思想流派兼文学流派,在研究范围上与上述的金柄珉的论著是有所重合的。《朝鲜文学论稿》是一部论文集,共收二十二篇文章,其中有些文章涉及朝鲜文学与佛教文化的关系以及李白、杜甫对朝鲜文学的影响。
金宽雄(1951—)的《韩国古小说史稿·上卷》(延边大学出版社1998)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地梳理韩国古小说及其与中国文学关系的专门著作。《韩国古小说史稿·上卷》共分三编。第一编《通论》,第二编《汉文小说史》,此两编为上卷。第三编为《韩文小说史》,尚未出版。其中,第一编的《通论》部分,以二百多页的篇幅,细致地论述了韩国古小说中的一系列基本的理论问题,在论述这些问题的时候,又是以中韩文学的比较为基础的,充分体现了作者的理论概括力。例如,在谈到韩国古小说兴起早,但与日本相比发展缓慢的问题时,金宽雄指出:这与韩文的相对晚出有关系,而且在韩国的民族文字“训民正音”诞生后,仍然不能动摇汉字汉文的正统地位,而朝鲜人使用的汉文,又是作为书面语的文言文,习之不易。
“长期以来,韩国文人在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字或在自己的民族文字不够完善的条件下,只能把自己束缚在早已凝固化了的文言形式中,从而大大减损了文学语言的创造力和生命力”,这也是造成汉文小说篇幅普遍较短的原因。而晚近(李朝后期)出现的汉文小说,由于没有汉语文言的制约,有的作品(如《玩月会盟宴》)甚至达到了一百八十卷、六百万万字的巨大规模,在篇幅上为中国、日本的小说远不能及。《通论》部分还专门有一节论述了韩国古小说与中国文学的关联,以及韩国古小说通过中国文学所受到的印度佛经文学的影响。其中,论及中国的史传文学对韩国古小说的影响时,颇有新意。
他指出:司马迁所创立的纪传体史书的叙事模式为韩国古小说提供了不可企及的范本,为此韩国古小说的作者们都有意或无意地仿效它。作者还指出,史传小说之外的杂体传记文学,即“杂传”,特别是杂传中的“假传”,在韩国古小说中数量多,影响大,占重要地位,而在中国文学史上,《毛颖传》之类的假传是一个不起眼的种类,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也不大。
然而,这些假传东渐韩国后反响很大,高丽时期的文人竞相效法,使得高丽时期汉文学中假传迭出,出现了假传文学繁荣的局面,并对后世小说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第二编《汉文小说史》中,作者先介绍了汉文小说的概况,然后将韩国汉文小说划分为“孕育期”、“诞生期”、“发展期”、“成熟期”共四个时期分章论述。金宽雄的中韩比较文学方面的著作除《韩国古小说史稿·上卷》外,还有《朝鲜古典小说叙述模式研究》(延边大学出版社1995年)等,但印数都太少(几百册),搜求不易,限制了在读者中的流传。
在中韩文学关系的研究著作中,值得提到的还有延边大学的崔雄权的《朝鲜朝中期山水田园文学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这是作者的博士论文,对朝鲜朝中期二百多年的山水田园文学做了系统的阐述和研究,其中有一专章分析了陶渊明对朝鲜山水田园文学的影响及朝鲜作家接受这种影响的历史文化的原因。就这个问题论述的深度而言,在其他有关研究著作中是少见的。湖南的陈蒲清的《古代中韩文学关系史略》(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是一本十二万字的小册子。作者原本不是韩国文学研究者,也未习韩文。他主要根据中文文献,对中韩文学关系做了清理。作者在“后记”谦称:这只是一本普及性的书,“而难以达到研究的高度”。但在有些方面,还是补充了现有研究中的不足,而具备了自己的特色。特别是在朝鲜神话传说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研究上,材料较为丰富,论述也较为透彻。
1980年代以来,有关中朝(韩)研究的论文也陆续见诸报刊。1982年,《文学研究动态》第六期刊载了杨昭全的《中国古代文学对朝鲜文学的影响与交流》一文,同年5月,《天津日报》刊登了朱泽等人合写的题为《堂堂笔阵,滚滚谈锋——异国相知的中朝诗人》的文章,可以说是80年代中朝(韩)比较文学研究的发端。1980—90年代,在中朝(韩)比较文学方面发表论文较多的有韦旭升(有关论文已收入《韦旭升文集》第3卷)、杨昭全、金宽雄、金柄珉等。刊发有关论文最多的期刊是《延边大学学报》和《东疆学刊》。事实上,这两家刊物已经成为我国中朝(韩)文学比较文学的最重要和影响最大的核心期刊。
(第四节)中国与东南亚各国文学关系的研究
中国文学与东南亚各国文学,也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中国文学与东南亚文学的关系研究、比较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方兴未艾的现代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其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东南亚华文文学(主要是所谓“马华文学”)的研究。宽泛地说,这也属于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但由于这种研究只跨了国界,而没有跨越语言和民族,而且有人认为海外的华文文学只是中国文学的分支或支流,所以我们暂不准备将有关东南亚各国华文文学的研究纳入本书评述的范围。
一、中国与东南亚各国文学关系的研究
除现代海外华人文学研究之外的、以中国与东南亚各国文学为中心的比较文学研究,在近20年来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尽管数量有限,也还是陆续出现了一些文章和专著。
其中,中越文学比较研究的文章较多,共有十来篇。北京大学教授颜保的《越南文学与中国文化》一文,是我国最早的系统地概述中越文学关系的有分量的论文。文章论述了越南的三个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学——汉语文学、字喃文学和文字拉丁化以后的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密切关联,并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