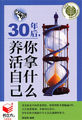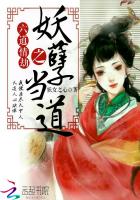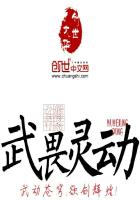尽管从吴朝独立以来,有些王朝在不同的情况下,曾经采用过不同的措施来争取摆脱中国文化的羁囿,但总是较难冲破这一樊篱。如为了摆脱汉字的束缚,创制了自己的文字——字喃,但组成字喃的基础仍是汉字;创立了自己的诗体——韩律、六八体、双七六八体诗,但音韵格律仍未超出汉诗的规矩,而作品的内容又多采自中国。到了拉丁化文字产生之后,翻译工作开始了,又是以译介中国作品为主,对一些常用词或成语,竟好多都直接音译,使得越南词汇中的汉语成分更加增多。而最突出的是贯彻着整个越南文学创作进程的思想,一直是从中国传入的儒道并重的精神。
这些分析和概括都是十分精当的。
1989年,温祖荫发表了《越南汉诗与中国文化》(《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评述了越南汉诗的发展演变和古今重要诗人的作品,并将越南汉诗分为咏古缅怀诗、神州行旅诗、中越友谊诗、抒怀咏志诗四个方面,指出了它们与中国文化的深刻联系。1992年,《文史知识》杂志发表了胡文彬的《中国文学名著在越南的流传》,主要谈了《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特别是《红楼梦》六部名著在越南的翻译、改写和流布情况。
同年,《国外文学》杂志发表了钟逢义的《论越南李朝禅诗》,分析了中国的佛教禅宗对越南诗歌的影响。有关的论文还有:国安的《唐代中原与越南文人的友好往来诗》(《印度支那》1986年第2期)、陈黎创的《浅谈〈诗经〉在越南》(《贵州文史丛刊》1995年第4期)、余富兆的《浅谈由中国小说演化而来的越南的喃字文学》(《东南亚论坛》1998年第1期)、蒋春红的《王翠翘的形象与女性命运——兼论〈金云翘传〉在亚洲的传播和影响》(《东方丛刊》1998年第3期)、麻国钧的《中越水傀儡戏漫议》(《戏剧》1998年第4期)、于再照的《论越南汉诗的产生与演变》(《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1999年第5期)、陈益源的《越南〈金云翘传〉的汉文译本》(《明清小说研究》1999年第2期)等。
此外,我国还出版或发表了越南学者有关中越文学比较研究的成果。如,1979年,台湾台北大乘精舍印书会出版了越南释德念(本名胡玄明)博士用汉文撰写的博士论文《中国文学与越南李朝文学之研究》,在研究的系统性、深入性和规模方面,是二十年来少见的,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台湾学者陈益源2000年在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的《小说与艳情》一书中,作为附录收入了越南学者范秀珠的两篇文章《〈贪欢报〉:在越中文化交流中离了谱的一部书》、《〈贪欢报〉与越南汉文性小说》,其资料和观点都有参考价值。
除越南之外的东南亚其他国家,在文化上主要属于印度文化圈的范围,但中国文学在那里也有频繁的传播,它们的文学也或多或少受到中国文学的影响。在这方面,近20年来也出现了若干研究成果。
关于中国与缅甸文学的关系,《国外文学》1983年第4期发表了北京大学缅甸语言文学专家李谋、姚秉彦的文章《浅谈中国文学在缅甸》。文章在谈到缅甸传统文学为什么受中国的影响不明显这一问题时认为,这首先与佛教的传播有关,所以它受到了印度文学的很大影响,而缅甸的佛教是小乘佛教,与中国所接受的大乘佛教在体系上不同,所以中缅历代都有政治经济上的频繁的往来,而中国文学影响缅甸却不明显。
其次,虽然缅甸的中国侨民不少,但他们文化水平低,并且从事着与文学无关的商业与手工业,所以对中缅文学交流作用不大。关于中泰文学关系,有潘远洋的《泰国文学史上的“中国热”》(《东南亚》1988年第1期)、戚盛中的《中国古代通俗小说在泰国》(《国外文学》1990年第1期)、张兴芳的《泰国文坛的中国文学》(《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1年第3期)、饶凡子的《中泰文化融合与泰华文学个性》(《暨南学报》1992年第1期)等。
关于中国文学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文学关系的研究,有许友年的小册子《论马来民歌》、王振科的文章《中国现代作家在新马的文学活动》(《海南师范学院学报》1990年第2期)、杨启光的文章《中国武侠作品在印尼》(《文史知识》1992年第2期)等。其中,许友年的《论马来民歌》是我国唯一一部介绍和研究马来民歌(原文称马来班顿)的专门著作。全书共十万字,分上下两编。上编是《马来民歌选译、简介》,共译介包括儿歌、讽喻歌、情歌、生活歌及其他类型的马来民歌二百四十八首。
下编是《论马来民歌》,以较多的篇幅论述了马来民歌与中国文化、中国民歌的深刻联系,认为“中国移民在推广和普及马来班顿这种民歌形式方面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指出马来民歌中大量反映了中国的人物、事件和风俗习惯。作者还对马来民歌与中国民歌(包括《诗经》、《乐府诗集》和我国南方地区的山歌)的相似性做了分析。全书最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大量的事实证明,马来民歌是接受了中国民歌传统的影响,除了史前马来人种南迁时带去的影响外,主要还是通过后来的中国东南沿海移民,特别是闽南人带过去的。其根据是印度尼西亚语和马来语中吸收的汉语借词,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闽南方言,而一百多年来对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文学起过广泛和深远影响的华裔文学的作家或翻译家也多为闽南人。印度尼西亚和马来半岛的中国侨民几百年来不仅是马来民歌的热心的即席创作者,而且有不少还是创作马来民歌的里手。上述这一切,毋庸置疑,必然要把中国的文化和民歌传统带到马来民歌中去。
中国文学与东南亚文学的总体的比较研究专著出现得很晚,而且数量很少。1980年代尚无这方面的专著。1989年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了颜保翻译的法国著名汉学家克劳婷·苏尔梦编选的《中国传统小说在亚洲》一书,虽是译著,但也值得一提。其中选收的十六篇由各国学者写的论文中,大部分是以中国传统小说在东南亚的传播与影响为课题的,是一部很有用的专题论文集。到了1990年代初,当乐黛云教授等在主编《中国文学在国外》丛书的时候,曾将《中国文学在越南》和《中国文学在东南亚》两种著作列入出版计划,但最终都没有在本套丛书中问世。直到1999年,暨南大学饶凡子教授主编的《中国文学在东南亚》一书才由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成为我国出版的第一种有关领域的专门著作。
全书共分四章。第一章《中国文学在越南》,由林明华执笔,第二章《中国文学在泰国》,由王棉长执笔,第三章《中国文学在新马》,由黄松赞、莫嘉丽执笔,第四章《中国文学在菲律宾》,由王列耀执笔。该书较为系统扼要地评述了从古至今中国文学在东南亚主要国家的传播和影响情况。饶凡子在该书的前言中坦言:“一些国家的这方面资料目前还很难掌握。在本书中,我们只就与中国文学交往较深的越南、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菲律宾等几个国家做尝试性的探索。”尽管论及的范围并不周全,但作者们毕竟是做出了相当大的努力。前三章写得比较翔实,第四章虽较简略,但有关中国文学在菲律宾传播的问题,此前基本上没有人做过认真的研究,该书列出专章讲述,填补了一个空白。